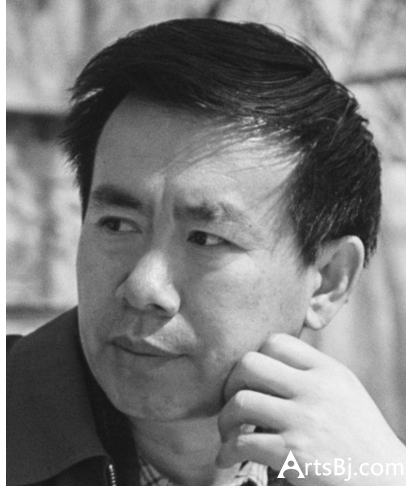
像闯入一片陌生的热带森林,处处是奇异迷人的风景,流动着盛情绽放的芳香,一种神秘的悬念不由地魅惑你前行,仿佛真有更奇幻的风景或装满宝藏的山洞。
而阿里巴巴的咒语,隐藏在《独药师》中。
这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张炜吗?语言诗性依旧,思想深刻依旧,叙事耐心依旧;然而又全然是陌生的。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的异质文本,饱满充沛的叙述以及环环紧扣的情节,带来阅读的冲击力非同寻常。
张炜有很多头衔: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数不清的各大高校的兼职教授……2016年12日3日,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又和贾平凹同时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曾被冠以诗人之名,也被标识为“道德理想主义”,更因“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标志性人物。
他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最爱的是写作。
所以张炜同样看重《中华读书报》所颁发的“年度作家”。因为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中华读书报》所刊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很多文章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和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被记录进当代思想史。
时代不同了,类似的讨论不可能接续下去。今天看这样的讨论甚至有些奢侈。但讨论又是极有意义的。尽管讨论中有对作品的误读,但也有吸引读者再次深入阅读的作用。误读是发生在所有作家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误读会一点点解除,不过新的误读也会一点点出现。而这一切,正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作家应该是丰富的、经得起误读折磨的、多解的,有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张炜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讨论了,似乎大家关注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一些事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娱乐品。当年一些言辞激烈的青年参与了那场大讨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或准老年,再回头看去,大有人事沧桑之慨。他认为,关于“人文”,关于“精神”,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成为话题,当然是至为难能可贵的。人们现在谈论的往往是其他,虽然也不乏意义。不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定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它仍旧在以各种方式进行下去,只要人类还有生存,还要活着,也就不会间断这种思考。
多年来,张炜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也包括2016年初出版的古典文化随笔《陶渊明的遗产》。他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在加入他们,不过是异常缓慢地进行着,时而有时而无,断断续续。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已经被符号化了。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陶渊明以前作为一个符号太过简单化概念化,有时候简直成为极肤浅的东西存在着。所以深入解读陶渊明,是一件时代大事,这个事情不光是一两个人需要做,而是很多人都要做起来。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会大致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关于他们的单纯学术解读很多了,从阶级学说出发的社会解读也很多了。但仅有这些似乎仍旧不够。有一些永恒的冲突缠绕着他们,这些冲突更需要我们当代人去直面。
在张炜的阐述中,真正抵达远方的诗人,可能仅仅只有一个陶渊明——他论证五柳先生的“心远地自偏”真正达到了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远方。陶渊明所有的诗歌中,仰望远远不及俯视,他注目土地和原野的时间非常多,对于土地和田园,他的视角与我们大多数人并无二致。张炜从陶渊明的视角中发现了一种坚固,这坚固包含了文人的自我坚持与不肯屈从,这是极为珍稀的。
之所以能发现这坚固,亦或因为张炜内心同样坚固的倔强。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而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它的出版对我是一次考验。40多年的文字磨练,人生经验,在里面都会留下痕迹。我在年轻的时候写不出这样的书。对生活的理解,对文字的严苛,这一切加起来才能使我试着把握它。”《独药师》的品质只有今天才能显现,对张炜来说正是如此。这部书需要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去领悟。
“我一直强调‘文学阅读能力’这句话,说多了也许有人不解,误以为是导向‘小众’。其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文学作品的阅读当然需要这种能力。我们有时候将写作的目标,自觉不自觉地瞄向了没有这种能力的人,认为成功就在那个方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写给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恰是最基本最朴素的想法。”张炜说,无论是谁,只要离开了这个想法,他的文学就会败坏。事实证明有这种能力的人还是很多的,这部书的热烈反响和回应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有这种能力的人并非“小众”,他们有自己强大和广泛的一面。而且不同的是,他们会坚持到最后,走向很远。对这一点张炜仍然是乐观的。
这部书出版后一连数周在销售榜的前三。
同时名列榜单前茅的还有张炜一系列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他总是担心少年读者已经读到了许多坏的文字。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你在高原》刚刚出版时,诗人朋友送给张炜一个别致的笔记本,鼓励他继续写诗。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张炜写满了一个又一个大笔记本,精致地搁在书架上,这些诗歌让他满足且快乐。将来把它们出版,或留作自读,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诗通向心灵深处。离开了诗的写作,就会枯槁。真正的诗人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是念念不忘的朋友,但他们不一定总是使用诗的常用的格式去做。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性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能不是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马尔克斯说:生活只是我们能够记住的日子。“如果生活仅仅是这样,那写作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幸亏有了写作,这才能使已经过去的时间记录下来。”张炜说,接下去的事情就是好好写作。他要写许多许多诗,因为它是记忆的最好方式。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