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想象力很难离开地面,而您的想象世界却总是在天空之上。”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对宫崎骏的赞誉,应该也是动画迷的心声。
01
不管怎样,先画起来
从《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到《起风了》,宫崎骏单独执导了11部动画长片,历时30余年。从孩童到耄耋老者,画画陪伴了宫崎骏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在与动画相伴的时光里结婚、生子,在事业上走出低谷,摘取荣耀,获得自信,可在生活里,却成了“充满懊悔的父亲”。 他说: “我只知道工作,根本就是工作过度的父亲,我没有带给他们任何阴影,但在家里也没有任何存在感。 ”
长子宫崎吾朗最终还是沿着他的道路,走上了动画导演之路,可这似乎并没能弥合他们疏离的关系,父亲的光环就是无形的压力,在工作室创作分镜脚本时,如果宫崎骏走过来,宫崎吾朗就会把贴满分镜脚本的木板背过去,一眼也不让父亲看。宫崎吾朗已经执导了两部动画片——《地海战记》和《虞美人盛开的山坡》,前者惨败,后者成熟了许多,但也并没有显现出足以与父亲抗衡的才华。

《虞美人盛开的山坡》
宫崎骏的想象力并未枯竭,可是如何把它们具象化,以栩栩如生的动态呈现在画面上,却是对体能的挑战,他不想告别,可是不得不与日渐衰老的身体妥协。他一直坚持手绘动画,画笔从HB换成了5B,即便在理疗按摩的帮助下,每日能坚持的作画时间还是从以前的1/3降到1/5,不断递减。他把自己限定在工作室半径不超过3米的空间里作画,在精神的高度集中里感受大脑的灼烧,所以勒令自己从跨出大门那一刻开始,就绝对不再考虑工作上的事情。 他自我训练了一套减压方法:“回家的路上我数巴士,盯着马路那头,一心一意地数,如果到达一定数量,就认为每天做的事都是正确的。”
不管怎样,先画起来。这是宫崎骏的创作方式:“不从故事情节出发,先把想要表达的场景通过图画表现出来。”“不停地画,越多越好。画够了,—个世界便成形了。”“借由想象力、技术,以及所有磨炼技艺的过程,你的题材会渐次成‘形’。就算它现在显得暧昧不明,或只是一个朦胧的憧憬也没关系。 只要拥有想要表达的目标,那就是一切的开始。 ”比起逻辑,他更仰仗灵感,故事结构在平衡感上的缺陷,反而成就了宫崎骏影片的特色,因为灵感和想象力,才是不可言说的天赋。
他说自己就是“电影的奴隶”,他的心愿是“娱乐于人”,“只有让大家感受到娱乐,才能使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得承认”。他以动画作为自己并不快乐的童年的心理补偿,传达出的讯息却是生之礼赞。 不管怎样,都要用力活下去,这是宫崎骏的影片中永恒的主题。 他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够唤起潜藏在孩子们心中的坚韧,令他们有所改变,像《千与千寻》的主角荻野千寻那样,最终发掘出自己“不被吞噬的力量”。“生存就是生命体在发展中保持平衡的方法,为了保持平衡,就必须做一些努力。”
在朋友们眼里,宫崎骏本人比作品更有趣。他总是有各种奇思妙想,比如幻想着“当一个可怕又奇怪的祖父,为孙子们制造惊奇”;“孙子一进到祖父的房内,就看到一大堆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在天花板画上惊悚的云朵,然后挂上一幅长达3米的巨翼龙画像,让它随风摇晃,而我这爷爷便端坐其中”。
他也是个“爱操心的人”,“老是担心别人且乐于助人”,“结果把一大堆麻烦事往自己身上揽”。他还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挚友高畑勋说,宫崎骏“是个非常害羞的人,有孩子气的一面,天真无邪又任性率直,所以会把自己的欲望表现在脸上。可是,却又有着比别人多一倍的律己、禁欲意志以及羞耻心,因此经常想要加以隐藏,使得表现出来的行为显得曲折不可测”。
对于内心的矛盾与分裂,宫崎骏自己寻找过追根溯源的解释:“从小,我就认为父亲是个错误的示范,可是,我却觉得自己跟他很像,那种杂乱无章的处事风格,与矛盾和平共处的态度,我都继承了下来。”他描述的父亲,是一个“公开声明不想上战场,却又因为战争而致富,随时都能与矛盾和平共处”的人。“战争结束之后,父亲对于自己曾经担任军需产业的制造者和生产瑕疵品这两件事,根本没有任何罪恶感。什么做人的道理、国家的命运,全都与他无关。他唯一关心的是,一家人应该要如何活下去。”
在2005年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获奖感言,是宫崎骏对他和吉卜力的定位:
“我们的作品本来就不代表日本的动画电影,反倒应该说,我们是站在日本动画的边陲,所从事的一向都是反潮流的工作。 我们总是以要在下一部作品背叛死忠观众的方式,勇敢向前行。”
“就像我的肚子完全不会缩小一样,我对于大量的消费文化日渐肥大也感到气愤。而我们的动画电影本身,就是大量消费文化的一员,因此,这个大矛盾就像是我们的宿命一样,随时威胁着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美术热衷于将太阳的光芒放进画面里,描绘出空间层次,表现出世界之美。尽管惨剧正在眼前展开,我们仍应尽全力表现出其背后的世界之美。”
02
我们有的只是野心
“若问那个充满不安又缺乏自信,拙于表达自己的我,当时可以从哪里得到自由,答案是有时从手冢先生的漫画,有时则是从一本借来的书。现在大家虽然疾呼要正视现实,直接面对,但我觉得,对那些一旦面对现实往往就信心全失的人来说,首要之务应该是让他们拥有自己能够当主角的空间,而这就是幻想的力量。”
“我认为创作动画就是在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那个世界能抚慰受现实压迫的心灵,激励萎靡的意志,能化解紊乱的情感,使观者拥有平缓轻快的心情,以及受到净化后的澄明心境。”
在吉卜力工作室里系上作画用的围裙,宫崎骏看起来既像传统的手工匠人,也像动画片里有魔法的老爷爷。挚友高畑勋曾戏谑说,“每一顶帽子都必须是特大号”才能装下宫崎骏的头,或许是因为头特别大,须发皆白、戴着大黑框眼镜的宫崎骏,亲切又有些卡通,这也是动画迷眼中,动漫大师宫崎骏的标准像——他成名晚。
大学毕业进入东映动画公司,宫崎骏才正式涉足动画业。在公司前辈保田道世的回忆里,这个年轻人才华超群:“他的想象力之丰富令人震惊,我那时候就认识到,他这个人不得了。”如果这是个预言,那么早已成真,只是过程波折。事实上,在动画制作行业里打磨了16年之后,宫崎骏才第一次得到执导一部剧场版动画长片的机会。1979年12月25日,《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公映,宫崎骏才有了自己的处女作,38岁,几近不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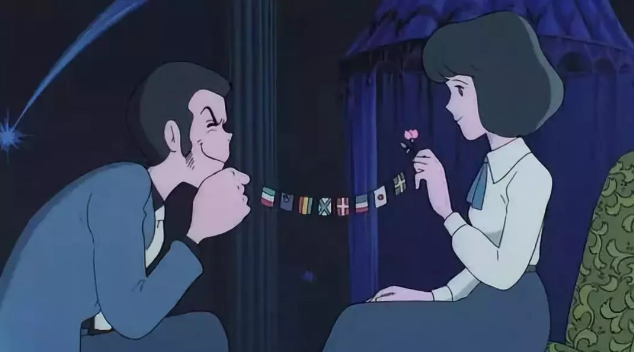
《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
《鲁邦三世》是日本漫画家加藤一彦的作品,从1967年开始连载,讲述怪盗鲁邦家族第三代传人的冒险传奇,故事杂糅,画风粗犷,在日本拥有超高人气,陆续被改编为电视动画、剧场版和OVA(原创动画录像带)。就像永远在读小学的少年侦探柯南一样,侠盗鲁邦三世也是日本动漫界的不死传说。20世纪70年代末,《鲁邦三世》的电视动画系列已经陆续播放了近200集,故事情节也从最初的偏成人化转向低龄化。宫崎骏拿到的片约,是制作《鲁邦三世》剧场版的第二部,目标观众设定为十五六岁的青少年。
宫崎骏是东映动画招收的最后一批正式雇佣制社员,经过3个月的入职培训,开始动画师生涯。动画师,就是“让图画动起来的画师”,他们是支撑日本庞大动漫产业的基石。成名之后的宫崎骏这样勾勒动画师的群像:“平均年龄都很轻”“特征是善良和贫穷”“大多数人是按件计酬”“有人甚至无力投保国民年金和健康保险”。
具体到年轻的宫崎骏,起步月薪只有1.95万日元,蜗居在东京都练马区一间“四贴半”的公寓,约等于7平方米,是日式房间的最小极限,月租6000日元。他自嘲:“每当动画师聚在一起,总是不外乎要冒出‘我看我转行算了!’或‘没有别的好工作了吗?’这种话。”可是他并不打算放弃,“回想起我们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刚走进动画这一行,既没有职业生涯的保障,也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没有钱,甚至也没有才能。我们有的只是野心,或者说是希望,在各行各业中,仅仅凭借着它来奋斗的,唯独动画而已。”
他太想创作出“只属于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大家从心中感受到快乐”的作品,以此回应母亲对他人生的希冀。而他唯一的资本,只有1963年入行以来累积的职业历练。终于,《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到来了。宫崎骏不仅担任导演,还负责脚本和分镜。他用110分钟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怪盗鲁邦捣毁了野心家的假钞基地,拯救了被困的公主,找出了隐藏的宝藏,然后继续与警探猫捉老鼠般的刺激逃亡。
30多年前的片子,现在重看,那种幽默、轻快和奇思妙想,依旧能让人会心一笑。影片开场的几段追车戏,据说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被斯皮尔伯格赞誉为“电影历史上最完美的追车戏”。这部动画长片,以独特的风格获得了影评家们的青睐,摘取了日本动画界一流的奖项——大藤信郎奖。30年之后,宫崎骏凭借《悬崖上的金鱼姬》第二次赢得这个奖项。

《悬崖上的金鱼姬》
可是,影评人并不能代表市场。70年代末,正逢日本科幻题材兴起,以《宇宙战舰大和号》为代表,机器人和未来时空,成为动漫作品中的主流趣味,牢牢地吸引着媒体和消费者。影院里空荡荡的座位,宣告了宫崎骏处女作的失败,此后3年,他没有接到任何片约。身为动画师的野心和希望,在宫崎骏的不惑之年,遭受重创。
03
“我不是环保人士”
不惑之年的宫崎骏拿着厚厚的画稿,辗转于各个电视台,在业界功利的冷漠里毛遂自荐,“那时就想,自己不能这样烂掉,我就是喜欢动画”。他想讲述的故事,有猞猁与人间公主坠入情网,有森林妖怪大显身手,有空中浮城。这些分别是后来《幽灵公主》《龙猫》和《天空之城》的雏形,只是都与当时的科幻主流格格不入。“题材陈腐,没有票房”,“一股子马粪臭”,他就这样被拒绝、贬低和嫌弃。
宫崎骏的另一位挚友,后来与他在吉卜力共事的金牌制作人铃木敏夫,在这时候出现并施以援手。1981年,铃木敏夫担任了德间书店旗下老牌动画月刊Animaga的总编,在8月号的Animaga推出了第一个宫崎骏特辑。他从《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开始,就很欣赏宫崎骏的才华,他还几番游说,邀请宫崎骏在杂志上刊登连载漫画。日本的漫画家获得声望的方式,都是先从连载漫画开始,作品受到读者追捧,被证明有市场,才有可能被改编为动画,然后获得更大声誉。其实宫崎骏很早就尝试过连载创作,他曾经在《少年少女新闻》杂志上连载原创漫画《沙漠之民》,从1969年9月延续到1970年3月,只是他没有用真名,笔名秋津三朗也被湮没在同期的竞争者中。
1982年2月,宫崎骏的《风之谷》开始在Animaga上连载。故事背景设定在巨大的工业文明毁灭数千年之后,以风之谷公主娜乌西卡为主角,来审视人类与腐海森林的生存对决,这是宫崎骏当时心境的表达。他回忆说:“我当时心里非常焦虑,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感到很生气……环境问题固然令人心急,但问题并非仅止于此,虽然人类该何去何从也令我相当在意,但最大的问题是日本现况。还有,最令人生气的恐怕是自己当时的状况吧。”“我感到丢脸,而且是火冒三丈。”

《风之谷》
这是宫崎骏的背水一战。1984年3月,剧场版《风之谷》公映。影评家野村正昭给《风之谷》打了10分。他写道:“我不想用与《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并列的杰作之类定位,将这部影片局限在动画片的范畴之内,难道在1984年,还可能期待一部在气势上超过《风之谷》,在情感上表现得更丰富的传统日本电影出现吗?”这一次,影评人的赞许终于与市场的认可度合拍了,《风之谷》的观众数量突破了91万人次。《风之谷》甚至被《电影旬报》列为1984年十佳影片的第7位。在此之前,日本动画片排位最高的是1979年的《银河铁道999》,仅列第17位。所以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动画史上,《风之谷》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让动画片赢得了作为电影才能拥有的评价,从而大幅度拓宽了动画片的观众层和观赏年龄层”。
日本动画界也感受到空前的冲击,宫崎骏曾经最喜爱的漫画家,动画界巨擘手冢治虫对《风之谷》没有发表任何评价,一直到他去世之后,担任过他的助理的漫画家石坂启才说了一点猜想:“先生对《风之谷》一定感到十分沮丧,他自己最想用动画去做的事情,却被宫崎骏抢在了前面,我认为先生最想做的,其实就是创作那样的作品。”《风之谷》被动画界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分野,低劣作品在有诚意的佳作面前无地自容,宫崎骏所坚持的动画理念和精益求精的制作方式,成为动画片“正统道路”的代表。
从《风之谷》开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宫崎骏作品中恒久的母题 ;少女与少年,天空与森林,万物有灵,是他“梦境”中最突出的意象。《风之谷》恰合了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环境危机意识和环保热潮,宫崎骏和高畑勋因此都被奉为“环保主义者”,可是宫崎骏自己却说,他讨厌被贴上这种标签:“常有人把我和高畑先生错当成环保人士,以为我们总是用环保意识做主题,以为只要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将之制作成影片。这误会可大了。”
宫崎骏会身体力行地在工作室和居所周围的树林和河川捡拾垃圾,但也仅此而已,他并不觉得自然就那么脆弱,相反,他坚信“大自然拥有无穷的力量,那是一种超越了人类善恶线的巨大力量”。宫崎骏不愿意“关怀绿色,关怀自然”被当成吉卜力的品牌标签,他想“打破那些奇怪的观念”。
在《红猪》之后,他创作了《幽灵公主》,一场森林中凶暴诸神与人类的战争。影片的制作用了4年时间,花了23亿日元,而整个故事的构思酝酿用了16年。宫崎骏以赌上吉卜力的一切、任性地制作最后一部动画长片的心情,在1997年为观众奉上了这部影片。故事里,达达拉城主“黑帽大人”代表的是人类的无所畏惧和对自然的毁坏,狼女小桑代表的是自然诸神对人类的憎恨和报复,而被诅咒的少年阿希达卡代表的是和解,和不管怎样都要努力生存的意志。

《幽灵公主》
这一次,票房与影评之间,又呈现出微妙差异。《幽灵公主》打破了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E.T.》1982年在日本创下的无可撼动的票房地位,上映184天,观众3000万人次,票房收入179亿日元,创下了日本历史上电影的最高纪录。但是影评人却对这种颠覆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电影的主旨和部分画面过于残酷血腥。宫崎骏承认,画面中确实有过于残酷的部分存在,那是因为“凶暴诸神和人类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以喜剧收场的”。他说:“所谓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其实可以用因果报应来形容。”所以,“不能盖上盖子,只挑愉快的部分给大家看。”
04
残花,旧枝头再开放
其实,颠覆一直是宫崎骏对自己创作的设定。“我确实和铃木不断商量交谈而理出了一个防线,那就是一旦观众对吉卜力的作品怀有某种期待,我们就必须在下一次的企划中努力想办法背叛他们。”“所以我不觉得这次有何特别之处,反倒是很清楚地告诉自己,要是把它做成《龙猫2》就完了。”颠覆当然会有风险,宫崎骏也很明白,动画制作也是娱乐业,“所谓娱乐,就是有义务将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但是他也坚持,“以赚钱又安全为前提的电视作品,只会磨损年轻人的人生,根本学不到东西。”
残酷的《幽灵公主》,虽然是对《龙猫》《魔女宅急便》轻快叙事的颠覆,但本质上并没有偏离宫崎骏持之以恒的创作核心,那就是“即使在憎恨和杀戮之中,还是找得到生存的意义,还是存在着美好的邂逅和美丽的事物”。故事的结尾,是典型的宫崎骏式生之礼赞的表达——小桑说:“我喜欢阿希达卡,但是我不能原谅人类。”而阿希达卡回答:“那也可以,那么就和我一起活下去吧。”
在制作《幽灵公主》的时候,宫崎骏觉得,1997年已经是吉卜力的顶点,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力量正达到顶峰,换句话说,是指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力量方面,今后都将慢慢走下坡。”他还是低估了自己。4年之后,2001年7月20日,《千与千寻》在日本公映,本土票房304亿日元,超越了同期上映的《泰坦尼克号》,不仅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还成为唯一一部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动画电影。同年10月,宫崎骏倾心设计打造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也正式开馆。
在电影首映式上,年满60岁的宫崎骏发表了诸多感慨:“身体不如从前是事实,到深夜脑子就自动罢工了,怎么休息也难免有糊涂的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寻找一个可靠的接班人吧。”“我现在才算明白黑泽明当时的心情,在《乱》中安排了李尔王这个角色,不是不想放开手中的权力,而是国王一旦成了老王就难免可笑愚蠢,我只要还有力气、干劲,就会一直制作电影,不知道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我想黑泽明当初的心情一定也是如此复杂。”
《千与千寻》是宫崎骏专门为10岁大的女孩们创作的片子。 他解释说:“这不是一部挥动武器、较量超能力的作品,而应该算是一部描述冒险故事的作品。虽说是冒险,但主题并非正邪对决,而是述说少女因为被丢进了好人和坏人混合存在的世界里,而展开修炼,学习友爱和风险,并发挥智慧让自己得以返回原来世界的故事。她回到原来的世界,并不是因为世间的恶毁灭了,而是因为她获得了生存的力量。”他想要“刺激那些麻木了的知觉,唤醒那沉睡了的创造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不能为了激发孩子的本能,而要他们独自面对种种困难,我相信一部用心制作的电影将是孩子借鉴的好对象”。
故事的主角荻野千寻,乍一看和宫崎骏以前塑造的少女似乎有所不同,她不像娜乌西卡、小月姐妹、魔女琦琦或是狼女小桑,拥有一眼看去就无所畏惧的力量,她的出场并不是活力洋溢,反而有些对世界漠不关心的赌气,她还是个笨拙的爱哭鬼,面对最初的险境惊恐得手足无措。但随着故事的演进,千寻不断成长,最终展现出了宫崎骏挚爱的少女们共同的特质——“拥有不被吞噬的力量”。
这就是宫崎骏想诉说的:“别担心,最终一切都会好的,一定有属于你们的世界。不仅仅是在电影院中,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更想说的是,如果是你,一样做得到哦!”《千与千寻》的制作,和宫崎骏所有的作品一样,也是从分镜脚本开始,反复打磨,随时更改,并不是跟随剧本的逻辑演进,而是跟随他的灵感。
这些闪耀的灵感中,最令宫崎骏满意的,是他对“无脸男”的塑造。 “这个角色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设定好,而是在看到他站在桥边的模样之后才决定的。说老实话,他是硬被我设计成跟踪狂的,听说制作人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到处去跟别人说,那就是宫崎先生的身份,但是,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可怕啊。”这个角色的逐步丰满,让宫崎骏“第一次很有骄傲的感觉”。

《千与千寻》
“我没有把它做成无脸男大闹,破坏了汤屋,然后企图吃掉千寻,而是安排千寻坐上电车,第一次出远门。比起无脸人大闹或者和汤婆婆电光交战,对孩子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坐上电车展开充满期待的旅程。”
《千与千寻》制作结束时,宫崎骏曾独自到神社求签,签文是“残花,旧枝头再开放”。他的理解是:“我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应该力求突破与创新,绝不能为了追求时髦迎合当今的商业需求,那样的事情对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获得蜚声国际的荣耀之后,宫崎骏依旧在坚持创作和颠覆,他之后的两部作品,《哈尔的移动城堡》和《悬崖上的金鱼姬》,虽然也获得了不同的奖项,但是,并没能超越《千与千寻》给观众的震撼。
在《千与千寻》为他赢得荣耀的60岁,宫崎骏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步入老年,眼前仿佛突然打开了一扇门。“门扉的那头并不是清晰可见的笔直道路,而是犹如天与地混在一起、渺茫模糊的灰色世界。尽管回头看是熟悉的世界,却是再也回不去。”他感叹说,“年老,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本来以为将因此变得更加心平气和,谁知道根本是一点都不平和,我努力想让自己变沉稳,却怎么也办不到。 ”
不过,越是这样,反倒越令人确信,宣告退休,只是宫崎骏与身体衰老的妥协方式,毕竟他已经72岁。但退休绝对不是他与挚爱的动画的诀别,只要他还在,只要吉卜力还在,他要通过动画传递的爱和激励,将会一直以其他方式延续。因为,宫崎骏一直就是个倔强的矛盾体。同为动画导演的押井守说,宫崎骏“内心永远充满了冲突,他一方面很希望做出他心中想做的东西,一方面却得考虑他到底能要求其他人做多大的牺牲……他是必须肩负那个重担的人,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再挣扎又挣扎,到现在还不断奋斗着的原因之一”。
这种“矛盾综合体”的个性,也贯穿了宫崎骏的创作生涯。他是娱乐文化的生产者,但他却又对大量消费文化的蓬勃持否定态度;他制作给孩子们看的动画,却又认定孩子们最好不要多看动画,在大自然中才能身心健康;他精益求精地打磨每一部影片,又坚信庞大的消费文化产业最多30年就会崩溃。
他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制作片子时,“绝对不传递这种情绪”,只是“把它停泊在自己的港湾里”。“我觉得成人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孩子们,孩子们完全有能力形成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情绪化的创作者,又是一个对工作室运营琐事无所不至的管理者,被高畑勋戏谑说,“从厕所问题到节省电费几乎是无所不管”。
对于这个世界的诸多想法,一直在宫崎骏心里冲突拉锯。他说:“当我站到众人面前说话,或写文章的时候,我会尽量去芜存菁,尽量积极正向,尽量不将破灭的部分表现出来……我是个在诸如凶残的部分或是愤怒、憎恶之类的情绪部分,都比别人强上一倍的人。明明是个偶尔会陷入失控的危险境地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压抑住这部分,因而甚至被认为是个好人,这和我的真面目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我并不了解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但可以确定,我的内心似乎住着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宫崎骏。”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