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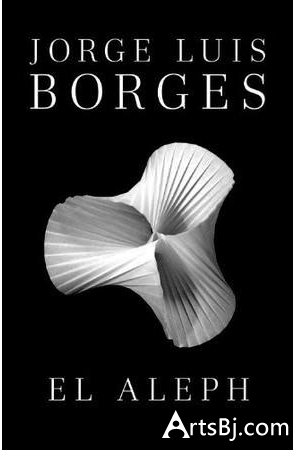
西班牙语版《阿莱夫》
纪念《阿莱夫》“显现”七十周年:1945-2015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在《括号内》中提到他在日内瓦Plainpalais公墓的经历。根据管理员的指示,他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想起卡尔德隆,想起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想起人生的诡异,换句话说就是:我什么都没想。我就看着那墓,石头上刻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名字,生卒年和一行诗。”然后在面对墓石的凳子坐下,就听见一声沙哑的鸦啼。不远处的这一只乌鸦瞬间把他从日内瓦带到了爱伦·坡的诗里。
博尔赫斯已被谈论得太多?即使一一翻阅所有能找到的研究文献,直看到“手指没入漆黑的书页”,就像(博尔赫斯提到过的)克维多笔下的读者,这一点我仍不能确定。十七世纪的一位加泰罗尼亚修辞学家说过,不知从何开始之时,可从第一个字母开始。于是我遵从先贤的指引,不避断章取义的嫌疑,从那部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命名的小说开始。
七十年前问世的《阿莱夫》,奠定了博尔赫斯的光荣地位。《阿莱夫》中统摄万有又包含自身的阿莱夫,已成为博氏诗学的纹章:正如堂吉诃德之于塞万提斯。但作为小说家的博尔赫斯几乎不创造人物,纵然算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那也不过是人形版的阿莱夫而已。初读的时候我曾一度困惑,为何作者用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一位三流诗人及其诗作,即使他是叙事者“博尔赫斯”已死情人的表哥,阿莱夫的“发现者”——就像哥伦布是美洲的“发现者”。他名叫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Carlos Argentino Daneri),这个近似漫画式的人物背后暗藏着一段拉美文学外史。
包括哈罗德·布鲁姆在内的评论家都认定达内里是对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戏仿。努涅斯-法拉科将他看作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投影,同时也是博尔赫斯对其早年“极端主义”诗学的自我嘲讽。但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意大利学者,在达内里身上看到了诗人但丁的变体:Daneri (达内里)= 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利吉耶里)。而阿亨蒂诺(Argentino)在西语中意为“阿根廷人”或“阿根廷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一位阿根廷的(反)但丁。他的野心是写一部以本行星为对象的长诗,题为《大千世界》(La Tierra,直译即“地球”),恰好是《神曲》的对置镜像:“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九月十一日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为了达成这一伟业,加拉伊街老宅地下室角落里的那个阿莱夫必不可少,尽管“包罗万象的一点”对他来说只是“了不起的观察站”:诗人从阿莱夫中观看世界,并把看到的部分复制到诗里。如果有读者在达内里的写作模式中发现某种机械模仿论的现实主义,似乎也不算离谱。胡里奥·奥尔特加曾饶有意味地将闪耀在边缘地带(地下室第十九级台阶:远离社交空间、光与暗的交界),以字母表首位命名的阿莱夫视为文学的象征,并从中推演出两种诗学:像达内里一样将文学作为考察-反映世界的工具,或者像那一刻被阿莱夫迷住的“博尔赫斯”,关注-审视(作为实存和行动的)文学本身。
博尔赫斯的魅力或许正在于,他试图证明文学是世界的一部分,且同时包含世界:“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肺腑,看到你的脸……”
直到这一刻才发现,我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读者的脸,都已经被叙述者“博尔赫斯”和小说作者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同时看见——看见我正在读《阿莱夫》的脸。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一发现几乎没有不安的感觉,就是博尔赫斯在《堂吉诃德的部分魔法》结尾解释的那种不安:“堂吉诃德成为《堂吉诃德》的读者,哈姆雷特成为《哈姆雷特》的观众,为什么使我们感到不安?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或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
将《阿莱夫》与《神曲》相提并论的研究者们并未忽略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前者是以贝雅特丽齐的死开篇。奥尔特加认为这象征着《阿莱夫》中的世界是衰减的世界,正如达内里的长诗是《神曲》的苍白衰减版。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了文学自身的仓皇失所:一边是“阿根廷的但丁”达里内的无味作品在诗歌大赛折桂,一边是阿莱夫栖居的地下室因咖啡馆扩建而被拆。我不会贸然试图在我们的时代与《阿莱夫》的衰减世界间建立联系,借以解释上述不安感的消失。同样我也并不确定,如果博尔赫斯不再让我们不安,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或许说明这时代已经有了新的贝雅特丽齐,或许阿莱夫已经规模量产。
在小说后记中,“博尔赫斯”断言“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假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出于竞争落选者在旁征博引后隐藏的沮丧和嫉妒。直到后来下面的想法令我豁然开朗:与奥尔特加的解读方向不同——他认为既然充当了文学的象征,“加拉伊街的阿莱夫”必然为“假”(falso)/ 虚构(ficción);而我倒是觉得,小说人物“博尔赫斯”所见的“阿莱夫”之所以是“假的”,正因为小说作者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文本才是真正的阿莱夫:如果运气够好,我或许能在其中看到世界和“你的脸”。博尔赫斯的面孔。
阅读博尔赫斯的“利弊”
博尔赫斯自称是享乐主义读者。何塞·米盖尔·奥维多在他著名的《西语美洲文学史》(第四卷)中说,如果作者的伟大是以读者从中获得的阅读愉悦来衡量,那么博尔赫斯无疑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不知道博尔赫斯自己会不会同意。他应该会说,这不是一个他感兴趣的主题。
我目前读过的最令人愉悦的博尔赫斯指南,是奥古斯都·蒙特罗索写的。在墨西哥城某个不起眼的小书店,我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这本全是苍蝇的小书《永恒运动》(Joaquín Mortiz出版社1972年初版)——书中收集了许多关于苍蝇的名人名言,而且从封面到插图也是同一主题。不过现在要说的是书里那一篇疑似指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利与害》。蒙特罗索结合个人的阅读经历肯定了这位阿根廷作家对西班牙语的贡献,他说自己这一代人在读到博尔赫斯之前大都已对母语绝望,没想到有人竟能让她死里复活,面貌一新。另外博尔赫斯善于制造惊异(古罗马伟大的昆体良的教诲),但不像卡夫卡从开篇就让甲虫出现,而是善于将读者引入其彀中而不自知。模仿博尔赫斯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但注定徒劳无功。因为博尔赫斯和乔伊斯一样,都是不可能模仿的:因为太容易也太明显了。
最后他列举了十条与博尔赫斯相遇的可能后果并作出评估:
1.从他身边经过而毫无察觉(有害)。
2.从他身边经过,返回并跟了他一段路看看他在干什么(有利)。
3.从他身边经过,返回并从此跟随他(有害)。
4.发现自己是傻瓜,迄今为止从未冒出过任何有价值的想法(有利)。
5.发现自己很聪明,因为喜欢博尔赫斯(有利)。
6.……(有害)。
7.……(有利)。
8.……(有利)。
9.……(有害)。
10.不再写作(有利)。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