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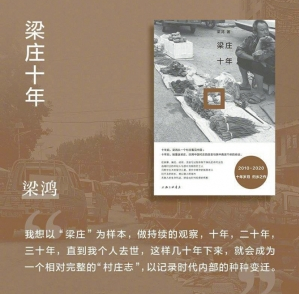
《梁庄十年》
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疫情肆虐,促人警醒,珍惜生命之珍贵。作家梁鸿也不例外,“突然间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丝表情,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悲痛,都让人感到特别珍贵。”在人大教书的梁鸿,平均每年要从北京回家两到三次,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在河南邓州市穰东镇梁庄村走访各处各家。父亲过世后,轮到姐姐们和闺蜜陪着她。疫情不那么紧张时,梁鸿又一次回梁庄。
重新审视故土的冲动
走到梁庄村庄路口的红伟家,看到曾经在《中国在梁庄》里写过的五奶奶,又在那儿跟大家一块说笑,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喝茶,有的还在田里干活儿,“我觉得太珍惜了,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一个个人的表情,一个个人的面容的热爱。”
此情此景,让梁鸿有了再写梁庄的冲动。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的故事。一个中国平凡村庄里的人与事,那些流落在外的梁庄人,他们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让很多读者共鸣,唤起自己对家乡的记忆。“梁庄”也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圈的一个标识性的存在。
10年后,梁鸿再次运用“非虚构”的文学方式,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也将当下的梁庄,重新带回读者的视野。2021年1月,《梁庄十年》由理想国策划出版。10年时间,梁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梁庄人也各自迎来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在这本新书中,我们跟着梁鸿的眼光,可以看见,10年之间,梁庄的村民们有哪些变化,流经梁庄的湍河,又出现了哪些新样貌。
梁庄的女儿都去哪了
在写《梁庄十年》时,梁鸿突然意识到,此前自己笔下的梁庄人,如果是男人们,这些男人就有名有姓。无论走多远,过年总会回到村庄里。但村庄中的女性,过年要跟随丈夫去到婆家的村庄,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惯性。她写梁庄的哪一个媳妇,写哪一个奶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她们叫什么名字,就好像她们作为少女时的那个女孩子从来不存在一样。她到了梁庄,就变成了‘某某家的’,就变成了几婶,就变成了几嫂,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也在无形中把女性的某一部分主体抹掉了。这是我突然意识到的。”这也给梁鸿一个非常大的起念:找一找梁庄那些失去的女孩子。梁庄丢失的女儿,她们都到哪儿去了?
在《梁庄十年》第二章,梁鸿集中书写了“梁庄女孩”们的故事。被抱养的女孩燕子,长大后变成了让“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的少女,可被村里男青年们的疯狂追求吓坏了,以至于耽误了学业;同样美得耀眼的春静,一次恋爱没谈过,当年却被指责“风流”,背负着骂名……在梁鸿北京的家中,燕子、春静、小玉,四位“梁庄女孩”的相聚,是全书最值得关注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在梁鸿的书房里聊天、席地而眠,彼此袒露心迹,诚实叙说伤痕。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受歧视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最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还特别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梁鸿说。
十年返乡在场的观察
有好几年,与春节拜年短信轰炸相伴随的,是各种学者或者博士“返乡文”的轮番刷屏。与这些乡村调查作品不同,梁鸿对梁庄的书写,虽然也有她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外部观察视角,但更多的是,看到梁鸿作为一个梁庄人,与当下依然在梁庄生活的亲邻们真实的内部互动。也就是说,梁鸿虽然也是观察者、思考者,但她更是参与者、在场者。她是后辈口中的“梁姑”“清姐”,是长辈在路上认出来的“光正家的闺女小清”。她将自己隐没在梁庄儿女众生相中。看到瑞雪刚走春风又至的梁庄,看到生老病死看到“湍水有鱼”,十年梁庄的人事变迁、现实与人心的风景,尽收眼底。“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梁鸿说。
梁鸿是在写梁庄,但又不仅仅在写梁庄。梁鸿的目光所及、关切所在,是在时代浪潮正经历变动之中的中国村庄。这些村庄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想到此,梁鸿有点激动,“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对话:梁庄是一个生命体 它一直在变化、在生长
记者:比起此前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显得更有感性的文学气息,朴素的情感气味更浓。很多片段,其实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情节显得比较戏剧化。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中,加入了小说的写法技艺,让非虚构写作,也带上了虚构文学的表达魅力。我能看到你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内所进行的开拓性努力。
梁鸿:的确如此。其实,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是,在表达事实层面时,可以在表达方式上,进行适当的表达方式创新。描述一个事物,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在可见的和不可见之间,把握好一个平衡。非虚构的边界和更多可能性,我一直在思考。这一次,我也想试试,通过《梁庄十年》这个作品来实践一下。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如何把故事讲得更有魅力,在文体上进行一些实验和探索,都是分内的事情。非虚构写作是文学,是作品,而文学就是要在表达上做到更有魅力。
记者:梁庄成了你写作的一大源头。你对梁庄的写作,是“进行时”。一直关注着梁庄的当下。所以你也应该不会担心,把梁庄写穷尽了。
梁鸿:对。其实我们很难穷尽一个事物。更何况梁庄是一个生命体、有机体,一直在变化,在生长。包括我自己,随着年龄,认知的变化,我对梁庄的观察和思考也不同。
记者:你说自己对梁庄的爱,“兜不住,要溢出来”。这种溢出的爱,表达出来,表达好,就是文学,就是作品。这种爱,能一直鲜活,应该也是跟梁庄一直给你带来精神营养有关?
梁鸿:是的。我和梁庄的关系,现在已变成像一个孩子和自己家庭的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爱,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容,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这些共同组成了深刻的爱。
记者:从你的描写,采访你的纪录片中,都能看到你的家乡梁庄,总体来说,还是生机勃勃的。2020年夏天,我看到你也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感到在城市里感觉不到的舒适?
梁鸿:是的。总体来说,乡村生活比起城市来说更具弹性。比如这次的疫情十分影响城市的生活,但对像梁庄这样的村庄的内部发展反而没有过大的影响:农民干的活儿大部分都是零工,工厂不开工,就在家里;开工了,就回去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感觉;但在城市里,工作的停滞、房贷的持续……这些都会令人在疫情中变得艰难。而且,在乡下,能感受到开阔感,是很大的治愈的力量。
记者:近些年,农村空巢化让不少人感伤。很多村里面没什么年轻人了,都出去打工了。你是怎样的感受和思考?
梁鸿:每次回到梁庄,看到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中年人,或者很小的小孩子,让人觉得这个村庄有某些缺陷。但我会注意,不让自己陷入悲伤的情绪,并且努力看得宽阔一些。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