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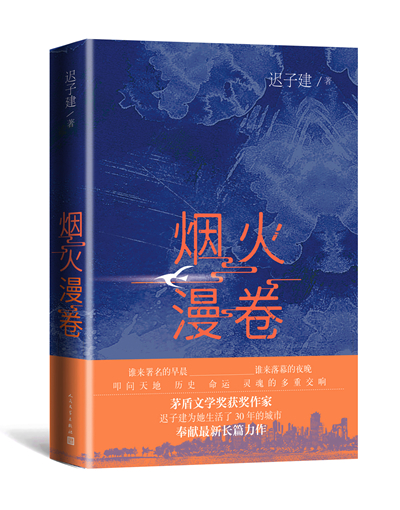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的生灵——这是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中要讲述的故事。每个作家都在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哈尔滨”是迟子建笔下继“北极村”之后第二个精神家园。
迟子建出生于漠河北极村,听上去就是一个适合作家的地方:神秘、清冷。大概因为身处北极村,方向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迟子建在哈尔滨第一次搬家时,朋友们帮她搬完,大家一起喝了点儿小酒,喝完她就找不到家了。30年前还没有手机,迟子建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问一个帮她搬家的朋友,“我家在哪里”;朋友也是她同道中人,“你家在一个绿色的垃圾桶旁边”。
迟子建在北极村长大,17岁求学才离开大兴安岭到了山外,1990年来到哈尔滨,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活至今。初到哈尔滨,她的写作与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它的居民,更像是个过客,她倾情写的还是心心念念的故乡。
慢慢地,当她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感情在升温,也就有了表达的欲望。从早期的《伪满洲国》,到后来的《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再到这部《烟火漫卷》。
在完成《群山之巅》后,迟子建便有了《烟火漫卷》的创作计划。
2019年4月正式动笔,写完开头两章,因为访欧而中断了一段时间。然而,在远离哈尔滨的旅途中,小说中的人和事反而更加洗练鲜明。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迟子建也能找到哈尔滨的影子;而当她真正回到哈尔滨,这座城市重新带给她愉悦和安宁。
对城市的聚焦,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将城市生活作为小说的焦点,对她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说,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多年以后,一定有责任和义务写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每个作家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当你觉得一个题材培养成熟以后,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从容驾驭它”。
写作期间,写累了,迟子建就会停一两天,乘公交车或者地铁,在城区间穿行。她起大早去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们,到凌晨的哈达果蔬批发市场去看交易情况,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旧货市场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欢迎,当然,还去新闻电影院看二人转,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演出……凡是作品里涉及的地方,哪怕是一笔带过,她都要去触摸一下它的门——人世间最盛的烟火,可以说全在作品里了。
迟子建:“我喜欢烟火人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一定写到我小说当中,但是我不经意这样走过的时候,就感染了这种人间烟火气。”
我们也许无法亲见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黄昏,漫卷城市的,不止烟火,还有无数散发着蓬勃生气的生命。
在《烟火漫卷》中,生活在哈尔滨的人物,每一个都自有来处,又往归处。但无论是已经融为历史背影的犹太人谢普莲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还是沉迹于普通人生活的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在经历了生命伤痛之后,仍然“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别夜晚”。
有读者问,书中有没有外卖小哥这样的普通人?迟子建回答:“上部‘谁来署名的早晨’中,谁起得更早、早于日出之前的人,其中就有外卖员。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应该关注的、最湿润的人间烟火。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群体,跟他们休戚相关。”
而朋友们眼中的迟子建是什么样的?
上世纪80年代,李敬泽刚从北大毕业,是《小说选刊》的一个年轻编辑,作为一个满怀惊喜的读者,给当时出版了《北极村童话》的迟子建写信,抬头是“迟子建同志”。30多年过去了,李敬泽觉得迟子建身上有一直不变的东西,“那种温暖、明亮,对人依然怀着一种天真的眼光”。
格非认识迟子建35年,是那种“随时可以抓起电话分享读书心得、甚至人生看法”的朋友。格非印象最深的是迟子建每次给他打电话,声音都十分爽朗,“把我耳膜都要震下来”。
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20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迟子建说:“尤其我经历过个人的创痛以后,我觉得命运可以让两个特别相爱的人离散,可是命运不会让你和你的笔分离。只要我有呼吸,这支笔会陪伴我一直走下去,是它滋养了我。我希望有一天,这支笔陪伴着我,和我的白发一样,能让我的作品,真正经过岁月的洗礼以后,能够闪光。”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