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神话中有关死神桑纳托斯的传说入手,分析了海勒小说中死亡这一层“黑色性”内涵,揭示了黑色幽默小说之“黑”以及幽默媒介如何对其进行传达。与此同时,海勒小说中还蕴含了“再生”的神话元素,在“黑色”之中指出了潜在的光明之所。正因如此,在众多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中,海勒的“黑色”与众不同地让读者感受到了未来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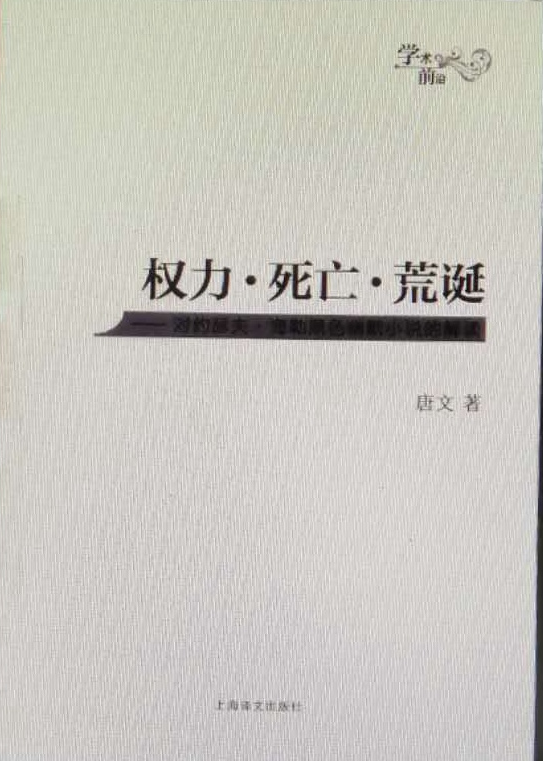
1.1. 死亡和再生
黑色,本身就蕴含了死亡的意味,它自然成为黑色幽默小说家阐释的重点之一。事实上,在黑色幽默小说中,死亡主题占有核心地位,大部分小说情节都围绕着某一死亡展开,而其它情节都是作为死亡的后续事件出现的。因此,和传统小说不同,黑色幽默小说中的死亡是故事的开端而不是结局。正如汤玛斯·利克莱尔说的,死亡是“行为的原因”,而不是黑色幽默的结果。(“Death and Black Humor” 37)如果死亡的结局变成故事的开端,那是什么代替了传统的死亡场景,而成为故事的结局呢?一般说来,小说以死亡为故事的开端,可能导致两种结局,即死亡和再生。接连的死亡是虚无主义,而死后的重生则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死亡或者再生的结局,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综合看来,海勒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否则的话,约塞连不会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叛逃,斯洛克姆不会如此痛苦地在两个世界之间挣扎,戈尔德不会最终与历史和过去妥协,而大卫王也不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如此地恐惧,等等。很明显,和大多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不同,海勒的作品包含了对未来的信仰,相信在死亡的另一头还有再生的存在。
时间的“滴”“答”声此起彼伏,不断地重复下去,构建了人类生存的时空。一方面,“答”声是“滴”声的应答,作品中的终结感让读者感受到了时间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如果作品以死亡为叙事的开端,那么总有另一“滴”声与之对应,这个“滴”声便包含了再生的意味。谈及死亡和再生的关系,罗伯特·利夫顿提出,“再生的意象……是死亡意象的对立面。两种意象具有共生性”(LIfton and Olson 136)。利夫顿认为,死亡和再生形影不离,它们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缺少任一个整体将不复存在,否认任一个也会抹杀了另一个的意义。“滴”“答”声彼此相应,连续不断,声声入耳,共同见证了人类的生命历程。“滴”声作为前一“答”声的回应,带有再生的意味,给人以生命持续不断的信心和希望。也就是说,如果终结感让读者接收到“答”声,那么应该有另一个“滴”声来补充说明这一“答”声的意义。因此,再生补充说明了死亡的意义,没有再生,死亡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意识总是指向未来,用想象构建未来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从人类的视角看去,没有未来的世界是虚无的,正如芬格莱特所描述的,“因为生存的本质就是向未来发展。没有未来,意味着看不见的鬼魂,黑暗中的声音,对难以想象事物的不可知、无法触碰、模糊的恐惧”(71)。感知到未来的希望,人类才能够理解死亡的真正意义,才能够拥有延续生命的信心以及克服死亡恐惧的勇气。如此看来,生命还会继续下去,这成为人类接受死亡事实、理解死亡意义的必要条件。
在海勒的小说中,《画画这个》的结尾尤为凄凉,主要人物在小说结束前全部死去,就连人类生存的时空意义都被否定。然而,在这种悲凉的氛围之中,苏格拉底之死仍然给读者留一下了一丝“活下去”的希望。海勒之所以在小说结束前描述苏格拉底的死亡,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苏格拉底坚信,他是为了维护信仰而牺牲,因此肉体的消亡换来的是精神的永生,自己会以“大我”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另一方面,临死前,苏格拉底的身边围满了学生,他相信学生会是维系自己信仰的重要媒介,因此在他眼中,学生成为他生命的延续。当克里斯多询问老师的遗愿时,苏格拉底回答到,“照料好自己,按照我所教授的方式去生活,你就是在为我做事,为所有的我们做事”(345)。由此看来,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自信生命会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他的信仰也会永远被维系下去。通过肉体的消亡,苏格拉底反而获取了精神的再生。凄凉如《画画这个》仍然含有“活下去”的希望,何况最能体现海勒创作风格和文学主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小说表面描述的是一幅令人绝望的荒原图:约塞连所有的朋友都死去,在战争中阵亡、或消失、或被消失,在39章更是描绘了死寂的人间地狱罗马。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在小说中安插了为数不少的再生符号象征,这些再生符号为故事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表面死寂的小说时时闪现生的希望。
再生的意象隐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例如,“白色士兵”(the soldier in white)的形象就包含了再生的意味。表面看来,白色士兵好像死神一般,每次出现都会带来死亡和不幸。第一章中,海勒这样描述白色士兵:他“全身上下都裹着石膏和纱布,双腿双臂已全无用处”(6)。这个形象异常滑稽,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埃及木乃伊的样子。根据埃及的文化习俗,之所以将死者做成木乃伊,是为了等灵魂复苏之后,他可以继续使用保存下来的躯体。因此,形似木乃伊,实际为白色士兵的形象增加了一丝再生的意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三个部分都是以白色士兵的出现为开始标志。随着三个部分故事情节的逐渐深入,约塞连最终下定决心叛逃。因此,白色士兵的每次出现,都暗示了约塞连对周边环境进一步的了解,促使他最终踏上了叛逃之路。从这层含义上,可以说白色士兵对整个故事具有强大的再生力量的。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研究:往返两次》中,乔恩·伍德森就提出了白色士兵形象的再生意味。他认为,白色士兵实际象征了埃及神话中的地狱之神奥西里斯,能够让“死者接收到他们的永生”(19)。除了白色士兵,伍德森还谈到了小说中的另一个再生意象:消失在云端的克莱文杰。他特别的死亡方式,让读者联想到公元前九世纪生活在以色列的先知预言家伊利亚。传说中,伊利亚在让死者复活后,将火种带到人间,然后飞升入天堂。克莱文杰消失在云端,与伊利亚升入天堂十分相似,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克莱文杰的死亡也促进了约塞连符号意义上的再生,即他的最终叛逃。
小说中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特形似玛雅文化中的谷神形象,同样也具有深刻的再生意味。首先,海勒对哈尔福特外表的描述突出了两个特点:长相英俊和“一头蓬乱的头发”(45),而玛雅文化中的谷神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头发像谷穗一样凌乱”(Hammond 281)。另外,谷神是主管农耕的神,而哈尔福特手中的黑麦酒,暗示他与农作物的密切关系。其次,在玛雅传说中,谷神会在冬季被斩首而死,但下一个春季又会复活。这样的死亡有两个含义:“为了死亡,也是为了稻米的丰收”(McKillop 218)。小说中,神秘的直觉让哈尔福特意识到,他将会在冬季死于肺炎。当冬季真的来临时,“直觉告诉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特,他的死期就要到了”(391),而这和谷神的生命轨迹恰巧重合了。最后,哈尔福特在小说中的登场和谢幕,都是小说中生命轮回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尔福特是为了接替战死的库姆斯中尉而被派到皮亚诺萨岛,因此是库姆斯再生的符号象征。之后,看到弗卢姆上尉性格的改变,哈尔福特“很自豪地视这个新的弗卢姆上尉为自己创作的作品”(61)。当哈尔福特最终搬到医院等死的时候,弗卢姆从丛林中搬回了以前的帐篷里,俨然替代了即将死去的哈尔福特,成为他的再生符号。再有,等哈尔福特果真在医院里死于肺炎,内特利又主动请缨替代了哈尔福特的战斗职位,成为他的另一个再生的符号象征。因此,哈尔福特的出现总是作为从死到生的生命轮回的组成部分,他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再生意味。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所有人物中,奥尔对约塞连的成长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深入,小说的基调逐渐黑暗阴沉,直到最后几页奥尔的名字再次出现,瞬间扭转了故事的整个基调。在这之前,约塞连陷入绝望的泥淖之中。他在游历了死亡之城罗马后,冲动之下接受了卡斯卡特上校的协约,之后被内特利女孩砍伤住院。灵魂被出卖,肉体受创伤,约塞连开始对能否“活下去”产生疑惑。就在这个时候,牧师带来了奥尔的消息: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牧师可着嗓门嚷嚷着冲进门来。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关于奥尔的。他又高兴又激动,有那么一两分钟连话都说不成句了。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喜悦的泪花。当约塞连终于听明白牧师的话时,他不敢相信地大叫一声,抬腿从床上跳了下来。
在引文中,海勒用了一个句子便扭转了小说的基调,奥尔的消息一扫灰暗的阴霾,为约塞连指明了道路,也为小说顺利完结做好了准备。奥尔叛逃的消息让约塞连意识到,除了“生存,还是死亡”的选项,还有另外一个颠覆一切、寻找出路的办法——叛逃。直到这时,约塞连才意识到,奥尔实际上曾经多次向他暗示一起逃跑。可惜的是,约塞连并没有明白奥尔的真正意图,错失了逃跑的机会。最终,在奥尔叛逃消息的鼓舞下,约塞连踏上了逃亡之路。从名字上看,奥尔(Orr-or)实际上就是暗示了另一个选择的意味。在希伯来语中,奥尔的名字还含有“光明”的意思。既然奥尔为约塞连指明了最终的出路,那么将他成为促使约塞连再生的生命之光,是实至名归的。由此看来,海勒有意将奥尔的事情安插在小说的最后,用其打破约塞连所处的僵局,再次点亮了约塞连的未来之路,顺理成章地将小说结尾呈献给了读者。
尽管海勒最后才将奥尔的谜底打破,实际上小说中多处细节都暗示,奥尔最后会走上叛逃之路。首先,奥尔的生活习惯,预示了他最终的叛逃。奥尔热爱美好的生活,他的房间总是温馨惬意地,这与外面冰冷阴暗的战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例如,在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寒冷的冬季冰冻住了一切,这时与约塞连同住的奥尔却搭建了一顶温暖的帐篷——“多亏了与他同居的奥尔,他才有幸住进这间全中队最舒适的帐篷”(14)。奥尔想尽一切办法,努力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他在帐篷里暗转勾勒自来水龙头、烧木头的壁炉、甚至水泥地板,等等。夏天的时候,有心的奥尔还会“卷起帐篷侧帘,透些许清风”(15)。其次,奥尔有意在飞行中被击落,以此来为最终的叛逃做准备。在博洛尼亚第一次飞行时,奥尔的飞机被击落,他是抱住引擎才活了下来。然后在阿维尼翁第二次飞行任务中,奥尔又一次被击落。这一次,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在其中自得其乐:漂浮在海中的小木筏上,奥尔为同机的伙伴捧上热巧克力和热茶,他甚至还钓到了鳕鱼,做成了美味的大餐。之后,奥尔在博洛尼亚第二次飞行时又被击落,而后他坐着木筏消失在海洋的深处。故事进行到这里,有关奥尔的信息戛然而止。直到故事最后,随军牧师告诉约塞连,奥尔坐着一只黄色木筏漂到了瑞典。当一切谜底被解开,奥尔的形象十分鲜明:海洋深处的黄色木筏上一个小小的士兵,孤独却开心地漂往希望之地。有关木筏的意象,评论家莫得·博德金在《诗歌中的原型》中有专门的研究。为了阐释木筏的含义,他提到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军官的梦境:
他梦到自己和一群人乘坐轮船。他突然站在轮船的一侧,并只身投入大海中。他愈往下沉,愈发现海水变得温暖起来。最后他转过身来,开始往海面游。当他到达海面的时候,他的头几乎碰到了一直空空的小船。轮船消失了,只有一只小舟。(61)
博德金解释说,军官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梦境,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总想拥有一些私人空间。在符号意义上,大轮船以及乘客象征着集体,而无人乘坐的小舟则代表着个人。在跳离轮船游向小船的过程中,做梦者经历了从死亡到再生的历程:从致命的群体到存活下来的个人。水越温暖,存活的机会就越大。在针对小舟意象的研究中,博德金主要强调了两点。其一,梦中的环境的改变,主要是由集体空间转为私人空间。其二,改变的方向是由死亡到再生:大轮船代表死亡,而小舟则代表着生存。奥尔的木筏从皮亚诺萨岛出发,逃离了死亡的战争,驶向希望的彼岸。如果第256飞行中队是集体空间,那么奥尔的木筏则代表了私人空间;如果战争带来了死亡,那么叛逃理应通往希望。总而言之,海勒非但不是虚无主义者,他的创作理念中还蕴含对未来和希望的深刻信仰。正是这样一个乐观的黑色幽默小说家,创作了约塞连这样一个敢于挑战荒诞的西西弗形象。
在海勒的小说中,含有“再生”意味的场景都出现在死亡之后,死亡场景之后才有了再生的希望。。利夫顿在讨论再生问题时,就多次强调了死亡的意义,“所有的宗教,都教人如何利用时间和死亡调整自我。调整后的自我就是灵魂的再生,但这必须要有一个发生过的死亡场景为前提”(Lifton and Olson 72)。一般说来,海勒都会将主要的死亡场景放在小说的最后,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经历过长久的磨难之后,主人公最终通过死亡的媒介获得符号意义上的再生。这种再生,常常以主人公寻觅自我认知的形式出现。例如,约塞连就是经历了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才获取了“再生”,晋身为荒诞英雄。小说中,桑纳托斯的魔抓最终抓住了约塞连,内特利的女孩“一刀砍在他扬起的那只胳膊下面的腰上。约塞连尖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他看到那女人又举刀朝他砍下来,便惊骇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十二条军规》 484)。昏迷之中,约塞连遭遇到了死神,并由此获得了斯诺登死亡的秘密。濒死的经历,开启了约塞连新生的历程,为了寻觅“自我”的意义,最终决定叛逃瑞典。很明显,没有濒死的经验,约塞连不会获得象征性的再生。同样地,《出事了》中斯洛克姆的再生也是从死亡中获取的。不同的是,这一死亡不再和斯洛克姆自身相关,而是儿子的死亡。
上文提到,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斯洛克姆逐渐分裂为两个自我。世俗成人的自我和纯真孩童的自我不断斗争,令斯洛克姆痛苦不已。饱受煎熬的斯洛克姆不堪折磨,站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岌岌可危,这在他逐渐语无伦次的自白中可以看出。例如,他在感叹面对岁月束手无策之际,突然就失去了逻辑能力,“我不想活过85岁,我不想在186岁前死去”(Something Happened 561)。除了结束两个自我的争斗,斯洛克姆根本没有办法摆脱困境。他非常清楚,如果必须除掉其中一个,牺牲的只能是孩童的纯真。在斯洛克姆看来,心爱的儿子就是内心那个纯真的孩童。因为儿子的死亡象征着纯真自我的消亡,所以斯洛克姆杀死儿子的念头逐渐明朗。随着纯真自我的消亡,成人世俗的占了主导地位,斯洛克姆由此获得了言行上的统一,从而摆脱困境获得新生。在解决了两个自我的争斗之后,斯洛克姆心满意足地看到事业和家庭均有了起色:他得到了卡格尔的职位,并再次赢得了家人的信任。他总结到,“没人知道,勇敢地坚持下去是最简单的事情”(565)。死亡是最残忍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这样斯洛克姆决绝地牺牲了纯真的自我和心爱的孩子,终于回归了盼望已久的平和。但儿子的死亡,并没有终结他内心对纯真之美的渴求。某种意义上,杀死儿子能够隐藏珍爱却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纯真,但这种隐藏并不是抹杀,而是将其深深隐藏在了意识的深处。
故事快结尾时,斯洛克姆对儿子的憎恨与日俱增。儿子内心起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粘着他,这让父亲感到无比地痛心。斯洛克姆说到,“他(儿子)轻轻地咧嘴笑了笑,表示自己已经明白。转身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561)斯洛克姆害怕关着的房门,更恐惧纯真温顺的儿子真地会慢慢离他远去。渴望永久地保存那纯真的形象,他除了杀戮别无选择。杀死了儿子,父亲就可以永久地留住纯真,因为死亡挽留住了正在逝去的美丽。弗洛伊德曾经就美的事物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正是由于“稍纵即逝”(transitoriness),美的事物才会变得更美好:
悲观的诗人认为,美的事物稍纵即逝,转而失去了价值。我对此表示疑问。相反——稍纵即逝使其更加美丽!稍纵即逝的意义在于,在时空的限定内它总是匮乏的。正因为享有美丽的机遇不可多得,美丽才显得弥足珍贵……在我们的生命中,美丽的肉体和容颜总会逝去,然而正是存在的短暂性使其更具魅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杀戮的行为不仅没有终结儿子代表的完美价值观,反而在时空的秩序上将这种美好冷冻并永存。儿子的生命已然结束,但他的美好却存留下来。斯洛克姆分裂的自我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世俗自我获胜,斯洛克姆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另一方面,被驱散的自我之美悄悄转移到世俗自我之中,斯洛克姆因而变得更加成熟和复杂。这样看来,尽管杀死儿子是残忍地,但是对斯洛克姆的新生却是必不可少的。总之,死亡是再生的必要前提,已死之物增加了新生事物本身的价值和复杂性。
在海勒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再生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从死亡中获得了生命的新体验,并由此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新认知。芬格莱特认为,从死亡中获取的新视角属于再生的范畴,“随着视角的增加,我的生存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矛盾的,但却增加了生命的乐趣和素材。”(87)这种新获取的生命视角可以被看做是符号象征意义上的再生。有些评论家批评海勒小说结尾突兀、不自然,但是考虑到在死亡之后紧跟的再生环节,这些批评的言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上文提到过,在海勒的小说中,死亡都是作为中心事件呈现的,它并不会发生在主人公身上,但却会深深地影响到主人公的人生。这种影响,实际上就是从他人死亡中获取的符号再生。下面将再以《像戈尔德一样好》中的布鲁斯·戈尔德为例加以说明。
按照惯例,海勒在小说的结尾处安排了一幕反高潮的剧情。戈尔德最终参加了政府晚宴,按计划将在那里见到总统,并以此为起点真正地开始“辉煌”的政治生涯。然而,命运女神从来不眷顾戈尔德。哥哥希德死于心脏病的消息突然传来,因而在没有见到总统之前他就必须得离开了。希德死之前,戈尔德总是梦想进入政坛,“洗清”自己的犹太身份。当他百般周折费看到希望之时,希德的死像晴天霹雳一样将他惊醒。离开晚宴,戈尔德的车子和总统乘坐的车子擦肩而过。看到这一幕,他觉得万念俱灰,不禁感叹道:“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Good as Gold 472)。事实上,哥哥的葬礼改变了一切。在葬礼上,整个家族分裂为两个派别,而戈尔德则充当了他们之间的和事老。“无数责任的重担都落到了戈尔德身上”(474)。只有这个时候,戈尔德才了解到哥哥生前的责任和压力,从而真切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然后他就爆发了,大声地喊了出来:
“希德,你这个混蛋——为什么你必须得死?从今往后谁来照顾我们?”
没有人听到戈尔德的话。他的言语也被湮灭在自己的啜泣声中。(475)
希德的死亡和葬礼,赋予戈尔德新的生命视角,正是因此他才获得了“再生”。扔掉虚幻的政治梦想,戈尔德回归到家庭生活之中,重新拾起他曾经鄙夷的大学老师的工作。
希德的死亡,使戈尔德回归于真实的生活之中。然而,正如《出事了》中斯洛克姆杀死儿子也不能抹杀对纯真的向往,戈尔德的内心仍然充满着对在政坛叱咤风云的梦想。尽管已经获得了与现实生活环境相符的象征性的再生,但戈尔德并没有彻底忘却政治梦想。斯洛克姆和戈尔德的生活矛盾,实际就是难解的克尔凯郭尔生存困境。追根究底,这种矛盾是由生活的荒诞性引起的。贝克在谈论再生主题时,曾经说过“再生……意味着不得不真正面对令人恐惧的生存困境”(58)。正因如此,再生的主题归属于荒诞的范畴。而荒诞的主题将是第三章探讨的中心问题。
——摘自《权力·死亡·荒诞——对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小说的解读》第二章
专著简介:
《权力·死亡·荒诞——对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小说的解读》是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美学探究”(项目编号:13DWXJ13,2013-2016)的结项成果。专著围绕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作品展开,揭示了该流派发轫、发展和衰退的内在原因,对于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唐文(1980- ),山东省青岛市人,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在站博士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一项,发表CSSCI期刊论文8篇,获得山东省社科三等奖等奖项。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