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来说,70年不寻常。从学科的草创,到如今的蔚为大观,有人数众多的研究者群体,在文学研究和社会生活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历程。过去70年的中国文论,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这是关于中国文论的阶段论,作者在别处作过论述。在本文中,主要探讨文论资源的层次论。这里所说的层次论,指文论资源具有层累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不同的资源依次出场,累积在中国文论中。通过不同资源动态的相互作用,形成当代的中国文论知识体系。
隐性与显性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所接受的主体资源,主要还是来自根据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苏联的文论体系。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代中国文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并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从晚清和“五四”以来,前辈学者在理论上作出了多种建构的努力。他们在对国外文学理论的引进,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创造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历史不能截然断开。但是,公允地说,1949年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来说,的确是一个新开端。这时,正如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这集中表现在,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向全国进军,并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来自原“国统区”的作家,与原“解放区”的作家,在会上相聚,实现了“会师”,并由此使两支文艺队伍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这支队伍,承担着要对旧的文艺进行彻底改造的使命。文艺理论在那一时期,就起到了对文艺进行改造的动力源的作用。
在文艺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手空空地进城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在30年代的上海,还是40年代的延安,都积累了不少指导革命文艺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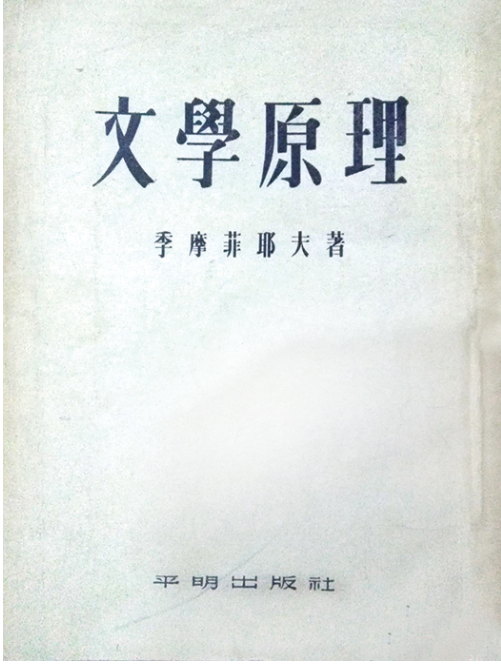
在当时中苏友好的环境下,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学习,文艺理论中也出现了对苏联模式的引入。季莫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由查良铮翻译,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在北京大学,毕达可夫班培养了一代文艺理论研究者。其他一些高校也邀请苏联专家授课。这些翻译活动和讲授活动,都对此后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在50年代,来自根据地和来自苏联的文艺理论资源,在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面,起着显性的作用。因此,在文艺理论建设上也实现了会师。在指导文艺工作方面,来自根据地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苏联的理论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大学的教学中,苏联的教材体系,由于有着现成的结构,同时也由于它是在苏联的大学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更适应学校教学,因而有着更大的影响。
这种显性的影响是主导的。无论是在大学的文艺理论教学中,还是在文艺评论所使用的术语中,都体现了出来。在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并未消失。从晚清到“五四”,以及此后的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都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在西方文论引进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都有着一定的成果。在大学的文学教学和文艺批评中,都体现出来。但是,与这时的根据地文论和苏俄文论相比,这些影响在50年代呈现出隐性的状态。
中国的革命,曾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要推翻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受这一“反帝反封建”中心任务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所接受的主体资源,主要还是来自根据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苏联的文论体系。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代中国文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资源的接受,也是当时中国文论的功能所决定的。关于文论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统一的、一劳永逸的回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论的作用是不同的。在50年代,文论所具有的作用,是对当时的文艺进行改造。在文艺界,西方的和古代的影响都很深厚。对这些文艺进行改造,实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革命,是当时的中心任务。我们所熟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原本就有对古代和西方文艺进行改造的含义。这个方针于1964年提出,缘起于毛泽东对一位名叫陈莲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上的批示。这位学生来信的原意,是认为革命现代京剧的演出,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而这位学生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还是西洋的那一套,没有任何革新,因而表示不满。毛泽东的批示赞同这位学生来信中的意见,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就是要对来自外国的和古代的文艺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文学艺术的样式来。
作为主流的三个资源相互更替
古代的,外国的,与现代的这三种资源,是80年代以后文论发展三重动力源,而它们的出场,都是与文论发展的特点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符合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再加上此前在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著名的“十六字方针”。对于文艺理论研究者来说,这16个字的意义极其重大。在“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的“新时期”,重提这”十六字方针“,对其含义的理解,就有了变化和深化。在这时,文论资源有了极大的丰富。原本处于隐性状态的外国资源和古代资源,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被凸显了出来。
当然,介绍外国文艺理论的工作,从来没有断过。有一套《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出版,挑选了“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下至20世纪初”的“各历史时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说明》,见布瓦洛《诗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扉页),其中包含有柏拉图的《诗学》、亚理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而对20世纪外国文艺理论的介绍,则主要是在80年代才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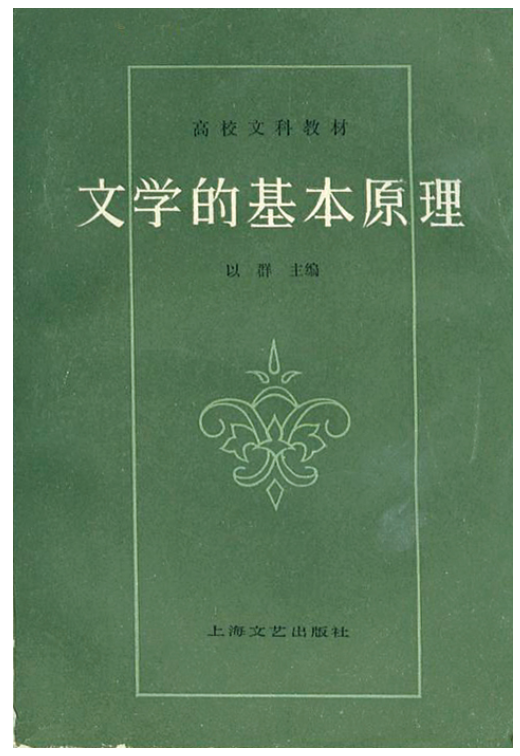
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理论界学习西方,多译快译西方文论著作,成为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由王春元和钱中文主编的文艺理论译丛,收入了以韦勒克和沃伦著的《文学理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论著作,再加上一些美学和艺术学的译丛,改变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面貌。原来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显得过时。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和赵毅衡的《新批评》等介绍西方20世纪文论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哲学上看,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众多的方法在影响文论,从心理学上看,弗洛伊德、荣格的思想走进了文论之中。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也影响到了文论上的语言学转向。在80年代中期,还曾有过从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出发,形成具有中国自创性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热潮。这一热潮后来受到人们的垢病,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一热潮对于文论的转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是当时多种诉求的一种合流。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和“与世界接轨”的要求,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新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文学文化的影响,使得“文化”的概念在文论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审美文化”研究,到“大众文化”研究,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文论学者思想活跃,文论界也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种“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而积极的结果,是中国学者逐渐克服了“中”与“外”的二元对立,不再将中国看成是处于世界之外的特殊一国,而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接轨”所带来的,是将学问打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面对一些人类的共同问题进行学术思考。当然,这种转向也有不足之处。在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上,仍是引进消化为主,创新不足,甚至有学术时尚化的倾向。学者不再根据实践的需要,来研究学术前沿,而是根据在国外流行情况来判断是否“过时”,追逐最新最时尚的学术潮流。
不仅对外来的文论资源是如此,对古代文论资源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当代中国文论建设者们对古代文论的价值及其对建设当代文论的意义,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国文论史的研究,是在文论观念的形成,以及大学开设文论课程的要求基础上开始出现的。这方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像范文澜、罗根泽这样一些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以及郭绍虞等人对中国文论史和批评史的写作。这种研究有一种倒序性,即有了现代文论观念,才开始追溯这些观念所限定的对象在古代的历史。在当代文论研究发展的推动下,开始有人专门从事文论史研究,并将当代文论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所形成的概念体系向古代投射,寻找其同与异,从而写出有关古代文论的历史著作,这是研究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繁荣,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怎样从古代文论中汲取资源,充实到当代文论研究之中,这是另一层次的问题。这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命题。古代的文论能否实现现代转换?如何转?这在中国文论界出现了大讨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争论,成功地吸引了文艺研究界的注意,对于古代文论在现代中国被找回,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比起这一争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还是对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和关键词的研究。关键词所具有的抽象性,使它们成为从古代通向现代的桥梁,同时,关键词也成为当代文论在思想建构过程中的脚手架。
除了外国资源和古代资源以外,在中国当代的文论资源建设中,还有一重资源,在80年代以后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这就是20世纪前期,从晚清,经“五四”直到40年代所积累的文论资源。这种20世纪前期的文论资源,并不是天然地进入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之中的。50年代的两种资源,即根据地资源与苏俄资源的结合,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底色。在那一时期,只有这两种文论才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这两种文论打下了底色,其他的资源只是在此之上所作的画而已。20世纪前期的一些学者的创造,也是在吸收了西方的和古代的文论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着20世纪中国学者融合中西、自主发展的成果。这时,跟着前辈学者“接着讲”的思想,开始在学界流行起来。这种“接着讲”的提法,在此前的50年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为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新社会实现思想的全面更新。具体到文论上,不可能对此前的观点“接着讲”。经过了几十年的变化,中国学者已经视野开阔,储备了丰富的知识。这时,在新的基础上接续过去的一些思路,从前辈学人的成果那里汲取营养并“接着讲”,就有了可能。
这种“接着讲”,还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们倡导“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但实际上在研究界,所出现的是“古”与“洋”的二元对立。主张“古”的人,认为要强调中国主体性,就要从古代去追寻纯粹的中国性;主张“洋”的人,或者只是将中国的文艺现象当做西方理论注脚,或者在“过时论”的影响下,陷入到对西方最新理论的追逐之中。这两种研究者相互分裂和对立,争吵不休或不再争吵而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接续20世纪前期的一些讨论,学习当时处理“古今”和“中外”问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不失为克服二元对立之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外国的,与现代的这三种资源,是80年代以后文论发展三重动力源,而它们的出场,都是与文论发展的特点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符合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践层面:进入与新时代的创新
近年来开展的关于文学理论“接地性”的讨论,就是不满于文学理论的不及物状态和游击主义心态而提出的。
我们在讲上述关于文论建设的资源时,尚未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即文论发展的内在需要。实际上,文论的发展变化,对一些资源的重视,在一个时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都是与这个时期的特定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在上世纪50年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以及对资源的选择,植根于这样一种需要,即发展革命的、进步的文艺理论,通过这种理论来对当时的文学艺术进行改造,从而建设新的文学艺术。在这时,文艺理论具有指导的意义,其指导的对象,是当时继承下来的文艺现状。
这种对文学的改造,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将这种实践在大得多的范围里,在文化情况复杂得多的大城市里实现这种改造,需要理论的支持。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大学教学中,也面临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改革,需要从理论上的提高做起。从苏联引进的一些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适应了这方面的要求。在文学中,要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塑造革命的英雄人物,反映现实的斗争,等等。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些创作方法是对文艺创作提出要求,对于文艺的变革具有指导意义。
在80年代提出的文艺向内转,引进了“新批评”和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这些方法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原本赋予文艺理论的对文艺进行改造的任务,转变为降低理论姿态,仅对既有文本进行描述分析。这时,文艺理论不再研究文艺应该是什么,而是转向研究文艺实际上是什么。理论的这种文本转向,是一种追求实践性的表现。它丰富了文艺理论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学教学之中,文本分析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有助于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细读。这本身也是受着研究的实践性推动的。
与50年代盛行的从俄国引进的文学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着贴近文本,细读文本,并对文本进行评点的特点。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也就有着相似的命运。在50年代得不到鼓励,而到了80年代却受到欢迎,配合了当时向内转的大潮。
上述“向内转”所形成的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这种“描述性”,在文艺研究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不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且在此后,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发展。例如,由这种描述倾向所形成的对作品细读传统,叙事学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文学符号学形成,都在保持着这一传统。
然而,从国外后续传来的“后现代的转向”以及“文化转向”,使得文学理论再一次“向外转”。在上世纪90年代,在文学理论界出现了“文化研究”热,呼吁文学研究的“跨界”和“扩容”。这种“跨界”和“扩容”,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跟上发展着的西方文论的新潮流。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的消极意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来。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提出,“文学理论”变成了“理论”,在“理论”的名义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走出了文学,涉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然而,出去了还要回来。打一个比方,只是守着文学,不看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划地为牢。但是,如果走出文学,只谈理论不谈文学,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那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家的定义,应该是可进可出的常驻地。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还是家园。
近年来开展的关于文学理论“接地性”的讨论,就是不满于文学理论的不及物状态和游击主义心态而提出的。文学理论有着自身的历史传承性,有一套理论话语体系,与其他学科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对话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同时,又时时面向当下的现实,受当下的文学实践影响,在这种实践的推动下前进。
纵观70年的文论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理论总是应文学实践的需求而发生发展的。这里的文学实践,既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写作;既包括对现有文学改造的要求,也包括在大学课堂讲述文学的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学家族,包括作家、评论家,还包括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文学期刊的编辑者,大学的文学研究者,中小学里的语文课老师,还有众多的从事各行各业工作,或者不从事任何职业的有闲人群中的文学业余爱好者。这些人的需要,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70年国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发展的需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各种资源,加入到文学理论的体系中来。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被选择的文论资源和实践的主体性关系。从文学发展的实践出发,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丰富的体系。
我们将70年的文论分成五段,即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在新时代,“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仍然有效,但一个更突出的主题出现了,这就是面向当下的实践,面向未来,而进行自主创新。中国文论在新时代的创新,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艺,推动文艺的繁荣,也要面向世界,使中国文论的话语走出去,进入到国际的对话之中。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