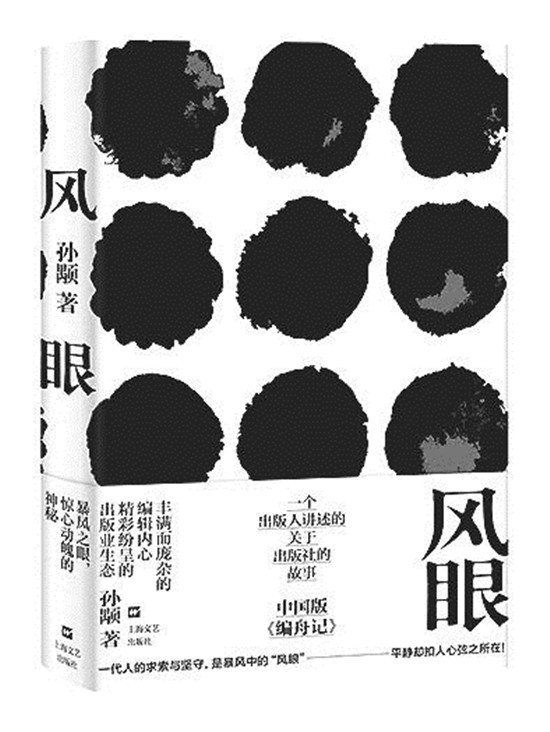
在很多人眼中,孙颙是上海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不在于他多年担任出版社、新闻出版局以及上海市作协领导职务,而是无论身居何职,处于怎样繁忙的工作状态,他总是见缝插针地写自己心中所想,用书写的方式与当下生活发生着切实、紧密的联系。近些年,读者所熟悉的,是他以长篇小说《拍卖师阿独》《漂移者》《缥缈的峰》等关注社会发展中新生事物、新生职业人群为主线的一系列创作。正如有评论者所言,孙颙的创作存在一条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却有内在联系的线索——他的才能在于总能写出符合他其时所思所想的作品。
其实,孙颙也有更多的故事在心头一压就是几十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只有和作家朋友聊天时,才零零散散地倾吐。他们劝他,写吧,不写的话,它始终在心里折磨着你。——他们所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孙颙在出版社工作时耳闻目睹的种种。那时,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东西并没有定论,而是在不断讨论、争论和尝试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在这其中,出版业并未缺位,正如孙颙所言,“出版业非但是鼓吹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而且是改革开放进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其中有非常多珍贵的素材有待书写。无论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还是自远方传来的激越、复杂而多义的声音,即使时隔多年,也常令他心潮澎湃。那时,各方压力下出版人的作为与不为,往往投射着社会上最早一批听到“春雷”的人的心态,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迅疾变化着的社会氛围的影响——如果以小说来写,究竟从哪里切入、如何展现,孙颙思量了很久。最终,以一套《市场经济常识丛书》出版后的风波为中心,他虚构了一家出版社,以及一批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于狂风暴雨中面临抉择、经受考验的过程——《风眼》应运而生。
对于改革开放,孙颙作为亲历者充满了个体情感。“当下中国社会的活力,就是通过市场经济这么一步步释放出来的。”他说:“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人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激情,这就是来自于市场经济释放出来无数人的创造力。市场经济不光给了我们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也实际上激发了无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他手下曾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因为住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真心相恋的未婚妻与其分手,南下深圳。他仍记得当时那位编辑的话:“我没有一间小房子让我们成亲。”这让身为社长却无能为力的孙颙难过了很久:“国家如果不快快发展起来,那个年代的上海的市民多数挤在破旧的房子里,三代甚至四代同房,七十二家房客,年轻人有个小家的愿望就只能是飘渺的梦。”而如今,这段曾多次在他脑海徘徊的记忆,终于在《风眼》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好比这个细节,如果我不在哪个作品里用到它,它会一直跟着我,时常提醒我,那种感情没法宣泄出来。小说是虚构的,人物是编的,但在我的写作中,那些感受都是很真实的。”
“从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来看,孙颙老师经历了新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整个历程。”日前,在上海作家书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主席孙甘露表示。“他首先是一位作家,同时在做出版的过程、以及后来到作协做领导期间,一直在持续地写作,他可以从这两个部分来观察创作和出版的生态。”在他的解读中,“风眼”所指的是台风眼,核心区域平静无澜,却在周围酝酿风暴,“从小说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这套丛书,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处在变动时期、很丰富的社会面貌。整个出版业多年以来,跟国家层面、文化层面的决策、跟整个社会思潮的变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外人不大能够清晰地意识到”。他认为,《风眼》的别有意味正在于此,“通过日常的生活把‘风眼’中风雨欲来的感觉表现出来,同时里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精神样貌——它写了一个很特殊的事件,但是又通过出版社非常日常的状况来反映”。
看过《风眼》后,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的第一个反应是,孙颙将“王副社长”所代表的老上海滩原有的那一批已经“沉下去”的人,在市场经济潮流中又写“活”了。或许是因为写自己常年工作其中的行业,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虽然明确表示没有具体原型,但孙颙在其中似乎叠加了无数旧识的身影。比如业精于勤、严谨治学的郭副总编背后,是上海出版界许多老老实实做学问、很难在某个时候成为亮点的人,关键时刻却充满担当;退休在即的唐社长,则是前辈学人与知识分子的缩影。“老一辈的人非常可爱,有时他们也会吵架,但绝对和文化相关,而不是和个人利益相关。他们的精神气质一直伫立在我们心里,这一代人,正在离我们远去。”近些年,孙颙陆续送走了许多文化老人,不无沉痛地写了对于钱谷融、丁景唐、屠岸等前辈的悼文,每写一篇,缅怀与哀伤的同时,他感受到的是这代人的道德文章与感召力,“与他们的交往,是实实在在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我人生的导航”。这些前辈对他的扶持和帮助,让他永生难忘:作为师长,钱谷融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位学生,在他的处女作《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毅然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支持和鼓励他去北京赴会,助他从此走上文学道路;丁景唐身为他的前任社长,敞开心和他谈具体社情以及难处理的问题,并用心良苦地全部“放手”,促成他的迅速成长;屠岸和韦君宜商议决定录用《冬》,使得孙颙与冯骥才、竹林的名字一同刻写在新时期文学的崭新开篇上,并在多年的淡然交往中,时不时给他以支持和鼓励……
某种意义上来说,《风眼》也可看做孙颙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雪庐》《烟尘》《门槛》三部曲陆续出版,在宏大的结构下,勾勒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也奠定了他在写作中始终思考知识分子命运走向的底色。孙颙从小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深深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但在写作中,他所侧重的从不是他们所经受的苦难,而是某种屹立至今的精神。《风眼》中,处于同一家出版社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诸多困惑:风暴当前时,是选择谋私利,还是保公利,他们都作出了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而在真正的出版人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有底线的坚守:“总体上认为是对的事,要坚持。当你的坚持没法抗衡于给你的压力时,可以不行动,但不要做相反的事。”
在快速的社会发展和审美变迁中,孙颙突然发现,自己有些“落伍”了。第一次看到《风眼》的封面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忍不住提出抗议:“黑乎乎的一个个圆,像眼睛一样,这怎么行?”但在不断沟通中,他逐渐理解并接受了编辑的想法。正式付印后,很多人告诉孙颙,这本小说“颜值很高”,他才彻底放下心来。就像小说名原来叫作“社长室”,在编辑的建议下才另作思考,最后定名《风眼》。谈起这些细节,孙颙坦然“服输”:“现在看他们成功了,年轻编辑更懂得现在读者的审美和眼光,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超过我的。”正如小说中,一本书、一套书的诞生,是一位乃至多位出版人从判断力、专业意识,到对于读者审美以及社会局势把握的综合成果。出版人身上背负的绝不仅仅是书,而是对于知识、理念、价值的认可和推介,这一切随着时代更迭而时时更新。以《风眼》一书,孙颙告诉出版业的后来者,路漫漫其修远兮,而最需坚守的,莫过于内心的平静和淡然。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