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梳理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处处是拐点,一个不小心就行差踏错万劫不复。
他有太多里的理由烂在故乡,死在军队,他也有太多的理由堕落,但最终都没有,反而成长为一位世界级作家。
为什么?
因为对于沈从文来说,人间值得。

沈从文去当兵的理由很平庸,主要是凤凰尚武风气很强,外加在军队可以随便野。
这个著名作家是“野”大的。
别人上学他逃课,别人背之乎者也他带头捉迷藏,夫子都快把他掌心打出茧了,第二天还翘,跑到街上看热闹,乡亲杀猪宰羊,手艺人做棺材雕佛像,男人决斗,男女唱情歌,都比书好看。
在沱江里游水捉蛇,与小混混打架斗殴也是少不了的,被他叔叔都快揍皮实了。
乡里各派武装械斗,河里尽是死尸,脸被野狗啃了半边,他混不在意,捡根木枝戳戳那剩下烂了的半边。
沈从文在凤凰无拘无束地晃荡到了十四岁,终于背上小小包袱,顺着小河,决计去闯一闯。恰逢部队招人,他和家里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这支部队是湘西的军阀武装,沈从文随之流连沅水上下,跟士兵在船舱里打牌,听老兵瞎扯淡,给死刑犯写罪状,拿手活儿是炖狗肉。
刚开始他满口“老子”,一位姓文的秘书惋惜地劝他,“小师爷,你还这样小,不要张口闭口老子老子的。”
沈从文摇头晃脑,“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
他那时的状态近乎于小兽,无拘无束,天真野蛮。
文秘书看着他微笑,“你聪明,应该学好,世上有许多好事情可学。”
哦?什么东西比这种野来野去的日子还好?沈从文倒要看看。
于是便开始订《申报》,看《辞源》,后来又想尽办法看《新潮》《改造》,五四精神从千里之外的北平上海浸润着这个尚处在蒙昧、原始、野蛮山地里的少年。
他虽仍是在部队里无所事事,不是看士兵上操,妇女浣衣,就是跑到山洞里吹吹凉风,但意识中,已有许多他年少时尚辨不明白的东西在渐渐发芽。
世界愈来愈广阔了,除了湘川黔的大山与那一条长长的沅水,他还有了北平、有了上海,有了轰轰烈烈的正在变化的新时代。
沈从文心想,去他的,凭什么?我病死淹死或饿死,有什么不同?不如出去看看!
他做出一个孩子气又孤注一掷的豪赌:去北漂!我倒要看看,我自己支配自己,比命运处置是更好还是糟糕?要是赌输了,那就饿瘪瘪倒在空房下阴沟边算了!
这一年,沈从文20岁。

刚下火车,沈从文站在北平前门广场上,川流的都市映照着惶惶然孤伶伶的他,他几乎吓坏了——“北平好大!”
身上只有几块钱。
那也得咬牙活下去!
沈从文在酉西会馆的半年是很孤独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交际,每天就是扎进京师图书馆里自学,什么旧体文新体诗、史传笔记都被他就着两口馒头一点热水消化进去。
无人可应,无人可说,年轻人在冰凉凉一隅天地里,沉默地燃烧着。
半年之后,同在北京的表弟十分担心,“这可不行!”他生怕沈从文憋出个抑郁症或者反社会人格,于是介绍他搬到了银匣胡同公寓。
这公寓也不怎么样,沈从文叫它“窄而霉小斋”。不过这里条件虽差,却连同着周围几爿一起,热热闹闹地挤满了来北平求学的学子们。

正值蔡元培主持北大之际,学气斐然,毫无限制,旁听生比注册生多上几倍,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年轻的热切。
沈从文比较苦,小学文化,根基浅,时新的标点符号也得从头学。旁听了许久,仍没考上。
他写了几篇稿子去投稿,好一点的石沉大海,不好的被主编扔进垃圾桶公然嘲讽:“看看,这就是时下的新一代作家!”
沈从文又想了,凭什么?我还写不出来了?
他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住处没有火炉,只两条棉被,一件单衣。日子多苦?几天吃一顿,饿着蜷在被子里,一边流鼻血一边写,把上门探望的朋友妻吓得晕倒。
这乡下蛮子还记得自己来北平要找的是怎样的生活,要做的是怎样的事业,片刻未感忘怀。如此潦倒痛苦的日子,竟坚持了两年半之久。
后来他终于获得了徐志摩的欣赏,文章刊登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并专门为此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美得像诗: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给这类的作者,奖励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沈从文说这赞语简直让他“背膊发麻”。
他一边觉得徐志摩的欣赏让他起鸡皮疙瘩,一边又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天赋,给张兆和的信里动不动就自夸: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
这是沈从文式的自负。“行将超越一切而上”这几个字,天真,矜持,肃穆,让人无法发笑,反而由衷相信,并为这个年轻人热切企盼。
从学标点符号到站在现代文学之巅,沈从文只堪堪用了10年,这充沛的创作力又延续了10年,产出惊人,篇篇经典。
汪曾祺对老师推崇备至,“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在法国、瑞典、美国,沈从文的文字也捕获了大批的追随者,并两提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太阳升到最高处,就离沉没不远了,不久后,沈从文就要开始经历人生中漫长的黑夜。
但在旁人看来是黑透了的境遇,于他而言,却是迸发才华的催化剂。

沈从文47岁时,绝望自杀。他用剃刀划破脖颈和两腕动脉,又喝下煤油。他是怀着必死的决心自杀的,但被救出。
死过一次后的沈从文不再进行正式的文学创作,因为找不到源头。书店也写信给他,说你过时了,以前印刷好未发行的存货我们已代为烧毁。
一个写了近20年、站在文坛巅峰的天才型作家突然跌落,这比“50岁了突然被公司裁员”严重得多,写作不仅是他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他生命价值的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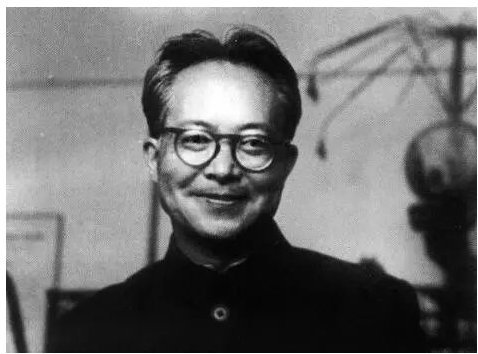
如果一个人在不知道沈从文结局的前提下,重生穿越到了他身上,家徒四壁、妻儿四散,事业颓败且永不可重返巅峰,他可能会想,那我还不如死了。
但是沈从文选择了重新开始。
不过是重新开始嘛。他从乡下小子去当兵,从一个小土蛮子去当作家,哪个不是重新开始?虽跌跌撞撞,但仍有可为。
沈从文很喜欢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而且是公认的有天赋。宋明旧纸,川蜀刺绣,吴地青瓷,云南漆器,他都很专精。
他先是申请进入历史博物馆做文书,贴贴标签,当当讲解员,后来被赶去扫厕所。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
从神坛跌落的他,谁都能来踩一脚。
当年他曾帮助范曾解决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但好心没好报,屡次遭暗算,被当面奚落:“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
杀人诛心。沈从文气得发抖,几乎哭了。

沈从文67岁时,境况更差了,服饰史的研究史料被当作垃圾论斤卖掉,手稿被焚毁或者神秘消失,人也被赶到了湖北双溪。
双溪属云梦泽区域,整天云遮雾绕,雨水蒸腾,而且几乎与世隔绝,又无书可读,除了看菜园子就看猪牛打架。

沈从文想的是什么?
这儿荷花真好。
他给黄永玉写信,“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黄永玉被表叔馋死了,虽然知道情况一定没这么好,但也忍不住羡慕: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花……”
沈从文在这种绝境里干了两件事:
一、他仅凭记忆就完成了中国服饰史数十万字的补充材料;
二、为黄永玉的家族变迁写了近两万字的“楔子”。黄永玉的两个孩子可爱读了,称之为“爷爷写的红楼梦”。
双溪的荷花再怎么美也挡不住日子苦,沈从文终于病入膏肓。死不大可怕,就是想起来工作做了一半很糟心。
临病死前他打报告,说与其如一废物坐以待毙,不如回去将一些需待亲手重抄的工作整理出来,上交机构。
报告没批复,他倒是从鬼门关遛了一圈又回来了。
春去夏来,曙光得失几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付梓出版。这本书什么地位?它被称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日本官方重金求版权未果,出版后一度当作国礼赠与尼克松、日本天皇及英国女王。
谁都没想到这事情能被他搞出来。谁又都觉得,这事情被他沈从文搞出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不了解沈从文的人总被他苍白的外表欺骗,加上他的文字清丽简峭,便总以为他真的很文弱。
实际上呢?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种硬,正是生命意志的不屈。
他面若蒲苇,却志如磐石。
众生在世,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兰桂未必齐芳,林木未必同秀。
公平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巨兽匍匐,也都有两把刀剑。凡人入渊升天,或由巨兽拉扯沉沦,或凭刀剑斩妖伏魔,便是生命庄严与否的转折。
这斩妖剑、除魔刀,一是意志,二是选择。
“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
70多年前,沈从文在《潜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而往前推算,从1922年离开行伍前往北京的那一刻起,他对自己的意志,就片刻未敢忘怀。
这意志蔓延了沈从文的一生。年少时,这意志是“凭什么”的大声疾呼,鞭策着他;
低谷时,他默默无言,似乎燃尽了篝火。
而实际上,泉水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这意志给他的生命托了底,这才有了触底反弹,至暗回光,重返生命巅峰。
屠魔不论少年,古稀亦可再来。
当纷杂的八卦褪去,浅薄的趣谈沉底,沈从文的人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正是这一点不屈的意志。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