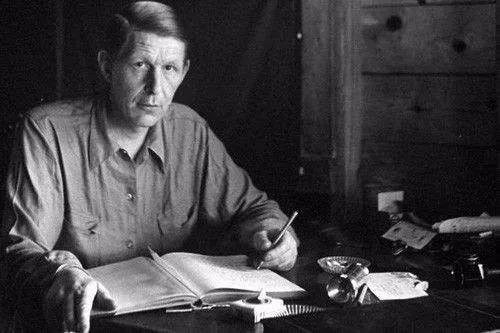
我由衷地感激一些诗人和小说家,我知道,假设我不曾读过他们,我的生活将变得更为贫乏,如果我试图列出他们所有的名字,将会长达几页。但是,当我思索所有我真正感激的批评家时,只得到三十四个名字。其中十二个是德国人,两个是法国人。这是否表明一种有意的偏见?的确是。
如果说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比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更罕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自我主义天性。诗人或小说家在面对自己的题材(一般来说是生活)时必须学会谦逊。然而,批评家必须学会谦逊对待的题材是由作者即人类个体构成的,而获取这种谦逊要困难得多。比起说——“A先生的作品比我所能评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说——“生活比我所能描述的任何事物更为重要”要容易得多。
有些人过于聪明,不能成为作家,但他们也不会成为批评家。
上帝知道,作家可以愚不可及,但是,并不总是像某类批评家所认为的那么愚蠢。我的意思是,当这类批评家谴责一部作品或一个篇章时,绝不可能想到:作者早就预见了他将要说些什么。
批评家的职责是什么?在我看来,他能为我提供以下一种或几种服务:
1、向我介绍迄今我尚未注意到的作家或作品。
2、使我确信,由于阅读时不够仔细,我低估了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
3、向我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我对它们所知不够,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仅凭自己无法看清这些关系。
4、给出对一部作品的一种“阅读”方式,可以加深我对它的理解。
5、阐明艺术的“创造”(Making)过程。
6、阐明艺术与生活、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的关系。
前三种服务需要学识。一名学者的知识不仅要渊博,还必须对他人有价值。我们不会把对曼哈顿电话簿烂熟于心的人由衷地称为学者,因为我们想象不出他在何种情形中可以赢得学生。由于学问意味着一种知道更多的人与知道较少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也许是暂时的;在与公众的关系上,每一位书评家暂时地都是一位学者,因为,他已经读过他正在评论的书,而公众却未曾读过。尽管学者拥有的知识必须具有潜在价值,但他自己不一定要认识到其价值;经常有这种情形:由他传授知识的学生对其知识的价值反而比他有更好的感受力。一般而言,在阅读学者的批评文章时,比起他的评论,人们从他的引文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教益。
后三种服务,需要的不是卓越的知识,而是卓越的洞察力。批评家的卓越洞察力表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新颖、重要,尽管人们可能并不同意他给出的答案。也许,很少有读者能接受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 )一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只要是读过这本书的人,绝对再也无法漠视托尔斯泰所提出的问题。
我最不愿意询问批评家的事情是,让他告诉我“应该”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我不反对他告诉我他自己喜欢、厌恶哪些作家和作品;事实上,这对我很有用,根据他对我读过的作品所表示的喜恶,我就可以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我会赞同或反对他对我尚未读过的作品所做的判断。不过,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我。选择读什么书是我自己的职责,世上没有人可以替我做主。
对于作家的批评主张,我们听取时总要大打折扣。因为,这些主张主要表明他自己在斟酌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应该避免什么。而且,与科学家不同,他比普通大众更加漠视同行们正在做的事情。一名超过三十岁的诗人可能依然是一名贪婪的读者,但是他所读的大部分未必是现代诗。
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夸口自己从未因道听途说而谴责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但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赞誉过自己尚未读过的书或作家。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里,恪守“不可反抗恶,反要以善胜恶”这条训诫,是不可能的,但在艺术领域这却是常识。低劣的作品经常伴随着我们,但任何特定的艺术作品一般只在某个时期内才是低劣的;其显露的低劣之处迟早会消失,被另一种特性所取代。所以,不必去攻击这种低劣之处,它终将消亡。如果麦考利从未写下评论罗伯特·蒙哥马利的文章,我们今天照样不会处于蒙哥马利是伟大诗人这一幻觉之中。对于批评家,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热情地宣扬他坚信的优秀作品,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低估的时候。
有些书被不恰当地遗忘了;然而没有书被不恰当地记住。
有些批评家争辩说,暴露某位作家的坏处是他们的道德职责,因为只有这样,这位作家才不会腐蚀其他作家。的确,年轻作家可能会被老作家引入歧途,即偏离正轨,但他似乎更有可能被优秀作家而不是坏作家诱惑。越是强大的、具有原创力的作家,对于正在试图寻找自我的天分较差的作家,就越危险。而且,内在贫乏的作品往往能够激发想象力,在别的作家身上间接地造就优秀作品。
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的品味,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煮过头的白菜,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不错,对于某些人,以下说教会立竿见影:“粗俗的人才喜欢吃煮烂的白菜,有教养的人则喜欢中国人烹饪白菜的口味”,但是效果不会持久。
当一位我信任其品味的书评家指责某本书时,如果我感到慰藉,那仅仅是因为出版的书籍过于丰盛,想到这点令人释然:“嘿,这里至少有一本不必为之操心的书。”但是假如他保持沉默,效果将是一样的。
攻击一本低劣之书不仅浪费时间,还损害人的品格。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的确很差劲,写文章抨击它所拥有的唯一乐趣只能源于我自身,源于我竭力展示自己的学识、才智和愤恨。一个人在评论低劣之书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文学上有一种罪恶,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保持缄默,相反,必须公开而持久地抨击,那就是对语言的败坏。作家不能自创语言,而是依赖于所继承的语言,所以,语言一经败坏,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关切这种罪恶的批评家应从根源处对它进行批判,而根源不在于文学作品,而在于普通人、新闻记者、政客之类的人对语言的滥用。而且,他必须能够践行自己的主张。当今的英美批评家,有多少是自己母语的大师,就像卡尔·克劳斯是德语的大师那样?
我们不能只责备书评家。他们大多数其实只希望评论那些他们相信值得一读的书,尽管这些书存在缺陷,但是,假如一位专门为各大报纸周日版撰写书评的人遵从自己的偏好,那么,三周中至少有一个周日,他的专栏会出现空白。任何具有责任感的书评家都很清楚,如果必须在有限的版面中评论一本新诗集,唯一妥善的办法是给出一系列引文,而不予评论,但是,一旦他这么做,编辑就会抱怨,他这是无功受禄。
然而,书评家给作家贴标签、归类的恶习应受指责。最初,批评家把作家划分为古典作家(即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和现代作家(即后古典作家)。随后,他们以时代划分作家:奥古斯都时代作家、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等等。如今他们则采取十年划分法:三十年代作家、四十年代作家等等。很快,他们似乎要以年份划分作家了,就像对待汽车一样。十年划分法已经有些荒诞,似乎是建议作家们在三十五岁左右合乎时宜地中止写作。
“当代”是一个被过分滥用的词。我的同时代人只是那些当我活在世上时他们也在人间的人,他们可能是婴孩也可能是百岁老人。
“你为谁写作?”作家,至少是诗人,经常被人们如此问及,尽管提问者对这个问题应该知道得更加清楚。这个问题当然愚蠢,但我也可以给一个愚蠢的答案。
有时候,当我邂逅一本书,会感到这本书只为我一人而写。就像唯恐失去的恋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存在。拥有一百万个这样的读者,他们之间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带着激情阅读,却从不相互交谈,这,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白日梦。
文章译者:胡桑,选自:《染匠之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