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游戏是王,而童年是这个王的领土,在这个王国里,‘幻想’是公开使用且被使用最多的唯一的官方语言。”《游戏是孩子的功课》为我们观察孩子们的世界打开了新的视野。
孩子们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过家家”,或“王子公主”之类的扮演游戏,玩得投入而忘我,我们每个人对此都不陌生。但极少有人会考虑,这种充满稚气的玩耍和幻想有什么意义。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长们也越来越焦虑的当下,它还很可能被看成是浪费时间,孩子们会被带领着学习更有用的知识,更丰富的特长,而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些散漫多变的游戏上。
但是,美国学前教育专家薇薇安·嘉辛·佩利的《游戏是孩子的功课》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她曾在新奥尔良、纽约及芝加哥的幼儿园共任教37年,一直跟孩子有密切的接触,并且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记录,和深入的思考。她发现,从看似无意义的幻想与扮演中,孩子们学习了语言、逻辑和合作;在由自己主导的游戏里,他们的专注力和想象力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薇薇安·嘉辛·佩利(Vivian Gussin Paley),1929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美国著名幼儿教育专家、作家、演讲家,曾在新奥尔良、纽约及芝加哥的幼儿园共任教37年,提倡“游戏本位教学法”。获得埃里克森机构颁发的儿童服务奖、麦克阿瑟奖、前哥伦布基金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等多个奖项。
《游戏是孩子的功课》总策划、学前教育学者孙莉莉介绍说,佩利开始任教的时代,刚好是美国非常强调考试、测评、标准化的时代,成人对于自由游戏、假想游戏、幻想游戏处于一种警惕的,不满的,甚至是敌对的状态,佩利对此有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她通过自己的研究、著述和演讲,提倡“游戏本位教学法”,强调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大人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主导权交给孩子们自己。“对于年幼的孩子而言,再没有比游戏更严肃的事情了,游戏就是他们的功课。他们在游戏中,在虚构和幻想中,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和不真实,寻找边际和边际的弹性。”
我们摘取了《游戏是孩子的功课》一书的前两节,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一窥薇薇安·嘉辛·佩利的思考,和她用心观察到的孩子们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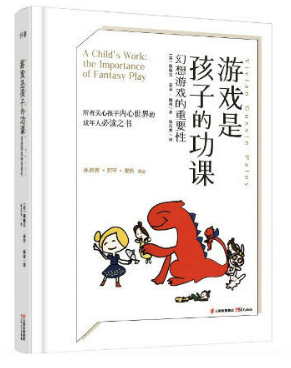
《游戏是孩子的功课》,(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杨茂秀译,禹晨千寻|晨光出版社2018年3月版
小孩子
“游戏(本书中提到的游戏,多特指儿童的幻想游戏)是孩子的功课”——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1949年,来自新奥尔良市纽科姆幼儿园(Newcomb Nursery School)的园长雷娜·威尔逊(Rena Wilson)女士。当时她是在索菲-纽科姆学院(Sophie Newcomb College)的“幼儿导论”课堂上说起这句话的。那时,我是刚刚转入该校的四年级新生。因为结婚的缘故,我暂停了大学的学业;搬到新奥尔良后,重新入学继续我的大学课程。那时,我还没有决定要当老师,只是觉得学习有关小孩的课程是不错的。课堂上,威尔逊教授承诺,将带领我们一起去探索童年心灵的核心。
小孩放学回家后,就换成我们班上的同学坐在幼儿园小孩坐过的小椅子上,仍在苦苦思考我们当天所观察到的现象。威尔逊教授告诉我们说:“你们正在观察的,是学校中唯一一群无时无刻不在忙着为自己设定功课的年龄群体。那看起来、听起来都像是戏,但我们觉得用孩子的功课(work)来称呼这些幻想游戏,是很恰当的。为什么说很恰当呢?这正是你们来这里要寻找的答案,而且,要自己找。”
我们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我们一开始记录某一组事件,被我们记录的主角就立刻改变主意,假扮别的去了。他们彼此给对方提供线索与消息,而我们却如同呆头鹅,感到莫名其妙。不过,我们会收集到有趣的小故事、好玩的谈话片段、一些积木建筑绘图,还有一些湿答答的绘画。收集这些的同时,我们也试图了解孩子在过程中学习到了什么。我们无法捕捉到的是孩子们在语言和行为中所附带的情感强度和意图。直到威尔逊教授温和地建议我们,要在这些混乱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我们才恍然大悟。
“假装你是在演戏的小朋友,”她说,“你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阻碍了你将你所见到的演出来?就这样填充你不了解的空白,并且不断地提醒自己,当小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游戏确实是功课。首先,要决定自己想扮演谁,而别人又该演谁,周围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更换场景。接下来就是更大的问题,要让别人听你的话,接受你的观点,同时还要对假象保持公正,对大家信守承诺,也许还需要好朋友的衷心相挺。奇怪的是,对我们来说,在复制和发明一场戏中,最难的部分是幻想本身。我们的幻想总是不如孩子的那么可信,那么有趣。我们要非常努力地练习,才能搞清幼儿园孩子的戏到底是什么。
雷娜·威尔逊教小朋友及小朋友们的老师,还有几代的大学生,每天演戏。到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让她来看今天美国幼儿中心和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她会怎么评判以课程代替游戏,来作为儿童社群生活之核心的设计呢?
“可能吗?”她也许会这么问,“现在这样,不是就把功课当作小孩的戏了吗?不,这绝对不可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注意观察,注意倾听我们的孩子,我们早已忘记自己身为孩童的感受了。”
然而,只要我们还想让现在的孩子像雷娜·威尔逊时代的孩子一样,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和演员的话,我们还需要超越观察、倾听和记忆的课程。我们不但要记录他们的语言、知识和表达,还要将它们变成戏,演出来。我的目标就是要检验幼儿课程本身的自然形态,以及孩子们通过游戏对彼此进行的研究和探索。
如果我叙述的这些故事能来回穿梭于几代人之间,那定是由于这种幻想游戏(fantasy play)一直都令人心醉神迷的缘故。在妮莎·罗培生(Nisha Ruparel-Sen)的幼儿园中,你见到的小孩和我三十年前教过的小孩,差异小得很;他们以及其他所有的小孩,他们的游戏,他们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这些记叙会一直继续下去。这些小孩是我认识的最有创新性的研究者,他们在回答雷娜·威尔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游戏称作孩子的功课?”
此外,我们为什么不把游戏也称作是老师的功课呢?正如同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所说,孩子们在游戏中的行为表现会比平时杰出。就让我们这些幼儿教师们寻求各种方法,紧紧跟随孩子们的脚步,从阶梯的第一级开始,不断向上攀登。正如所有孩子都知道的,那就是幻想游戏。
游戏的语言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游戏是王,而童年是这个王的领土,在这个王国里,“幻想”是公开使用且被使用最多的唯一官方语言,而那种独特的语言如今仍然在妮莎·罗培生老师的幼儿园里使用着!
“啊——哟——!水啊,水啊!假装我们在埃及走路,那里没有水,可是,我们看见一条大河。”
“咕噜,咕噜,咕噜,快来啊!喝水啊!”
“糟了,我掉到水里了,救命啊,救命啊!等一下,注意看,有牛蛙在跳,跳好高,比世贸中心大楼还要高!他活不了了,那里没虫子吃了,嘿,怎么回事!”
“爆炸了,跳走,快跳走,跳回河流,牛蛙烧着了。快,我们快游,不要被火烧到,游快点儿,呼,我把你救出来了!”
孩子们游到安全地带,远离爆炸的牛蛙,他们聊起天来,聊的是世贸中心大楼的悲剧。
维杰,一个印度孩子,他刚刚来到罗培生老师的班级。他还没开始和其他的孩子玩,可是,他注意听着积木区那边的孩子谈他们的幻想游戏;他们正在小声地对玩具说着话,而他则手拿玩具飞机绕着积木区转圈圈。
“嘿,你要炸我们吗?”金发小男孩问他。小男孩正在重建刚刚爆炸的积木大楼。这句话像是一句很礼貌的邀请。可是,维杰摇摇头,他还不想那么直接地采取行动。他应该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融入这个班级的文化,融入大家的童年世界。他走到故事桌的旁边,坐了下来。
“我有一个故事,”维杰轻声说,他的老师却吃了一惊,她此时正坐在故事桌边书写孩子们跟她说的故事。这是维杰第一次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主动表示要说故事。刚刚他在积木区并没有对那些正在堆积建筑物、堆积大厦的孩子们说他的故事。在学校里,现在不说的话,就再没有其他地方好说了,说不定只得等到回家才有机会说了,而且,到时候很可能没有人听他说。显然,他等不及了,他的故事现在就要说,话自然从他口中冲撞而出。
“这是一架飞机,”他开始了,“它飞到奥黑尔机场(O'Hare,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全世界最忙碌的机场之一)去载我爷爷,那是去年,那时,我的奶奶在金奈(印度城市),后来她去印度;后来我们去威斯汀酒店大楼,后来这架飞机撞毁了奥黑尔机场,撞进了威斯汀酒店大楼,接下来,他们来修飞机,他们也修了一些人,修好了,他们都回家去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修大楼,大楼起火了,一直烧。”
罗培生老师一脸认真地看着维杰,“表演这个故事时,你要演谁?”她问。在这个班,被说出来并且记录下来的故事只能算是半成品。要成为完整的故事,得在一个假装的舞台上,在其他同学的协助之下,当演员的当演员,当观众的当观众,要把故事演出来,故事才算完成。老师是导演,老师也当旁白的人。
“那架飞机,”维杰说。当时,他不断地把玩着手上的玩具飞机,来来回回地在桌上飞着。他玩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你知道维杰(Vijay)的意思吗?是胜利(Victory)的意思。”
“维杰的意思是胜利呀?真高兴你告诉我这个。” 妮莎·罗培生老师还想多知道一点儿,“我们会看到飞机修复的过程吗?我们会看到人被救助、被治疗的过程吗?”
“会。”维杰说,“我们怎么称呼修理的人?”
“机械师,好吗?”老师建议。
他点点头,“有一个医生救人,还有一辆救护车,还有救火的人,不过,不要大声吵闹。”
罗培生老师记下那些附加的说明。“胜利,”她重复着,“在你的故事里,当那些人回家的时候,又是一次胜利了。”
果思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在维杰的纸张旁边玩一个小小的超级英雄人偶。“你要放一个霸王龙在你的故事里吗?”他问,“他也会是一个胜利,我保证。”维杰摇头,不过两个男孩同时默默注视着那个玩偶,那个玩偶像是拥有了恐龙的威力。
果思知道维杰要表达的主题。他来自希腊,和维杰一样,他也有很多亲戚常常坐飞机飞来美国,住在高级酒店里。果思能够更好地在飞机失事与他自己之间放置一个虚构的角色,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娃娃角和积木区玩得比较久,有过练习的缘故。在那两个角落,每天都在表演故事,问题与解释每天都是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着。
轮到果思说故事让老师来记录的时候,他重新拾起他同学的主题,仿佛他们谈起话来了。“从前,有一架飞机,载着人,但是它飞得太快。这时,霸王龙出现了,他跳上跳下,飞机就撞到他了,但是,他比飞机强壮。后来,飞机里的人跳出来,跳到霸王龙头上,他的头用力摇摆,把他们都抖到水里去,他们都很会游泳。后来,他们都睡着了,他们的夹克就是他们的枕头。”
在罗培生老师的班上,平常故事演出很少用道具。可是,当霸王龙的故事演出时,参与演出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跑去拿他们的夹克来,仔细地叠好当作枕头。那一刻,语言在表演中可有可无。于是,有关“九一一事件”的谈话开始了,他们将事件编进他们的故事与幻想游戏里。大人们可能常常谈论那段恐怖的时期,有关的报道也一再出现,电视不断地回放那些画面,但是孩子们必须要有能力想象自己游到安全的地带,用他们自己的夹克当枕头。
接下来的那几天,孩子们一再重演维杰及果思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样的情节,总是会有一架飞机撞机,接着,孩子们就会跑去拿他们的夹克。接下来那个星期,维杰成了娃娃角里的爷爷,飞机撞机的事已经被抛到一边儿去了。
我们称之为幻想游戏的活动是多么让人惊讶的发明呀!我们真的愿意让它就这样从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消失吗?“如果我的老师们没办法掌控这一切,我就不想再鼓励幻想游戏之类的活动了。”最近有一位托儿所的主任这么表示,“如果老师会怕幻想游戏进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状况,尤其是四、五岁孩子的班级,那就不要做,只要按照课程计划与活动方案上课,大家就都会好过一些。”
“游戏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我问。
“老师们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是由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紧张情绪升高,孩子们看上去慌张不安,感到危险。所以在孩子熟悉的地方,按照原先计划好的课程上课,会让他们感觉更加安全可靠。”
关于这一点,我持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活动比幻想游戏更能让他们随时都准备好的了;没有什么活动比幻想游戏更可靠、更不带危险性。而且游戏中的危险也只是想象的,假装的。将人类最古老、最好用的学习工具——幻想游戏——如此大张旗鼓地定义为非法,弃而不用,那才是危险的事呀!
在接下来的论述里,我对幻想游戏的关注看起来可能会“压倒”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开设的其他领域的课程。但是我并不会脱离这些课程来强调幻想游戏,我不会放弃被我们一读再读直至铭记在心的书籍,不会放弃被我们一玩再玩并能扩展我们视野和技能的游戏,也不会放弃可以为我们的情感增添节奏和韵律的音乐和诗歌。
但是,不管如何,幻想游戏是强力胶,将我们其他所有的追求和努力都结合在一起。我不得不将它们展示出来,尽可能说明白、讲清楚。我以前的一位编辑常常对我说:“你的书,焦点是什么?在哪里提到了什么样的成长?”在这里,聚焦之处就是孩子的戏剧化的幻想游戏。至于其成长的部分,我想要写的其实是我个人的成长。
在孩子们设定幻想游戏的主题、人物和情节的过程里,他们会解释自己的思维,也能使作为老师的我们惊讶于自己的变化。如果说幻想游戏是可以为提高幼儿的认知、叙述和社交能力提供营养的温床,那么最能代表幼儿自然发展状况的早期学校经历则是我们与孩子们共同事业的舞台。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