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不仅在基因领域,更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最近,《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30周年版的基础上,新增了道金斯对于争议的回应,更加完善了其论述。本文为《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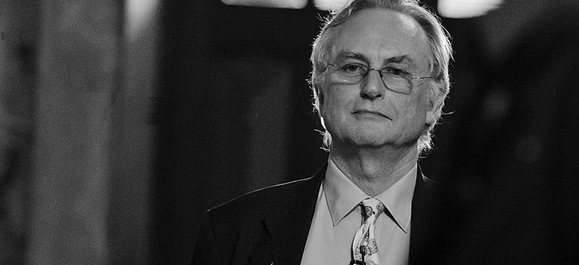
理查德·道金斯
科学家与政客不同,能够以错为乐。政客如果改变了主张,会被人说成是“ 反复无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就夸口说自己“从未开过倒车”。科学家一般来说也愿意看到自己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偶尔一两次的错判同样能够为自己赢得尊重,尤其是当他们能够优雅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位科学家被指责为反复无常。
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愿意找到一种方式来收回《自私的基因》一书的核心思想。在基因组学的世界中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激动人心的事情, 那么一本出版于40年前的以基因为题的书如果还不至于被彻底摒弃的话,必然需要接受大幅度的修改—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很是诱人。然而在这本书中,“基因”的定义比较特殊,它是为进化量身定做的,而不以描述发育问题为目的—若非如此,这本书就真要大改特改了。

本书中基因的定义来自种群进化生物学家乔治·C.威廉斯, 他已然仙逝,但无疑是本书的英雄。同样离我们而去的还有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比尔·汉密尔顿。威廉斯认为:“基因是染色体材料上任何一个可能存在得足够长久的代际,并且是可以当作自然选择的单位的部分。”我从这个定义中得出了一个多少有些好笑的结论:“严格来讲,这本书的书名应该是……《染色体有点自私的一大部分以及更为自私的一小部分》。”胚胎学家关心的是基因会如何影响表型,我们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关注点则是实体在种群中的频度发生的改变。这些实体在威廉斯看来就是基因(威廉斯后来称之为“ 抄本”)。基因是可以计数的, 而其出现频度是其成功与否的一种测度。
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生物个体不具备上述讨论的基础。单个生物体的基因频度都是100%,因而无法“当作自然选择的单位”。同样,复制单元也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如果非要说生物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单位,这其中的意味也很不一样,实际上是把生物个体视为基因的“载具”。生物个体成功与否的测度是其所携带的基因在未来代际中出现的频度,而其奋力去争取最大化的那个量值是汉密尔顿所说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
一个基因要获得这些数值层面的成功,就需要在生物个体身上表现出表型效应的价值来。一个成功的基因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表现在许多个体身上,它能够帮助这些个体在环境中存活得足够长久,令繁育下一代成为可能。不过,这里的环境指的并不仅仅是身体之外的外部环境,诸如树木、水体、天敌等等,其实还包括了内部环境,特别是其他基因—自私的基因与其他基因共享了一系列生物个体的身体,不仅遍布种群,而且跨越代际。由此,必然的结果是,自然选择会青睐那些在有性繁殖种群中其他基因的陪伴下共同繁荣的基因。从本书的主张来讲,基因的确是“ 自私的”。但基因同时也能够与其他基因合作,它们所共享的不仅仅只是某一个特定的生物体的身体,还是这个物种的基因库所产生出来的一般意义上的所有身体。一个有性繁殖种群是由相互兼容、彼此合作的基因所组成的联合体—它们今天会合作是由于许多世代以来在先祖类似身体中的合作已经让它们得以繁荣。需要了解的重点在于(这一点常常被人误解),合作性之所以得到青睐,并非是因为一组基因天然地作为一个整体接受选择,而是因为单个基因是单独接受选择的,但这个选择过程的背景是该基因在身体内有可能接触到的其他基因,也就是说物种的基因库内的其他基因。一个有性繁殖物种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从基因库中抽取自己的基因的。在一系列个体的身体里,这一物种(而非其他物种)的这些基因会不断地彼此相遇,彼此合作。
我们仍不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有性繁殖的起源。但是有性繁殖的一个结果就是,物种可以被创新性地定义为:相互兼容的基因所组成的合作联合体的栖息地。正如在《基因的延伸》这一章所指出的: 合作的关键在于,对于每一代而言,一个身体里所有基因共享的那个去往未来的出路如同“ 瓶颈”一般—那是它们渴望搭乘着前往下一代的精子或卵子。“ 合作的基因”也是一个同样恰当的书名,而且如此一来, 这本书就根本不用做任何修改了,我估计人们因误解提出的许多质疑也可以因此而避免了。
另一个不错的书名是“不朽的基因”。“不朽”比“自私”更有诗意,同时也抓住了本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DNA(脱氧核糖核酸)复制的高保真度对于自然选择而言是一个基本要素,也就是说突变是罕见的。高保真度意味着,基因作为准确的信息拷贝能够存续数百万年之久, 成功的基因如此,不成功的基因则不行—而这正是成功性的定义。不过,如果一段遗传信息可能的生命周期很短的话,两者的差异就不会很显著。换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活着的生物个体从其胚胎发育期开始就是由一些基因建造出来的,而这些基因能够追溯到许多许多代际以前的许多许多祖先个体身上。活着的生物继承了这些曾经帮助过许多许多祖先存活下来的基因,这就是为什么活着的生物具备存活下去所需的一切, 并且能够繁衍下去。它们所需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是因物种不同而各异的—捕猎者或是猎物,寄生虫或是宿主,水生或是陆生,栖息在地下或是森林的树冠层—但是普遍性的原则仍是相同的。
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由我的朋友,伟大的比尔·汉密尔顿提出并完善的。我至今仍在为他的离世感到哀痛。我们认为动物应该不仅仅要照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照料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对此,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简洁的表述方式,就是“汉密尔顿法则”:如果一个利他性的基因能够在种群中扩散开来,那么必然满足以下条件,即利他者的成本C要小于受益者获得的价值B与两者之间的亲缘度系数r之积。这里的r是一个介于0与1之间的比例。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r的取值是1,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则是0.5,孙子孙女、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 以及同胞兄弟姐妹的孩子是0.25,同胞兄弟姐妹生出来的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间则是0.125。但什么情况下r是0呢?在这种定义之下,0的含义是什么?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会更困难一些,但的确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自私的基因》第一版中没有完全给予阐明。0并不意味着两个个体没有共同的基因。
所有人类之间共享着超过99%的基因,人与老鼠也有超过90%相同的基因,与鱼有四分之三相同的基因。这些相当高的比例令许多人对于亲属选择产生了误解,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上面这些数字并非是r的含义。比如说我与我兄弟之间的r值是0.5,那么我与种群背景之中一个可能会与我竞争的任意成员之间的r值就是0。为了对利他主义的进化进行理论化的分析,堂兄弟姐妹之间的r值为0.125只是在与种群参照背景(r=0)相比较的情况下选取的。这里的参照背景是指种群中其余的个体,利他主义可能也曾在他们身上体现过:虽然面对食物和空间时是竞争对手,但面对物种的生存环境时是历经久远历史的伙伴。这些数值,0.5或是0.125等,指代的是在亲缘关系趋近于零的种群参照背景之上的额外的亲缘关系。
威廉斯所定义的基因是一种可以计数的东西,你可以随着一个物种的代际更替去计算它的数量变化,这无关其分子层面上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基因的本质是被基本呈惰性的“内含子”(会被翻译机器忽略)分隔的一系列“外显子”(被表达的部分),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威廉斯所定义的基因。分子基因组学是一个迷人的领域,但是它并未对进化的“基因视角”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这种视角正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换个说法:《自私的基因》的观点很可能对于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也是能够成立的,即便那些星球上的基因与DNA毫无关系。不过,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具体内容,以及关于DNA的具体研究成果,是可以有办法纳入基因视角之中的。结果你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证明了我关于生命的观点的正确性,而非对其产生怀疑。对于这一点,我会稍后再继续探讨。而现在,我要换个跨度有点大的话题, 它始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然能够代表一大票类似的疑问。
你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I)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多近?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是她的十五重堂兄弟姐妹的孙辈。我们共同的祖先是第三代约克公爵理查·金雀花(Richard Plantagenet,1412— 1460)。理查的儿子之一是英王爱德华四世(King Edward IV),伊丽莎白女王是他的后代。理查还有一个儿子是克拉伦斯公爵乔治(George, 传说是在一桶烈性白葡萄甜酒中淹死的),我是他的后代。很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自己与女王的亲缘关系其实比十五重还近,我亦如此,门口的邮递员也是如此。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成为某个人的远房表亲, 或者让我们都成为彼此的亲戚。我知道自己是妻子的十二重堂兄弟姐妹的孙辈(共同祖先是乔治·黑斯廷,第一代亨廷顿伯爵,1488—1544),但是很有可能我们还能通过某种未知的不同方式成为血缘关系更近的亲戚(从各自祖先查下来的不同路径),而且绝对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让我们成为血缘关系更远的亲戚。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你和女王可能既是九重堂兄弟姐妹的六世孙辈,又是二十重堂兄弟姐妹的玄孙辈,还是三十重堂兄弟姐妹的八世孙辈。我们所有人,无论生活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不仅仅是彼此的远房亲戚,而且还有几百种连接亲缘关系的路径。这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所有人都是种群的背景,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r趋近于零。我可以依照有据可查的一条路径去计算自己与女王之间的r值,但是根据r值的定义,最终算出来的数值会非常接近于零,因而完全起不了什么作用。
导致所有这些令人头昏脑涨的多重亲缘关系的原因在于性。我们有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越往上越多,近乎天文数字。如果你不断乘以2,一直计算到征服者威廉的年代,你的(以及我的、女王的、邮递员的)祖先数量将至少是个十亿数量级的数字,比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数量还多。这个计算本身就证明,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共同拥有许多祖先(如果回溯到足够久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彼此也是很多不同形式的亲戚。
如果你不是从生物个体的视角(生物学家的传统视角),而是从基因的视角(这一整本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提倡这种视角)来看待亲缘关系这件事情的话,所有这些复杂性就都不存在了。不要再问我与我的妻子(或邮递员,或女王)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相反,要从单独一个基因的视角来提问,比如我的蓝眼基因:我的蓝眼基因与邮递员的蓝眼基因有什么关系?像ABO血型系统这样的多态性可以回溯到久远的过去,甚至连猿类和猴子也有同样的系统。站在人类A型血的基因的立场上看,黑猩猩身上与之对应的基因是其近亲,而人类的B型血基因反而亲缘关系更远。在Y染色体上的SRY基因决定着动物个体是否是雄性。我的SRY基因会把一只袋鼠的SRY基因“ 看作”近亲。
或者,我们还可以从线粒体的视角来看待亲缘关系的问题。线粒体是充斥在我们细胞之中的小东西,攸关生死。它们是无性繁殖的,保留了自己残存的基因组(它们与自由生活的细菌有极远的亲缘关系)。根据威廉斯的定义,一个线粒体的基因组可以被看作一个单一的“ 基因”。我们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得线粒体。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的线粒体与女王的线粒体有怎样的亲缘关系,那么只会有一个答案。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她的线粒体与你的线粒体之间成为亲戚的方式只有一种,而非从整个身体的视角来看时的几百种不同方式。你可以一代一代回溯你的祖先,但是只能沿着母亲这条线回溯, 你会得到一条单一的(线粒体的)细线,而非不断分支的“ 整体生物家谱”。你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回溯女王的祖先,追踪她的那条母系细线。迟早,这两条线会彼此相遇,此时只要数数每条线上过了多少代,你就能轻易计算出你与女王的线粒体亲缘关系了。

你能在线粒体上做的操作,理论上也可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基因上重复,这就显示出了基因视角与生物体视角的不同。从整个生物个体的视角来看,你有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等等。但是, 每个基因就像线粒体一样,只有一位父母辈,一位祖父母辈,一位曾祖父母辈,等等。我有一个蓝眼基因,女王则有两个。理论上,我们能够回溯基因的代际,找到我的蓝眼基因与女王的每一个蓝眼基因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两个基因的共同祖先被称为“聚结点”。聚结分析已经成为遗传学的一个繁盛分支,而且非常吸引人。你看出来了吗?这与整本书都在宣扬的“基因视角”是多么相得益彰啊!我们已经不是在谈论利他主义了。基因视角在其他领域也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比如在寻找祖先这件事情上。
你甚至可以去分析一个生物个体的身体里两个等位基因之间的聚结点。查尔斯王子也有蓝色的眼睛,我们可以假定他的15号染色体上有一对不同的蓝眼等位基因。查尔斯王子的两个蓝眼基因分别来自他的父母,这两个基因之间有多近的亲缘关系呢?对此,我们知道一个可能的答案,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室的家谱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家谱记录得更为详尽。维多利亚女王也有蓝眼,而查尔斯王子可以有两种方式算作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从他母亲那边通过国王爱德华七世来算,或从他父亲那边通过黑森的爱丽丝公主来算。有50%的可能性,维多利亚的一个蓝眼基因剥离出了两个拷贝,一个给了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另一个给了她的女儿爱丽丝公主。这两个子代基因更进一步的拷贝很容易一代代传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身上,从而在查尔斯王子身上重新组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查尔斯两个基因的“ 聚结点”是维多利亚女王。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查尔斯的两个蓝眼基因是否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说,他的很多对等位基因肯定都会回溯到维多利亚女王身上聚结。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你的一对对基因和我的一对对基因。即便我们可能没有查尔斯王子那样清晰记录下来的族谱可供查询, 但是你的任何一对等位基因理论上也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祖先,那就是它们从一个单一先祖基因上“剥离”开的聚结点。
下面要说的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无法找到自己任何一对特定等位基因的确切聚结点,但是理论上来说,遗传学家们能够对任何一个个体身上的所有对等位基因做聚结点的分析,考虑历史上所有可能的亲缘路径(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可能路径,因为实在太多了,所以只能是抽取一个统计上的样本),从而得出这个个体整个基因组的聚结模式。位于剑桥的桑格研究所的李恒(Heng Li)和理查德·德宾(Richard Durbin)发现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一个单一个体的基因组中所有成对等位基因的聚结模式就可以给我们足够多的信息,让我们得以重建其整个物种在之前历史中的种群统计学细节,确定那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
在我们关于成对基因聚结的讨论中,两个等位基因中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这里“基因”的含义比分子生物学家所说的基因更为灵活一些。实际上,你可以说聚结遗传学家回归到了一个概念上,有点类似于我之前所说的“染色体有点自私的一大部分以及更为自私的一小部分”。聚结分析研究的对象是一块块的DNA序列,它可能比分子生物学家所理解的单个基因更大,也可能甚至更小,但是它们仍旧能被视为彼此的亲戚,是从一个有限数量的世代之前的共同祖先那里“ 剥离”出来的。当一个(上述意义上的)基因“剥离”成为自己的两个拷贝,并分
别传给两个子女时,这两个拷贝的后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不同的突变。这些突变可能是“ 不会被注意到的”,因为它们不会表现为表型上的区别。两者之间突变的差异与分离之后经历的时间是成正比的。这一事实,也就是所谓的“分子时钟”,已经被生物学家们很好地利用起来了,可以测量巨大的时间跨度。此外,我们去计算亲缘关系的这些成对基因不一定要有着相同的表型效应。我有一个来自父亲的蓝眼基因, 与之成对的等位基因则是来自母亲的棕眼基因。虽然这些基因不同,但它们必定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有一个聚结点:在那个时刻,我父母的共同祖先的一个特定基因剥离成了两个拷贝,分别传给了这位祖先的两个孩子。这次聚结(不同于维多利亚女王蓝眼基因的两个拷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从而让这对基因有足够长久的时间来积累差异,尤其是导致不同眼睛颜色的差异。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