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汉松与新作《以读攻读》
“用读《甄嬛传》的速度读文学作品是绝大的错误,好的文学不是在晃动的地铁车厢和咖啡店可以阅读的。好的阅读过程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艰苦的、复杂的,如同一次战斗,充满危险、死亡和伤痛,有时候会被杀得片甲不存。”2017年末,在思南文学之家新书《以读攻读》的活动现场,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但汉松这样向人们提示阅读的艰难和危险。
但汉松长期教授的两门课程是“美国文学”和“英美文学研究”。 在南大的课堂上,他开出的阅读书目会被学生们抱怨,“老师你选的怎么都是这些东西,读起来都让人挺难受的。”对此,但汉松回应说,“伟大的文学都是给你一刀的。从霍桑、梅尔维尔、亨利·詹姆斯、伍尔夫都是这样。”文学阅读的“危险性”就在于,它能够揭示普通人看似岁月静好、意气风发之下的绝境深渊,帮助人们察觉自己内心的幽微之处。“很多人看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会觉得自己就是艾玛,只是还没出轨而已;看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会觉得自己是娜拉,只不过还没出走而已。文学家将人们生命中的故事偷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将这些故事复活。”
相比本名但汉松,他的微博名“洛之秋”更为人所熟知。在微博上,他有十万粉丝,也经常点评新闻、分享日常,或与粉丝互动。译林出版社日前出版了他的新书 《以读攻读》,他微博如今的置顶文章题为《致我可能的读者们》,他写道:“(这本书)绝不是一本某些读者望文生义期待的那种文学阅读方法手册或指南……我并不打算手把手教会大家如何读,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文学阅读,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甚至也不应该遵循什么方法套路,唯一有效的方式是一行一行、逐字逐句地读下去,让自己的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与文本去冲突、碰撞。”

《以读攻读》
但汉松 著
译林出版社 2017年9月
在一次次重访经典作品的持久“战斗”里,但汉松以读者、教师与作者“三位一体”来要求自己: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好的阅读者,向学生讲授文学阅读的方法,也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论述自己的阅读——也就是说,阅读需要反复地训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书的自序中,他这样说道,“如果说伟大的文学,往往教会我们去习惯于停留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道德的含混中,那么好的阅读则完全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
文学贸易差之下,中国作家会被误读
作为在中国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学的学者,但汉松对于中西文学“贸易差”有着深切的体会。在这本书收录的一篇题为《文学的世界旅行》的文章中,他指出,“国内媒体的各种年终荐书排行榜,十之八九都是从欧美图书市场引进的译本……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贸易不过是西方文学独大的顺差模式。”而反观美国图书市场,翻译图书在1990年代所占的比例连百分之十都不到,文学翻译更是低到百分之三。
中西文学之间“贸易差”这种说法并不是但汉松的发明。早在1827年,歌德就曾在致于卡莱尔的信中说,跨文化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如同不同国家货币的交换。同年,歌德预言道,随着文学交易不断深入,“世界文学”终会出现。如今,我们在图书市场上确实看到了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莫言也参与到了世界诺贝尔文学大师的行伍中。但汉松却担忧,中西文学进出口严重的不平衡正在抹平各国文学的差异与多样性——中国作家学习的是西方师傅,中国批评家的工具也是西方尺子,西方对于中国作家的艺术水准也会有失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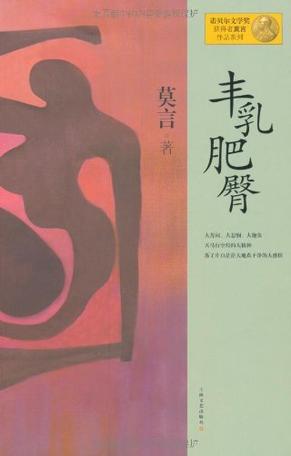
《丰乳肥臀》
莫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
厄普代克对于莫言的著名“误读”便是一例。2005年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丰乳肥臀》的书评,“厄普代克困惑的,是莫言那种魔幻现实背后毫无节制的密集修辞,是那些夸张到令人不安的文学譬喻……”,由此,厄普代克猜测中国小说没有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那样学会“得体”。在但汉松看来,这种揣度其实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当厄普代克以乔治·艾露特或者狄更斯式的“得体”作为世界文学跨界交换的“汇率”标准,自然对莫言的高密说书产生“不够得体”的判断。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授奖词“hallucinatory realism”(国内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也暗示着一种“与疾病有关的诊断”。
在互联网时代,阅读品钦反而变得容易了
在以“以读攻读”为题的现场活动上,文学编辑黄昱宁、上海作家小白和但汉松都“巧妙”地避开了讨论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或者是唐·德里罗等——这些屡次出现在《以读攻读》中的作家名字,似乎反而凸显了书中提及的“阅读之难”:阅读已经如此困难了,我们为何还要把读者吓走呢?
在但汉松看来,阅读的难中之难莫过于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但汉松对品钦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是读者和研究者,另一方面,他也是品钦的中文译者。他翻译了《性本恶》和《慢慢学》两本书,深受品钦的句式、词语和知识背景“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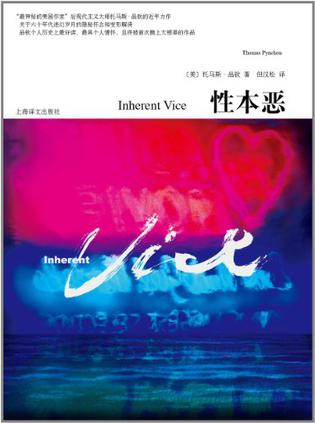
《性本恶》
托马斯·品钦 著 但汉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
有意思的是,据但汉松观察,对于像品钦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学院派和普通读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学院派“很喜欢”这样的作品,单是给《万有引力之虹》做的导读就有四五本,还有不少人凭借研究品钦小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或终身教职。而另一方面,习惯在星巴克和机场阅读的普通读者却将之视作梦魇。最为讽刺的是,就连有些为品钦作品评奖的专业评审也曾袒露,自己虽然很努力地去读,也只读完了三分之一——“这也是委员会在1974年坚决反对授予此书年度小说奖的原因”。
我们如何才能读懂品钦?但汉松戏谑地写道,需要精通英文的基础上,熟悉相当程度的德文、法文,还要会一些俄语、南非荷兰文,还要博闻多学,最好了解巴甫洛夫心理学、统计学、材料学、控制论、空气动力学、宗教学、音乐学等等。“最让人抓狂的是,品钦从来不是简单运用这些文学或非文学素材,也不会在叙事中稍缓片刻给你解释掌故或进行科普。品钦不认为自己作品的晦涩是个缺点,因为不忍卒读是读者自己的罪过。”所以说,要读品钦,就要先接受他的这种“作者-读者”契约,接受这种“自虐式的”阅读。
在互联网时代,阅读品钦反而变得容易了。人们可以通过检索发现文本的蛛丝马迹,例如毒品的各类别名、影视剧的典故、流行乐队的行话,还可以通过“品钦维基”阅读分享每一本小说的注释;甚至可以在谷歌地图中找到主人公所在的洛杉矶海滨小镇,还可以用网络搜索书中提到的音乐曲目,看看同步显示的歌词,揣测它们在文中的意义。”阅读品钦,就是浸入庞大的细节当中,但汉松说,这种阅读可以训练读者“像猎狗一样,去文本中对细节进行侦察”。
文学改编电影, 抒情性无法再现
《以读攻读》一书中不仅有对于品钦、莫言的阅读,还有流行的电影作品的品鉴。在文学名著改编电影方面,但汉松认为自己不是“小说原教旨主义者”(注:指唯小说至上,不赞同任何影视化改编的人),但也特别指出,像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杰作是无法被电影改编的。因为小说具有独特的抒情性与视觉性,电影无法再现。在他看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本不仅有虚构叙事的功能,还可以看作乐谱和自由诗:《盖茨比》里“词语的重音或爆破、诗行内部的音步或重复、诗节之间的押韵或停顿”都隐藏着自己的旋律。此外,“菲茨杰拉德的抒情格调和曼妙文风恰恰对应于他笔下那个喧嚣时代的香艳奢华和靡靡之音”——而这些长处,没有哪一种摄影机或者演员可以表现出来。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 著 姚乃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至于小说呈现的“视觉性”,表现为小说家对于细节的绝对掌控,也可以更加完美地引导读者去看什么,以及忽视什么。但汉松引用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的话,这样讲道,“文学与生活的区别在于,生活充满了太多形态不固定的细节,很少能引领我们去关注它,而文学能教会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导演虽然也可以用镜头的伸缩与运动来调动人们的注意力,却无法控制人们关注的重点。毕竟电影里的细节太多了:男主角的钻石手表、茶几上的马卡龙、角落里的旧书,人们到底先看到哪个、后看到哪个,导演是完全无法把握的。更为重要的是,但汉松认为,《盖茨比》中的框架叙事特色,即将故事嵌入人物叙事、让读者与故事人物保持距离的做法,也会在这样的电影改编中消失殆尽:电影中的叙事者“我”沦为配角,盖茨比的悲剧故事也丧失了原有的寓言意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