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容易把读书人想象成这样:不接地气,沉默寡言且独来独往。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书籍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Books)一书中,作者艾比盖尔·威廉斯(Abigail Williams)告诉我们,在18世纪的英格兰,曾经掀起一股共读的热潮。那时候,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出版业的兴起及专业作家群体的诞生,阅读成为了民间流行的消遣方式,参与者通常爱好大声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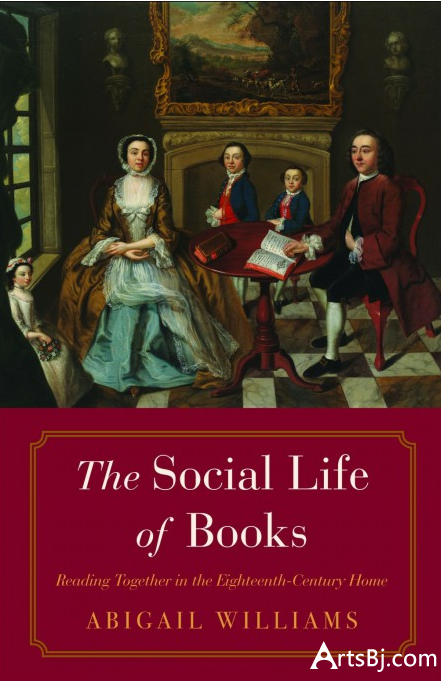
《书籍的社会生活》
威廉斯现执教于牛津大学,她指出: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看,世界已充斥着各种娱乐八卦和信息爆炸,“难以体会早年间读者曾经有过的那种喜悦,他们但凡有机会读到一本新书,都会十分兴奋。” 此外,在当今想要成为一名读书人,也不再需要“正规的古典教育,或是海量的图书馆资源”了。
当时,作家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dison)在《观察者》(Spectator)杂志上指出:读书文化“发端于藏书室、图书馆、学校和大学,并广泛存在于俱乐部、大型集会、茶座和咖啡馆当中”,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什么采取大声朗读的方式?理由多种多样。首先,那时蜡烛很贵,至少不比书便宜。其次,在现代眼科医学诞生以前,视力不好的人的确只能“听书”。早期的学者们挤在图书馆小单间里读书的场景,其实与我们这个时代里一家人一起弹钢琴或看电视是差不多的。
威廉斯的研究十分出色,以巧妙的笔法令读者身临其境,仿佛回到了18世纪英国的商贩、工人、店主、教士及其妻儿的日常生活当中。她分析了阅读是如何成为一项“观赏性体育活动”的(spectator sport)。当然,如同其他任何类型的演出活动一般,参与阅读的人必须做适当的准备工作,这又引发了一波为读书人撰写指导手册的小高潮,进而促成了一个威廉斯称之为“演讲艺术的伟大时代”,那时几乎所有英国人都深深地“迷恋于学习如何大声朗读”。商贩们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滔滔不绝俱乐部”,并借助诸如《新编口若悬河者学习伴侣》(The New Spouter's Companion)或是《动情的演说家》(The Sentimental Spouter)等练习手册,希望把自己锻炼成优秀的公共演说家。在公共领域中通常遭到冷遇的女性,那时也设法在家中进行这样的练习,以便与家人或朋友吟诗作对,借此在从事编织或清洁壁炉等家务劳动之余放松一番。
这些手册甚至细致到了规定应当如何皱眉来表达“恐惧情感”的程度,这在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法国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曾被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盛赞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法国艺术家”——译者注)对人物头部的描绘中也有所体现,展现了灵魂所具有的各种激情。而当时的另一位艺术家约书亚·斯蒂勒(Joshua Steele)则写出了《理性的韵律》(Prosodia Rationalis),试图专门为演说术发展出一套音乐符号,注明应有的抑扬顿挫,使演说变得如同演奏某种乐器一般。威廉斯指出:“想要在18世纪做一个优秀的读书人,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困难得多。”
在真正的英式风尚中,这样一本正经的态度很快就会遭人讽刺挖苦,例如亚历山大·史蒂文斯(Alexander Stevens)当时就举办活动对此进行了恶搞,主题是讨论“彗星抛物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黄瓜的生长发育”,以此来检验辩论者是否真的拥有过人的口才。那个时代的人对表演细节的纠缠可以说到了强迫症的程度,这样的恶搞无疑是富有一点挑衅意味的。
《书籍的社会生活》作者艾比盖尔·威廉斯
文化繁荣与建筑空间的开放是几乎同步的。成长中的商人阶级拥有了更加宽敞的住宅,而这些住宅又需要图书室,因此还掀起了一股与书籍相关的家具的消费热潮,其中就包括各式各样的书柜或书橱:有适用于女性用户的花哨设计,有做得像山形墙(pediment)或是带有垛口的(embattled)城墙的款式,还有哥特式风格等等可供选择,而书桌以及其它一些用来展示书籍用的家具在当时也是消费宠儿。一间有着一定规模的图书室的豪宅,不仅能服务到主人的家庭,也能辐射到周边的一些村庄。
与此同时,默读(silent reading)这种活动也不再仅限于客厅或书房范围内。威廉斯在研究中讲述了一个石匠的故事,他“将自己的马训练得熟悉行程路径,以便能够在旅途中安心读书”,许多女性也在理发的短暂空闲时间读书,这使得“书籍封面经常被脂粉污损,书页之间经常有润发油的痕迹”。如同现在一般,由于书籍的便携性得到改善,许多旅人得以在短暂的出差时间中多少读一点东西,正如我们现代人出游时通常会“带一本小说或是iPod/iPad来打发时间”。
威廉斯还提到了一些当时的趣闻:仆人趁其不备偷走主人书籍;物理学家托马斯·博德勒(Thomas Bowdler)为了不让家里小孩接触莎士比亚著作中“有伤风化”的部分,煞费苦心地改写了一本删减版的莎翁作品集,由此留下了“博德勒化(bowdlerize,用来指代敏感词过滤这种行为——译者注)”这个词作为笑柄;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再版时去掉了所有讨人厌的数学推导;另外,人们对那些与文学作品有关的周边商品也十分追捧,譬如受到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发表于1740年的小说《帕美勒》(Pamela)的影响,“粉丝”文化逐渐形成,与之相关的扑克、茶杯、蜡像以及奶壶等产品也一度流行。透过威廉斯的研究,我们还了解到,那时的人们读书经常不按顺序或者只读自己喜欢的段落,还会把一些自己喜欢的场景或是章节抄录到公共的“涂鸦本”(commonplace books,其功能类似于当代咖啡馆或者旅店里供客人留下体验或吐槽的本子,但那时的本子在信息内容上相对没有那么随性——译者注)上,威廉斯将此与当代生活中数位化的播放列表做了对比。
《书籍的社会生活》邀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时代:闲暇增多,对知识的渴求随之高涨起来,人们的阅读习惯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威廉斯对各种掌故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她透过对各种日记、信件乃至旁注的深度发掘,为我们重构出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它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迥然不同,但又在许多关键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一个阅读方兴未艾的时代,全世界仿佛都围绕它而转动起来。
(翻译:林达)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