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朱岳的故事。

朱岳被指挥到窗前,一本正经地看向窗外。摄影/吕萌
朱岳的采访被他安排在上班时间,因为下班后和双休日他都要看小孩,他翘了两个小时的班,找了他所在的出版社的一个会议室聊天。其间照例,摄影师要给采访对象拍照,这对朱岳来说可能过于正经。
朱岳被指挥到窗前,一本正经地看向窗外,手有点不知道往哪儿放,先抱在胸前,又垂下来,一手搭在另一只胳膊上。摄影师“咔嚓咔嚓”,朱岳突然浑身一耷拉,笑了:“我绷不住了。”“放松,放松。”摄影师说。朱岳继续摆好姿势,又偷偷说了一句,“跟打针似的”。照片定格,朱岳表情有点僵硬,一手抱着胳膊,后移的发际线显得额头很亮,面前窗台上有一盆绿植,朱岳看着前方,不知是在思考植物,还是在思考窗外的远方。
哲学家:我怎么能证明 我死以后世界还依然存在?
在写小说之前,朱岳的志向是写一本哲学着作。
朱岳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自己家楼下的小花园散步,突然被一个念头慑住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怎么能证明我死以后,世界还依然存在?”那时的朱岳甚至还表达不清,那是一种很朦胧的唯我论的思考,但这个问题从此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我想,随便一个哲学问题也够我消磨掉余生的时间,实在是茫无头绪的一团乱麻。”
十几岁的朱岳有些早熟。“在十岁或十岁之前我就是个小老头儿了”,朱岳在豆瓣日记上这样写,“童年乃至学生时代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这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就经历了一些残酷的事”。
小学的时候,朱岳总是受到一位语文老师的嘲讽,这位老师还引导全班同学嘲笑他,每次语文老师叫朱岳起来回答问题,总能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我想这和我说话没有重音有关,但无论我怎么注意,总是无法获得重音。”
初中时,朱岳上的是一个校园暴力比较严重的学校。而他跑步和做操的姿势还有些滑稽,他在初中画过一个系列漫画,叫“罗圈腿与肚脐眼”,故事的主人公是他和一个外号肚脐眼的同学。后来他才知道,跑步滑稽是因为小时候打青霉素打出来一种叫做“臀大肌挛缩”的毛病。
上大学的时候,朱岳对人生还没有什么规划,父亲觉得读法律对未来的出路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朱岳读了政法系。不过大学期间他开始“不务正业”,把时间都花在了读哲学书和思考哲学问题上。毕业时,朱岳面临着两个选择,去学校当政治老师或者做一名律师。“实在是不想教政治。”于是朱岳去尝试考取律师资格证,第一次没考上,他回家专门复习了一年,第二次,考上了。
朱岳所做的律师称为“包律师”,什么五花八门的案件都做。这段经历给朱岳的感觉是——跟卡夫卡笔下的世界简直一样。“就会觉得卡夫卡那些小说是非常写实的,你觉得很荒诞或者光怪陆离,但其实那些就是处理具体案子过程中直接的体验。”他去接待信访,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城堡》里的人物。律师的工作让朱岳很烦,很焦虑,“没有一件事是高兴的”。后来他就不再接活儿,想来律师事务所也已经把他的职务注销了。
在卡夫卡式的现实中,朱岳对哲学的欲望有增无减。2002年,25岁的朱岳经亲戚介绍,揣着自己一份类似哲学论文的作品去拜访社科院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国内分析哲学的前沿人物,而分析哲学是朱岳最感兴趣的哲学领域。见到朱岳后,这位老师就说:“我已经不带研究生了,如果你想考研究生,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老师。”朱岳说:“我没打算考研究生,就是想跟您讨论来了。”朱岳在老师家与他争论了一个上午的哲学问题,老师工作繁忙,身体也不太好,最后给朱岳建议,“你可以到网上去跟人讨论”。

朱岳在思考。摄影/吕萌
求教无门,朱岳只好去网上寻找,他在网上搜各种哲学论坛,上面的内容大多是正儿八经的“民哲”。“这方面爱好的人很多都是半疯似的,自己自创体系,然后就发现了一堆特别古怪的理论”,朱岳倍感失望,但还是在一个叫“哲学人生”的论坛里发帖,问有没有人懂分析哲学。有人回帖说,黑蓝文学网有个辨析版,那儿有人懂分析哲学。黑蓝其实是个文学论坛,里面大部分是写小说和写诗的人,只是专门开出了一个小的版块讨论哲学,朱岳在那里遇到了几位同样对哲学认真而充满热忱的朋友,他们讨论中动辄争得面红耳赤,但也乐在其中。
黑蓝文学毕竟还是搞文艺的,朱岳和几个朋友觉得还是和那里的文艺青年区别开来为好,于是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哲学论坛。论坛一开始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但做着做着分析哲学就成了主要内容,朱岳说,这是因为分析哲学更强调论证、逻辑技巧和思想的清晰,拒斥胡言乱语、故弄玄虚。“根据我长期观察,在网上(且仅在网上)讨论哲学的人里,推崇分析哲学的人中头脑混乱、容易激动的较少;推崇欧陆哲学或中国哲学的人中头脑混乱、容易激动的较多。”朱岳曾在文章里写道。
不久,论坛里的帖子被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不少高校哲学系的教授注意到,论坛里的讨论有了质的提升。朱岳自己的探索也取得了进展,他完成了一篇长论文《哲学随想录》,被收入了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程广云、夏年喜主编的学术丛刊《多元·2010分析哲学卷》里。
但在这之后,朱岳放弃了写哲学着作的理想。“写完《哲学随想录》,感觉自己想说的话差不多说完了,没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了。”“而且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理论背景,也不是学术性的,完全是个人爱好的很少,你写的基本没人看,能看懂的人可能不会去看,因为他们都是学术路子的人嘛,会看到的人可能也看不懂。”2004年,朱岳改而写起了小说。
二 小说家:在经世与娱乐之外,还有一种单纯为了审美的文学
朱岳开始写小说“主要是觉得好玩”,在黑蓝文学上,朱岳认识了不少写小说的朋友,放弃哲学着作后,朱岳“集中起的脑力就像一支失去目标的大军无处发泄”,于是转移到了小说上。“小说和哲学对我来说,都有一种解开谜题的心态,这个谜题有时候另我十分不安,就像有时候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将死亡时产生的那种不安。”
在和朱岳有关的营销语中,他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确直接刺激了他写小说。刚上大学时,朱岳跟着一个总给他讲文学哲学的“奇怪”的高中同学去买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刚读到博尔赫斯时,朱岳惊讶极了,”分不清博尔赫斯写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觉得可以从博尔赫斯那里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不说废话,不迷信直接的现实主义,以及打破文本的界限:写的好像是说明文,实际上是个故事,写的诗可能是小说,写的小说也可能是诗”。
朱岳正式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垒技》,灵感来源于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微妙感觉。小说介绍“垒技”这一技艺,使用了百科全书词条式的文体,结构上模仿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现在在网上搜“垒技”,你会发现它已经成为百度百科的一个词条:“垒技是一种专门的技巧,它既不是杂技,也不是魔术。一般人几乎无法理解它的意义,但人们对它并不十分陌生。在没事的时候,常有人把扑克牌、硬币、小酒杯这类物件搭起来,这其实就是垒技的民间形态。”这是朱岳的原话,在这条定义下面,有技艺特色、历史沿革、理论与实践现状、垒技的精神主旨几部分,内容就相当于把朱岳的这篇小说拆解。“垒技”的历史被当作真实存在过,大多数人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小说家的虚构。后来朱岳又用类似的文体写了《睡觉大师》、《迷宫制造大师》等小说,介绍了睡觉、迷宫制造等种种技艺,以及一些并没有存在过的人物生平和历史。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6-08
离开律师事务所后,朱岳去了《博览群书》杂志面试,杂志社要求交几篇能证明自己文字能力的东西,朱岳就交了几篇自己写的小说上去。编辑部主任一看到就很喜欢,于是朱岳进入杂志社成为了一名编辑。《博览群书》是上世纪80年代影响较大的读书刊物,但在朱岳到来的时候,国内的读书类杂志已经普遍变得不景气,销量很低。杂志没有市场,只靠主编拉赞助维持。体会了两年纸质杂志的艰难,朱岳再次选择了离开。
杂志社的工作不用坐班,朱岳每天就一个人在家里对着电脑看稿,总觉得阴气重重。可能因为长期一个人在家宅着,身体变虚,精神也会衰弱,朱岳变得疑神疑鬼的,好像老觉得周围有许多阴魂飘荡。朱岳一跟别人说起这个,对方就会给他讲鬼故事,听越多鬼故事,他就越是疑神疑鬼。后来他坚信,只有特别自律、勤奋的人才适合不坐班的工作,但纯文学作者通常不属于此类。
朱岳理想中的工作,首先得适合社交恐惧症患者,不用跟太多人打交道,也不用太操心;其次还得有强制性,让人能过上规律的生活;另外它还应该跟书有关,图书编辑或许是最符合条件的工作。从杂志社出来,朱岳就去图书公司做了编辑,先去启真馆,然后又到新经典,到楚尘文化,到当当,然后是后浪。朱岳辗转了一家又一家图书公司,但工作性质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变。
另外一个始终没有变的是,朱岳依然在执着地思考着终极问题,尽管他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找到答案,但他还是忍不住要想。“就像机器人下棋已经超越了人类,但是人类还是要下棋,就像一篇叫《43》的科幻小说,告诉你终极答案是43,但你还是要思考为什么是43。最后我觉得我是不由自主地想,可能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想这种问题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跟玩游戏一样。”朱岳有一段时间想出了强迫症,门上锁后他得反复检查,听到别人随便说一句话,他一定要把这句话想成有开头有结尾逻辑完全通顺的一句话,遇到各种与逻辑有关的问题他都会陷进去不停地琢磨,后来强迫症是通过跑步治好的。
朱岳的小说里展现了惊人的脑洞,用他的词来说,每一篇都是一只“怪异生物”。他管自己的小说叫“文学幻想小说”,在这里,文学之于小说,就好像“科学幻想小说”里科学之于小说。他用了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这个概念,“你如果篡改一下生活形式,这个世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朱岳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会设定一个新的有些怪异的世界,比如《原路追踪》,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植物——仙人掌,只有两种动物——灰熊和兔子,而你是一个刀客,而唯一让你战斗力变强的方法,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在《说部之乱》中,一种叫做“罗曼司症”的病席卷了世界,患者的意识被不同的小说入侵,陷入梦游状态。而在《星际远征》中,几个地球人去远征某颗星球,抵达后发现那儿是某个星球设的老年人活动站,老外星人把星球让给地球人接管,唯一的请求是逢年过节给埋在那里的老外星人烧点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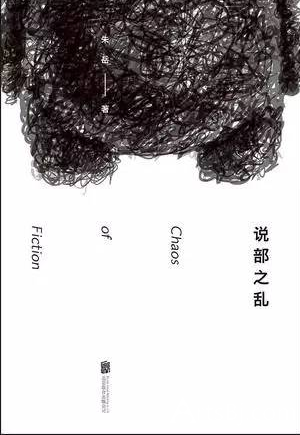
《说部之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5-03
朱岳的小说往往会违背惯常的叙述规则,往往在传统小说该高潮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发生,该情节转折的地方,没有转折。在《蒙着眼睛的旅行者》中有一篇《后记》,讲到朱岳偶然在一家小书店看到一本名为《虚构与生活形式》的书,其中作者总结了33个公式,并且声称任何短篇小说都可以根据这些公式构造出来,朱岳买下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想超越这些公式。当然这本书是朱岳虚构的,《后记》也许只是一篇叫《后记》的小说。不过朱岳确实试图超越叙述规则,“我反正特别不喜欢那种套路式的桥段,如果你都是按照已经总结好了的各种规律写,也没有什么意思。”
在几年前的一个采访中,朱岳曾经说过,自己写作“是为了摆脱绝望”。在一些小说中,确实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悲剧氛围。有一篇《我可怜的女朋友》,“我”去探望病房里的女朋友,女朋友“还剩下23根头发”,“手指被切除了,医生给她安上了10根面条”,“我搂住她枯柴般的身子,请求她不要激动,否则,连接她上下肢体的曲别针会变形的”,“我”和女朋友的蚯蚓被卖了,蛾子飞走了,最后“我”走出病房去为女朋友摘一朵玫瑰,只找到狗尾巴草。朱岳说,这篇小说他写得痛哭流涕,尽管“这些情感表达得挺怪异”。
2006年,朱岳28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在个人简介中,他是“一个像他书中大多数人物那样在现实世界中磕磕绊绊,成天在床上靠编造私人纸牌故事打发不快心情的人”。201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睡觉大师》,作家苗炜在一篇文章里讲到,出版社的编辑曾找两位着名小说家为这本书写推荐语,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其中一个问,这个叫“朱岳”的是不是神经不太正常?
2015年出版的《说部之乱》显得更加精简、准确,朱岳觉得,“在语言上它自觉度更高,已经有点章法了”。他在后记里给自己的小说做了一些附注,也作为给比他年轻的写作者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在经世与娱乐之外,还有一种单纯为了审美的文学,它比娱乐文学严肃,但不像经世文学那样有着特别的目的性。” “写诗是制造一个语言里的诗性事件,小说却是对诗性事件的模拟。”“无缘由的世界是神秘的,因其神秘而耐人寻味。”以及“写作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等,这一方法运用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朱岳这三本短篇小说集,加起来不到三十万字,花了十年的时间,他似乎的确是个低产的作家。但是他付出了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从来没停止过,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他的脑子里不断冒出各种新的想法,等到某个想法成型,就坐下开始动笔。但是朱岳写小说是越写越少,一篇小说可能一开始写了五万字,最后改成了五千字,开始五千字,最后可能只剩下了五百字。“你看到的那么一小段话,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很奇怪,最后我可能觉得那个最随意最短暂的形式是最好的。”
除了出版,朱岳的书在豆瓣阅读上也有售,有时豆瓣阅读会给他发通知:“亲爱的朱岳,你的作品正在豆瓣阅读出售。从12月1日到12月31日,作品总共销售8.00元……税后收益为7.56元……”“这似乎是一笔不错的稳定收益。”朱岳说。不过他还是收获了不少粉丝,在《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再版序言中他对读者写道:“感谢你们以一种善意的眼光看待这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是你们使我不再是一个孤独、可悲、一无是处的人。”
三 编辑:如果我有一大笔钱,就成立一个“纯文学作者职业介绍所”
朱岳两三个月前来到后浪图书公司工作,之前他是后浪的作者。后浪的办公地点在南锣鼓巷对面一个小胡同里,车不怎么进得来,人也很少。那栋楼挂的牌子是“北京市冶金设备自动化研究所”,不知道为什么后浪没有做一个自己的标识。朱岳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一个挨一个的座位中间有一个自己的工位,每天在这里看稿、联系作者、签合同。
跟和朱岳同在文学部的同事聊起朱岳,同事管他叫“会长”。“什么会长?”“秃顶会呀!”因为朱岳在豆瓣上成立了一个叫“秃顶会”的小组,自称“秃顶会圆首”,广发豆邮邀请已经秃了或者未来将秃的亲朋好友加入。“秃顶会”的宗旨是“照亮世界,最重要是秃顶们开开心心”,目前有3027名成员。前几天朱岳穿着一件自己画的秃顶会会服来上班,同事们纷纷要求团购,不过朱岳还在犹豫。
“除了秃顶,还能讲点儿关于朱岳的别的么……比如,他真的有社交恐惧症么……”“我觉得他不社交恐惧啊。”这位同事表示,“平时我们部门有一半话都是他说的。” 在同事看来,平时,朱岳就是一个脑洞特别多的人,随时会把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事儿说出来,比如他会用《推背图》来解说当今天下局势,拿同事的属相研究三合局。在维特根斯坦生日那天,朱岳提议大家一起去吃烤鸭庆祝。

穿着自己画的秃顶会会服的朱岳
不过朱岳在工作上很能发挥优势。“他的效率应该比我们高,看稿子刷刷刷就看完了。“ 一天会有好几单当当亚马逊的快递送到办公室,都是朱岳买的书,“我买的书够看好几辈子了”。朱岳知道一些奇奇怪怪的书,在豆瓣上还成立了一个小组叫“零想读”,专门推荐“想读”为零或几乎为零的书。工作时提到一些冷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的书,很多朱岳都知道。一个漫画部的同事讲,当她们要做的漫画书涉及到文学的内容,一般会去问朱岳。“他会提供一些不是资深文学粉想不到的资讯,比方说我们出了一本杰克·伦敦的原着改编的漫画《生活》,就问他怎么给这本书宣传,然后他就说村上春树和那个谁谁谁、谁谁谁,曾经在自己的小说里引用过《生活》。”
在后浪的一间小会客室里采访时,朱岳并没有表现出他在同事口中话多的一面。他比较端正地两腿叉开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腿上。“我不能翘二郎腿,臀大肌挛缩。”他笑着说。他讲自己的时候说得比较简练,但一不小心涉及到哲学,就突然收不住闸:
“维特根斯坦,我刚才说不是做过他的传吗……就像一个人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其实都是他想象的,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有经验才去解释,而是你已经有了一个解释,才能有一个经验的东西……其实人是没有一个纯粹感觉的,你看到一个东西已经在解读它了,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已经在看见一个杯子……胡塞尔……他太那个了,绕来绕去,我觉得他一个基本点可能就不太对……胡塞尔又影响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又影响了萨特,还有一个叫科耶夫的,然后巴塔耶,拉康……这是欧陆传统……英美它是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分析哲学传统……”
最近朱岳对死亡的问题十分着迷,“可能天天都在想,昨天晚上还在想”。他眼神游离地讲起来,“我现在对佛教的断灭相特别特别着迷,可能要坠入邪道了,我每天都在想断灭相,就是人一没了,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和你没什么太大关系,虽然你活着时候好像很有主人公的感觉。”
如今朱岳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有了小孩之后他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写东西了,他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在地铁上看书,回家陪小孩玩。他写小说是很慢的,一个几千字的小说,他要写两个月。“有没有希望能不干别的,把时间都用来写作?”“有时有过,不过这也属于要不断舍弃的。”
《说部之乱》后记里朱岳写道:“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能舍弃什么,而非得到些什么。”“舍弃什么呢?”“舍弃一些妄念吧。”以前他曾经希望用写作来治疗绝望,但后来他发现绝望不是最糟糕的,“妄念”才是最糟糕的。“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会希望得到什么,你肯定希望要得到肯定,你想得到意义,你想得到价值,想摆脱绝望,但是后来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很虚妄的东西。”
朱岳最近也在策划一套挖掘主流视野外的独立作家的书。“我还是想多做点什么的。”朱岳喝了一口水,很认真地说。他曾经写过一份模拟的自我采访,其中有一个问题,提问者问,如果你意外发现了古代海盗藏匿的宝藏,有了大笔金钱,你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什么吗?
朱岳回答:“作为一个图书编辑,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文明国度,纯文学的处境比较艰难。我们的社会大概有三种主要力量,体制、市场和圈子。而纯文学,从它的“纯”来看,总是要相对独立于这三者。我不相信现代社会中一个作者还可以绝对独立于它们,但仍有可能不完全依附于它们。这种独立性的代价就是吃不开、出不了头等等。那么既然我已经有了大把金钱,是不是该帮助一下纯文学作家们呢?我想如果我直接给他们打钱,他们就会依附于我,讨好那些我所雇用的评审委员。
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作者们不必靠写作为生,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所以我会投资创办一个‘纯文学作者职业介绍所’,向他们介绍一些不是太忙、不用加班、不用担负太大责任的工作,工作地点最好在家附近,收入中等。我可能还会给聘用纯文学作者的企业一笔补贴,奖励它们为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
“是的,作家就应该做一些晃晃悠悠的工作。“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朱岳笑着说。

朱岳自画像!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
朱岳:卡夫卡,我觉得他肯定是第一,就一般现代文学中都没有什么争议。我喜欢现代的,一是对他那种想象的力量很佩服,二是还有共同的法律背景,很能理解他写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
朱岳:孙甘露吧。他其实写的小说不多,就是短篇小说也是很有限的,还有一个不算太厚的长篇小说,他后来好像也又写过两三篇小说,但是都不是早期的那种,没有那种强度。首先他的语言我觉得比同时期的那些人好,我没读过余华的,但是我觉得他比马原和格非的语言要纯净,而且他的想象也很自由,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后来不写了,也挺牛的,他可能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也就不写了,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朱岳:我可能只和少数的一些朋友有很松散的联系,但是大部分都是我作为编辑人家作为作者的那么一种方式。以前可能有过,讨论讨论怎么写呀什么的,现在没有了。我觉得有些圈子是这些人成天都在一起泡酒馆,好像生活都在一起,我觉得太容易导致这些人相似,维特根斯坦有个概念,叫家族相似性,这些人就有点家族相似性。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朱岳:我现在没时间写作了,因为现在小孩特小,才一岁,回家就带孩子,然后上班坐班基本没时间了,等小孩大点的时候再说。以前基本就是周末写得最多,或者节假日能给我点时间就不错了。当律师的时候是挺有时间的,也不用坐班,但是那时候没有有意识地去一篇一篇写,完全是写着玩。坐班以后基本就没有什么时间了,下班之后精疲力尽,我也不是熬夜的那种人。
我还是挺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是一个内在规律,比如几个月能得到大概五六个想法,我就有五六个五六个的这种小的想法在脑子里,然后我就看那个想法能不能慢慢形成一个小说,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形成了要写了,一下笔,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放弃了,然后再换一个可能就写出来了。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朱岳:没有任何爱好,上豆瓣吧,上豆瓣、买书。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朱岳:我觉得好的电影还有叙事,它那个叙事感和小说很接近。不过现在小说它也有很独立的东西,小说是一个人的意志,它不是一群人的那种集体的意志,还是不太一样。我也做过编剧,特别痛苦,就是你提过一个想法,人家给你否定了,你提想法越多最后你成活靶子了,一群人否定你。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朱岳:故事。我觉得故事就是一个矿石或者是一个玉石,其它的都是雕琢这个东西,叙事和语言都是最后由这个故事来决定的,而且这个故事只要好,你的语言叙事再怎么差,只要别太乌七八糟的,就基本不会把这个故事给讲坏了,你三句话五句话讲了这个故事,它也照样是一个故事。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朱岳:好像不会,因为我写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浑身抽搐跟半身不遂似的那样写,基本想不到其它的事,周围有人说话都会非常愤怒。后来我老婆经常故意地在那儿惹我,把我给练好了。
我主要的忧虑不是读者接受不接受,我最焦虑的是以前有人写过类似的东西,或者是我的朋友有类似的想法,但是还没写,他告诉我“朱岳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我一看正好写过这么一篇,我就不想要这个了,就是这种焦虑。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朱岳:我觉得没有义务而且不应该,我关注只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去关注而不是作为一个作者去关注。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你要不关注政治,肯定政治是会来关注你的,写作之所以要关注政治,就是为了让政治不关注你,因为你不去管它,它都会来给你加各种东西。这个也有道理,所以我也不是那么绝对,只是我自己,起码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我觉得应该尽可能纯粹一点,因为中国人最大问题就是各种事不往纯粹里搞,该弄这个的人他想那个,拍电影的人不想电影,想好多经济的事,写小说的人不好好写,想好多社会问题,搞政治的人去想怎么搂钱。如果大家都想自己该想的弄自己该弄的,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维特根斯坦说提高自己是提高社会的唯一手段,大概就是这意思。一群龌龊的人成天批判这个骂这个的,然后自己都是那样的一群人。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小说读者是更多还是更少?
朱岳:我觉得看类型了,像读我这种小说的人真是很难增加,但是说减少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是会增加,因为我觉得现在90后的素质还是挺高的,我接触过的90后很多是很有想法的。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朱岳: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最好作者别自己评论自己。因为现在当假理论家非常容易,谁都能说出一套一套的,但是如果从分析哲学上讲都是胡说八道。分析哲学首先分析什么是“美”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标准,你看一个画说啊真美,它就是一个感叹,美并不是直接对应着一幅画上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叫美,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没标准的,就是说不能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说美,当然这个标准确实又不是一个很固定的标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比如什么黄金比例,这样其实就僵化了,看任何画你都不先说美不美,先看是不是黄金比例的,这样的东西也脱离了美的实际用法。所以这在分析哲学里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很多评论家都没有想过,然后就上来开始说,套一堆理论,拉康怎么说,德里达怎么说,福柯怎么说,那些人已经是很玄乎的东西,他们肯定研究的也是有限的,然后说一大堆,当然有时候也有启发性。
我很少看评论家的评论,因为我自己要写的话,我可能比他们写得好,真的这不是吹牛。但是我觉得写小说的人最好别写评论,写评论很容易变成自我辩护,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搞哲学的,也写小说,他的小说谁都不接受,写的太怪了,然后他就有自己的一套评论方式,他那评论写得非常好,但是我老觉得那样你就等于自己屏蔽了好多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的未来期许是什么?
朱岳:我还是希望能有变化,因为我现在写的东西就是尽量摆脱套路化的东西,想写点能有另外一种感觉的东西,首先就是放弃以前的很多东西,感觉以前写过这类的就尽量不去想,所以会越来越困难了。
人物简介:朱岳,1977年生于北京,A型血,射手座。毕业后先做律师,后转行从事编辑。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睡觉大师》、《说部之乱》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