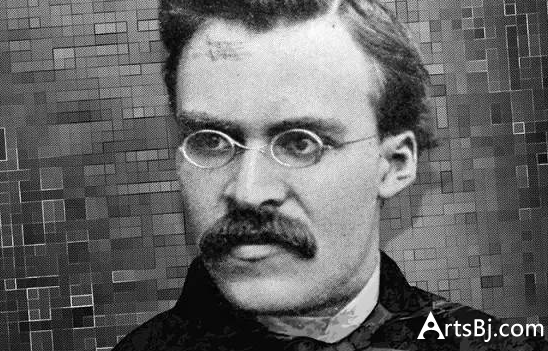
尼采,被中国人民熟知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但似乎被没有看上去那么“熟知”。就像因为写影评写出名的齐泽克一样,尼采的出名,似乎和他悲剧性的命运与不被理解的哲学思想有关。
尼采才华横溢,把哲学书写的和诗一样,《查拉斯特拉如是说》就被他写的闪闪发光,那些双关语、同音字,所有文字都是他的掌上游戏。可是《查》写得如此辉煌,依然难得美人欢心,于是尼采愤愤地说,“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你的鞭子。”
这句话忽然就被绝大部分男性记住了,可能还误会了。对此,写《西方哲学史》的罗素吐槽说,"十个女人有九个会让尼采丢掉鞭子,他明明知道如此,所以才要避开女人呀”。
尼采过世后,他的思想被希特勒大为赞赏,这又让普通群众,对尼采多生出一些误会。他和他原本就难以理清的思想体系,显得更加像迷雾一团。
中国对于尼采是热爱的。这一点作家梁晓声注意到了。在他的作品《生命,何以高贵》中,梁晓声很直白的指出,对尼采的追捧不啻为一种造神运动。
中国人对尼采的热情,到底是赞誉还是商业销售伎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伎。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溶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使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培、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佛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理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敌视或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老”死的。
1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的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几天就可以读完。十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地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但——他对“哲学”二字并无什么切实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一九○二年,尼采死后两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以极伟大之智力,其高瞻远瞩于精神界。”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也更见容于当局。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中国的一概当局,向来是颇愿表现出宽谅的开明的。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一九○○年到一九一五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这是为什么呢?
2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耳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
早期中国文人对自身作为的最高愿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顶尖级别是“相”,位如一国之总理。倘官运不通,于是沦为“布衣”。倘虽已沦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为,那么只有充当“士”这一社会角色了。反之,曰“隐士”。“士”与“隐士”,在中国,一向是相互大不以为然的两类文人。至近代,亦然。至当代,亦亦然。“士”们批评“隐士”们的全无时代使命感,以“隐”作消极逃遁的体面的盾。或“假隐”,其实巴望着张显的时机到来。“隐士”们嘲讽“士”们的担当责任是唐·吉诃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作秀”。或那句适用于任何人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无论“士”或“隐士”中,都曾涌现过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也都有伪隐者和冒牌的“士”。
在当今,中国的文人型知识分子,依然喜欢两件事——或在客厅里悬挂一幅古代的“士”们的词联;或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隐”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当今之中国,其实已没有像那么回子事的“隐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士”。
然而,毕竟的,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士”们的时代,不是“隐士”们获尊的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准切地说,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确乎的被封建王权、被封建王权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压抑得太久也太苦闷了。他们深感靠一己的思想的“锐”和“力”,实难一举划开几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质地绵紧的厚度。正如小鸡封在恐龙的坚硬蛋壳里,只从内部啄,是难以出生的。何况,那是一次中国的门户开放时代,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识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鉴和精神的依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煽动造反的嫌疑,何况当时以暴力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
于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张,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者们借来的一把利刃。由于他们是文化人,他们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压迫的“大山”。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更新了一种政权的性质,人类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马克思主义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权模式,但对文化却持尊重历史遗产的态度;尼采则认为,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则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
尼采的哲学,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文化至上”的哲学,或曰“惟文化论”的哲学。再进一步说,是“惟哲学论”的哲学,也是“惟尼采的哲学论”的哲学。
“借着这一本书(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给予我的同类人一种为他们所获得的最大赠予。”
“这本书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他足下一个难以估计的遥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无不满载而归的。”
语句的不连贯难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哝么?“我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说出的东西。”“这种东西(指他的书)只是给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的。能在这里作一个听者乃是无上的特权……”“我觉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书,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予他自己的最高荣誉。”
“能够了解那本书(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六句话——也就是说,在生命中体验了它们,会把一个人提升到比‘现代’人类中的优智者所到达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对他的哲学的自我评价。在他一生的文字中,类似的,或比以上话语还令人瞠目结舌的强烈自恋式的自我评价比比皆是。而对于他自己,尼采是这么宣言的:“我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良’人类。”“这个事实将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我得以完整地阅读尼采,我不禁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国现代史中极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感到难堪。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优秀和值得后人敬仰,乃由于读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诗体的小册子中的六句话。
我只能这么理解——中国历史上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需要一位外国的“战友”;正如中国后来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国的导师。于是自恋到极点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论中。这其实是尼采的殊荣。尼采死前决想不到这一点。如果他生前便获知了这一点,那么他也许不会是四十五岁才住进耶拿大学的精神病院,而一定会因为与中国“战友”们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进去……
在中国,我以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无论其学问渊博到什么程度,无论其思想高深到什么境界,无论其精神的世界自以为纯洁超俗到多高的高处,一旦自恋起来,紧接着便会矮小。
3
关于鲁迅与尼采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炮。他毫不乞灵于牛皮和铁的甲冑;他只有自己,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样的战士将谁们视为“敌人”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他微笑着,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战士是一定要挑战那虚假的“太平”的。“但他举起了投枪!”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于他似乎终不可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地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么?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
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归于尼采。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
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
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亩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鲁迅这一种自知之明,与尼采的病态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鲁迅有很自谦的一面。尼采则完全没有。非但没有,尼采甚而认为自谦是被异化了的道德,奴性的德道。
他那一种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体现。鲁迅是时常自省的。尼采则认为自省之于人也是虚伪丑陋的。仿佛,因为他拒绝自省,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完人。并且一再地声明自己的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这样写书:《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我的书是——“一部给一切人看而无人能看懂的书”……
鲁迅是悲悯大众的。尼采不但蔑视大众,并简直可以说仇视大众。他叫他们为“贱氓”。他说:“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说:“许多人逃避开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贱氓;他憎恨和他们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实。”
他说:“许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宁愿与猛兽一同感到干渴,只是因为不愿同污脏的赶骆驼的人坐在水槽的旁边。”他甚至无法容忍“贱氓”也有精神。“当我看出了贱氓也有精神,我即常常倦怠了精神。”“我的弟兄们,我觅到它了!这里在最高迈的高处,快乐之泉为我而迸涌!这里生命之杯没有一个贱氓和我共饮!”“真的,我们这里没有预备不净者的住处!我们的快乐当是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冰窖!”即使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如果谁是“贱氓”中的一员,或仅仅是体恤他们的人,都不禁会内心战栗的吧?我感到这仿佛是以日耳曼民族的血统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的纳粹军官在大喊大叫。
尼采若是中国人,尼采若活在鲁迅的时代;或反过来说,鲁迅若能像我们今人一样得以全面地“拜读”尼采,那么,我想——尼采将是鲁迅的一个死敌吧?怎么可能不是?!鲁迅对尼采的推崇——一个由于不全面的了解而“看错了人”的历史误会。一位深刻的中国思想者对一个思想花里胡哨虚张声势的“德国病人”的过分的抬举。
鲁迅是一次中国严重的时代危机的报警者。而尼采则不过是一种德国的精神危机暴发之后形成的新型病毒。
4
关于尼采的“超人”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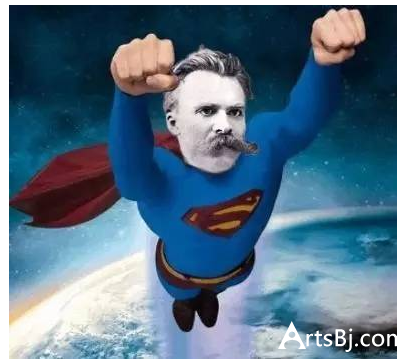
在尼采杂乱无章的、以热病般的亢奋状况所进行的思想或曰他的哲学妄语中,“超人”乃是他彻底否定一切前提之下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用尼采自己的话说——他们是“高迈的人”,“最高的高人”。尼采自己则似乎是他们的“精神之父”。
“超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迄今为止,一切研究尼采的人,都不能得出结论。
因为尼采一切关于他的“超人”的文字,都未提供得出任何较为明晰的结论的根据。
他不无愤怒地反对人们将他的“超人”与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过的这一种人或那一种人相提并论。哪怕那是些堪称伟大的人,尼采也还是感到倘与他的“超人”混为一论,是对他可爱而高贵的“超人”孩子们的侮辱。
故我们只能认为那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不曾出现过的人,是仅仅受精在尼采思想子宫里的人。既然业已受精成胎了,那么尼采自己是否能说明白他们的形态呢?尼采自己也从没说明白过。
他只强调“超人”非是这种人,非是那种人;他似乎极清楚他的“超人”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类,但就是不告诉世人。因为世人不是卑鄙虚伪的人,便是该被咒死光光的贱氓。“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尼采如是说。“他就是大海。”尼采如是说。“诚然。人类是条污秽的湍流。一个人必须成为一个大海,可以容纳污秽的湍流而不失其洁净。”这话也说得极好。“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一切生存者都能从他们自身的种类中创造出较优越的来。”这个道理也是极对的道理,但并非尼采发现的道理,几千年以前的稍有思想的人便懂得这个道理了。“上帝死了!——现在,是该由高人来支配世界的时候了!”
然而这一句话却是令人惊悸的了。原来否定了一个上帝只为制造另一个上帝。这“上帝”如是呐喊:“你们更渺小了,你们渺小了的人民哟!你们破碎吧,你们舒服的人们!时候到了,你们将毁灭了!”“毁灭于你们的渺小的道德,毁灭于你们的渺小的怠慢(对尼采的哲学及尼采的‘超人’孩子们的怠慢),毁灭于你们的乐天安命!”
这个上帝比“死了”的上帝更加严厉,“他”连渺小的人民乐天安命的渺小的权利都将予以毁灭予以剥夺。“不久他们将变成干草和枯枝!”“那一时刻就要到了,它已逼近了,那伟大的日午。”读来不禁使人毛骨悚然。尼采赋予他的“超人”们两种“性格”——优种的傲慢和征服者的勇猛。这两种性格也是尼采极其自我欣赏的“性格”。后来它们成为从将军到士兵的一切纳粹军人的集体精神。体现于纳粹军队的军旗、军服、军礼、军规、军犬乃至作战方式……
尼采生前,所谓尼采哲学在德国并不曾被认真对待;尼采死后的三十年间,他的思想渐在德国弥漫;又十年后,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人们从纳粹军国主义分子们不可一世的“精神气质”中,能很容易地发现尼采“超人”哲学的附魂。
细分析之,“超人”哲学是反众生反人类的哲学,是比任何一种反动宗教还反动的哲学。因为宗教只不过从德行上驯化世人,而“超人”哲学咒一切非是“超人”的众生该下地狱。它直接所咒的是众生普遍又普通的生存权。
太将尼采当成一回事的中国人(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人才这样),定会以尼采所谓“超人”哲学中那些用特别亢奋的散文诗句所表述的“精神”上“纯洁”自身的炽愿,当成某种正面的思想境界来肯定和颂扬。但是此种代之辩解的立场是极不牢靠的。
因为一个问题是——如果某人不能成为那种精神上“高迈”的“最高的高人”将如何?那么他还配是一个人么?答案是否定的——不配!那么他便是虚伪卑鄙之徒,是贱氓。或有知识的行为文明的贱氓。甚而,简直是禽兽不如的虫豸!倘他们竟敢与“最高的高人”们共享某一食物,那么那食物“便会烧焦了他们的嘴”,仿佛“他们吞食了火了”。更甚而,“最高的高人”于是便有权“将自己的脚踏入他们的嘴里”。
但“最高的高人”们的“精神”所达到的“纯洁”的高度又是怎样的一种高度呢?
“在最高迈的高峰的夏天,在清冷的流泉和可祝福的宁静之中——这是我们的高处,是我们的家——在将来的树枝之上,我们建筑我们的巢;鹰们的利喙当为我们孤独的人们带来食物!”“如同罡风一样,我们生活在他们上面!”“并以我们的精神夺去了他们精神的呼吸!”总之是坚决地不食人间烟火,亦不近人间烟火。而且,坚决地仇视人间烟火。“最高的高人”们的居处已是如此的“高迈”,食物又是那样的稀异,他们的“精神”上的“纯洁”程度高到何种境界,也就难以想象了。
自从有人类以来,有几个人能修成为那样的人?替尼采辩解的人们难道是么?若并不是,便先已是虫豸了!便先已该被“最高的高人”们“将脚踏入他们嘴里”了!尼采自己难道就是么?其实也断断不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停止过的一种怨恨就是——世人首先是他的国人对他的哲学的不重视。足见他又是多么地在乎凡人和贱氓们对他的感觉了。
尼采在这个世界上一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便是丹麦人莱德斯博士——因为后者在自己国家的大学里开讲“尼采哲学”……“超人”哲学——一种源于主宰人类精神的野心,通常每在知识者中形成瘟疫的思想疾病,却对症大力倡导“普通人”的哲学。
5
关于尼采和中国知识精英
凡尼采思想的熔岩在中国流淌到的地方,无不形成一股股混杂着精神硫黄气味的尼采热。
“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几乎一切古典思想,以及后来支撑中国人国家信仰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们而言,已不再能真实地成为他们头脑所需的食粮。
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面包者,洋主食也。在中国人看来,当时乃高级主食。
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如鲁迅当年因不闻文坛之“战叫”而倍感岑寂;中国那时的大小知识分子,无不因头脑的营养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尼采“面包”来了,弗洛伊德“面包”来了。在大小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它们是“精白粉面包”,似乎,还是夹了“奶油”的。
与水往低处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国知识结构高处流去的。
撇开弗氏不论,单说尼采——倘一名当时的大学生,居然不知尼采,那么他或她便枉为大学生了;倘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别人热烈地谈论尼采时自己不能发表一两点见解以证明自己是读过一些尼采的,那么简直等于承认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学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导师,关于尼采和学生之间毫无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语言的交流,那么仿佛他的知识结构在学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问题了。
这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追星”现象,或曰“赶时髦”现象。虽不见得是怎么普遍的现象,却委实是相当特别的现象。此现象在文科类大学里,在文化型大小知识分子之间,遂成景观。在哲学、文学、文化艺术、社会学乃至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诸方面,尼采的思想水银珠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而无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学,真的那么包罗万象吗?
台湾有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很凄美的咏落叶的诗。首段是: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状貌,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当时,对于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影响之久,之广,之深,我以为无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细分析起来,其影响又分为四个阶段。或反过来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藉尼采这张“西方皮”,进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灵魂的蜕变。
第一阶段:能动性膨胀时期。主要从尼采那里,“拿来”一厢情愿的“改良”者的野心。区别只不过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文人型知识分子们,恰恰由于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惭愧于面对世界发言,而只企图“改良”同胞了。这其实不能不说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和姿态,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为连鲁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未能达到之目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也是难以接近那大志的。
一国之民众是怎样的,首先取决于一国之国家性质是怎样的。所谓“道”不变,人亦不变。所以,在这一时期,“尼采”之“改良”的冲动体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诗体的呓语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个人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却有着“集体主义”的性质。
第二阶段:能动性退缩时期。由于“改良”民众力有不逮,“改良”国家又如纸上空谈,甚至进而变为清谈,最后仅仅变为一种连自己们也相互厌烦的习气。于是明智地退缩回对自己们具有“根据地”性质的领域,亦即“生长”于、来自于的领域。这当然只能退缩到文学、文化或所谓“学界”的领域。他们(某些知识分子)于是又恢复了如鱼得水的自信。
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话语权”。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所要赋予人并保证于人的“话语”的正当权利。对于社会大众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所要争夺到的是以他们的话语为神圣话语的特权“制高点”。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同类某时缺少连当局亦有的宽容,经常显得粗暴,心理阴暗而又刁又痞。并且每每对同类使用“诛心战术”的伎俩,欲置死地而后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锤”砸出一个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红卫兵认为自己们是仅次于“最高统帅”的新权威,声称要“千钧霹雳开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罡风”,要将他以前的人类思想吹个一干二净。
第三阶段——能动性萎缩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尼采弟子”们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赶快去恭迎商业时代这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并双膝齐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两人地做出他们曾一度所不齿的最最商业的勾当,从而证明了他们与尼采精神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尼采虽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确乎是远离“商业游戏”的。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却真的开始“回归”自我,在自己们的一隅精神世界里打坐修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具有某种精神追求标准的人。也足以证明他们先前的尼采式的社会角色,是发自内心的力图积极作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虚假姿态。他们和前一类人从来就没一样过。尽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
对于前一类人,尼采是一张“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们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对于他们,尼采是当时从西方飘来的唯一一团新思想的积雨云,他们希望能与之摩擦,产生中国上空的雷电,下一场对中国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过尼采这一团云,并不真的具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强大的电荷……
他们无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篱自我幽禁,分明的乃是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观。
尼采那种仿佛具有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张力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番贵宾式的巡礼之后,吸收了中国思想天空的潮度,湿嗒嗒地坠于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山头,在那儿凝成了与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一种中国特色的可称之为“后道家思想”的东西。一种“出世”选择与不甘心态相混杂的东西……
以上三个阶段,即从自我能动性的膨胀到退缩到自我幽禁的过程,也是许多根本不曾亲和过尼采的中国当代大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录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头脑中随时会自行“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有时它是相对于社会的一剂猛药;有时它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遗传病。
6
关于尼采其人
在一八四四年,在德国,尼采相当幸运地诞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远离欧洲大陆的一切灾难、愁苦和贫困。这个家庭使他从幼年至青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用尼采的话说:“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别打算,只要有耐心,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尼采五岁丧父。
尼采感激并崇拜他的父亲——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师: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泰莱莎公主。她们都是德国最显贵的女人,当然,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忠于王朝的人。
尼采的“哲学”几乎嘲讽了从“贱氓”到学者到诗人的世上的一切人们,包括上帝,而惟独对于世上的皇族和王权现象讳莫如深。
尼采的祖先是波兰贵族。但他对此出身并不完全满意。
尼采如是说:“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
但他强调:“一方面,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即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为像德国人。”
但他强调:“不过,我的母亲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样,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亲密的接触,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日记里的‘爱莫琴’即是她。”
毫无疑问,尼采纵然不是一个血统论者,也是极其看重出身、门第和血统的人。
故尼采认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
故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对有着“卑劣血统”的人,即“贱氓”们的鄙视。“贱氓”在尼采的“哲学”里,正是按“成分论”划分的人群,而非从其他意义上划分的人群。
尼采的成长备受呵护与关爱——他身旁一直围绕着惟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亲、祖母、两个姑姑和妹妹,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一个丧父的男孩,那些女人们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无微不至多么甜腻可想而知。
这是尼采成年后反感女性的第一个心理原因。
一种餍足后的反感。
尼采有过两次恋情,失败后终生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来可爱又有教养”。
没有结成婚姻的原因,从尼采这方面讲是“她企图将一位思想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
后来婚姻对尼采遂成为不太可能之事——因为他已开始多少被人认为“精神有问题”。而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尼采的反宗教,确切地说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学修习过神学。不少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恰恰是在真正系统化地接受过神学教诲而后来成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学院学生的俄国的别林斯基。过分赞扬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气是夸大其词的。因为“上帝”于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在世人心中“死了”,因为人类的历史已演进到了“上帝”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尼采是有教养的。他几乎能与周围任何人彬彬有礼地相处。当然,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一个“贱氓”。尼采是有才华的,他在古典语言学和文学见解方面的水平堪称一流。尼采的爱好是绝对优雅的——音乐和诗,而且品位极高,而且几乎成为他的头脑进行思想之余的精神依赖的爱好。
尼采是一个天生的思想者,是一个迷恋思想活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狂。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究竟是“思想强迫症”使尼采后来精神分裂,还是潜伏期的精神病使尼采无法摆脱“思想强迫症”。
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在我看来有两点:一、一切道德应该尊重并建立在承认人首先是自私的这一前提之下,而不是建立在想象人应该是多么无私的基础之上。二、这个世界发展的真相与其说是由争取平等驱动着的,毋宁说更是因为竞争——确乎,尼采以前的人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即使关于以上两点,也绝非尼采思想的“专利”。
在他之前,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论及此两点。比如罗素关于道德曾一语中的:“道德不应使对人快乐之事成为不快乐。”——言简意赅,说出了尼采絮絮叨叨说不清的人性真相。
尼采的生活方式,是纯洁的——远避声色犬马。类似康德的那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比康德在乎对美食的享受。“我甚至在音乐和诗歌方面也早已显示出伟大的天才。”“我对自己有一种严厉清洁的态度是我生存的第一个条件。”“恐怕他们(指他的国人)很少会评断过关于我的事情……”“然后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种嘲弄。”“在一种善意待我的态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态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周围一片伪装……”以上文字,比比皆是地出现在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中。
“尼采迷”们却便认为正是他狂得可爱和敏感得恨不能将其搂抱于怀大加抚慰的“鲜明的个性”之自我写照,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不从精神病学经验方面加以重视。
自恋、妄想、猜疑、神经质般的敏感——在今天,这些其实已成为早期诊断精神病的一种经验。
因而有才华的尼采首先是不幸的,其次是值得悲悯的,再次才是怎样看待他的“哲学”的问题……尼采又是孤独的。执迷地爱好思想的人,内心里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头脑被妄想型精神病所侵害着的人,内心也都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尼采的心不幸承受此两种孤独。诗人的气质,思想的睿智,思辨的才华,令人扼腕叹息地被精神病的侵害降低了它们结合起来所应达到的高质量。
在他那优美散文诗体的思想絮片之下,在他那些亢奋的、激情灼人的、浪漫四溢的“哲学”礼花的绚丽后面,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人类一颗最傲慢的心怎样被孤独所蚀损。
在这一点上尼采使我们联想到梵高。尼采在无忧无虑的体面生活中,被“思想强迫症”逼向精神分裂;梵高在朝不保夕的落魄的生活中,被“艺术强迫症”逼向同样的命运。他们反而在那过程中证明了各自毕竟具有的才华,此乃人类的一种奇迹。
尼采的孤独又体现着一部分人类之人性的典型性——即在人类那部分既“文化”了又执迷于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的内心里,上苍先天地播下了孤独的种子。他们的理念路线,常诱导他们去思想这样一个亘古命题——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

本文选自梁晓声 《生命,何以高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