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阿莱姆·桑萨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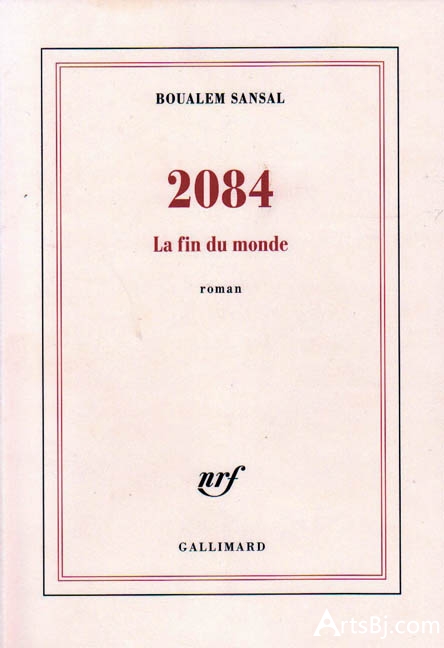
桑萨尔其人
布阿莱姆·桑萨尔 (Boualem Sansal,1949—)是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他生于乌阿色尼斯山区小村庄泰尼埃-艾尔-哈德,现居住在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布迈德斯城。
桑萨尔曾就读于阿尔及尔的综合理工科师范大学,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教过书,从过商,又曾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工业部担任高层,90年代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迪亚夫遇刺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刺激,改投文学创作之路,主要创作小说。
他的文学作品在法国和德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获得不少文学奖。199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蛮族的誓言》即获得小说处女作奖和热带奖。2000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空树中的疯孩子》获得了米歇尔-达尔奖。2007年,桑萨尔获得爱德华-格里桑奖;2008年出版《德国人的村庄,或席勒兄弟的日记》又为他带来RTL-Lire大奖以及另外三个奖。2011年,他获得德国书商和平奖。2011年,桑萨尔出版了小说《达尔文街》,讲述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故事,作品有很大的自传性。次年,该作获得了阿拉伯小说奖。2013年,法兰西学士院为他颁发了法语共同体大奖。2015年,他的《2084》获得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小说大奖(与海迪·卡杜尔的《优越者》并列)。
由于桑萨尔的书经常批评祖国阿尔及利亚的状况,因此在国内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争议。但他始终居住在祖国,认为自己的国家需要艺术家们来打开通向和平和民主的道路。2003年他发表的第三部小说《对我说说天堂》,描写后殖民化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对权势的批评性很强。因为小说强烈批评了腐败当局,尤其是坚决反对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倾向,桑萨尔被解除公职。几年后,《留邮局自取:阿尔及尔,致我同胞的一封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信》发表,但遭到政府的禁止,他自己也受到恐怖威胁。桑萨尔的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哈拉佳》,是根据他自身的经历写成的,以两个女性人物为主人公。
他的短篇小说也很多,有《嗓音》《无名的女人》《真相都在我们失落的爱情中》《简单的人寻找幸运的事件》《一切幸福都抵不上移动》《可怕的消息》《我的母亲》《克里希-苏-布瓦的约会》等。
随笔方面,桑萨尔的作品也不少。《对记忆的小小赞扬:四千零一年的怀念》是一部讲述柏柏尔人历险经历的史诗故事;《以安拉的名义管理》是对阿拉伯世界中伊斯兰化和权利渴望的思考。他的《德国人的村庄》已经译成汉语,由武忠森翻译,在中国台湾出版。
《2084,世界之末日》
小说名为《2084,世界之末日》,简称《2084》。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小说,那我会不带任何评论色彩地简述如下:2084年之后,一个叫阿比斯坦的国家在地球上开始了其永恒的统治。
正如《1984》并不是专门影射和批评某个国家那样,《2084》通篇也没有一个词提到诸如阿拉伯、穆斯林、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极端宗教狂热等,尽管书中描写的荒漠地带、居民穿的长袍披挂“布尔呢”、每天九次的祈祷“摩卡吧”,等等,会让人联想到西亚中东的地域和文明,但读者不需要自作多情地把小说中的虚构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对应起来。
小说开篇的“敬告”中写得极其明白:“这是一部纯虚构的作品,我在这里的书页中描绘的彼佳眼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会存在于将来,这就跟文学大师奥威尔所想象的并在他那本叫《1984》的白皮书中精彩绝伦地描绘过的老大哥的那个世界一样,它并不存在于他那个时代中,也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当然也真的没有任何理由要存在于将来。”
这个国家的议会叫“公正博爱会”,决策机关叫“机构局”,惟一的神叫尤拉,国家的领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节即代表。其指导思想的根本宗教叫“噶布尔”,而记载其宗教学说与信徒行为准则的圣书叫《噶布尔》。这个叫“阿比斯坦”的国家在哪里?它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又在任何地方,在世人的心中。
小说的主人公叫阿提,他先是因患肺结核病被送往偏僻至极的乌阿山的疗养院,好不容易痊愈后,返回首都,重新熟悉那个极其专制的制度和毫无个性色彩的生活。他是一个想发现国家的终极秘密,并竭力亲身实践,去冒险探寻其原因的人,这当然是决不被当局允许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同路人好朋友柯阿,还有他认识的考古专家纳斯,都死于非命。纳斯发现了颠覆国家信仰根基的秘密,即那个见证了“噶布尔”神启的所谓圣地原本竟然是假冒的,结果“被自杀”;而柯阿尽管出身显赫,其祖父是国家的功勋,但因与阿提一起闯荡违禁,力图发现什么残酷的真理,结果死于非命。
其实,阿提也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在整个国家中到处旅行”,他曾因为患肺结核病被送往十分遥远的乌阿山区的西恩疗养院,从那里死里逃生之后,历尽千辛万苦,返回首都阔扎巴德,后来,他又伙同隔离区的人一起走私,非法穿越阔扎巴德的三十个街区,以求进入到神之城。“这些事实本身,以及他从此地消失又从彼地露面的能力,已经极大地增强了他那邪恶妖魔的形象。他是天字第一号公共敌人,所有警察都想抓住他”。
2084不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份,而是那个时代之前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它可能是神主的使者、国家的缔造者阿比的诞生之年,也可能是“他获得突如其来的神圣光明之启蒙的那一年”。总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那之后,远远在那之后。正是在2084年前后,“信仰者之国”被称为了阿比斯坦,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这是一个秘密、永恒的秘密。谁都知道,“2084对国家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日期”,但同时,谁都不知道这2084“究竟与什么相关联”。
实际上,其中的因果关系很简单:种种的丑恶现象普遍存在,但国家为自己的生存需要,必须把这一切纳入到秘密之中。谁若发现真相,则会动摇信仰,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根基。这样的人就得被消灭。道德健康委员会每个月15日都要对行政工作人员作例行的道德审查,在每个人的价值手册上打分,如发现有什么违禁的言行苗头,那就有好看的了。
阿比斯坦国需要守住这个秘密,于是就得愚民,就得强调信仰,让人盲信,只许信,不许怀疑。这就是统治的诀窍。而即便是“信”,也建立在不许不信的悖论逻辑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别寻求去相信,你们说不定会迷途在另一种信仰中,只需来禁止怀疑好了,只要一再重复地说, 我的真理是惟一的和正义的,这样,你们的脑子里就将始终有它”。再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以下这条座右铭:“屈从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而诸如此类的座右铭,在阿比斯坦一共有99句,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得死记硬背,烂熟于心,而且得一生一世反复诵读。
如上所说,桑萨尔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对宗教本身总是持质疑的态度。在《2084》中,他虽没有点明某种现存于世的宗教名称,但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遍意义上的宗教。阿比斯坦国为维持永恒的统治,就得依靠某种所谓的神圣宗教,而书中那惟一的、至圣的、极端的宗教的代名词,则是《噶布尔》——那本所谓至圣的圣书。而小说的嘲讽和抨击的对象,也正是阿比斯坦国的统治根基——噶布尔教。在开篇第一页,作者就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这样写道:“宗教兴许让人爱神主,但没有什么还能比它更让人憎恶人,仇视人类。”以神的名义来反人类,这样的宗教不要也罢。
《2084》与《1984》
一读到《2084》这个书名,第一反应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紧接着,又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等等。
应该说,桑萨尔的《2084》跟奥威尔的《1984》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2084》通过对《1984》形式结构的某种摹写,写出了作者对未来某个专制主义国家的描绘和思考。
《2084》与《1984》确实存在着内在联系,其互文性是明显的,可以说,《2084》是对《1984》的某种形式的致敬。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小说《2084》中,直接就出现了“1984”的字样:当年,西恩疗养院矗立起来时,镌刻在要塞那宏伟大门半圆形拱顶上方石头上的一条碑铭,显示了数字“1984”,恰好“位于两个风化得面目全非神秘难解的符号之间”。
在《1984》中,我们经常读到并为之惊愕的一个句子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而在《2084》中,则是同样的警示在提醒公众:“彼佳眼在观察你们!”老大哥的原文为“Big Brother”,而彼佳眼的原文为“Bigaye”,两者何其相似。作者甚至还在《2084》中特地解释说:彼佳眼是一种俚语中的一个词,说的是类似“老大哥”“老家伙”“好同志”“大头领”的意思。
在《1984》作品的最后,奥威尔以大量篇幅“附录”了一篇“新语的原则”,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所谓“新语”的构成规则和使用特点,而在《2084》中,作者桑萨尔对阿比朗语的描述,也是不惜笔墨的,而且,也安排在故事叙述的最后面,即“尾声”之前。桑萨尔在书中强调:《噶布尔》之前的圣书是用一种很美、很丰富、很具暗示性的语言写的,它因更倾向于诗意化和雄辩术,而被阿比朗语所代替,阿比朗语的概念则得到了《1984》中“英社的新语的启迪”,它尤其致力于强调公众的“义务责任和严格的服从”。而这语言,完全“有能力在说话人心中消灭意志与好奇”。
至于权势者为维护统治而实施的洗脑,在两部作品中,有着异曲同工的描写。在《1984》中,洗脑的过程可分成这样的五步。一是让人害怕那个制度;二是让人不敢说它不好;三是让人经过被蒙骗之后来肯定它;四是自觉不自觉地相信它;五是最终爱上它。而在《2084》中,洗脑的过程则要简单得多:一是盲信,二是服从。盲信神主尤拉,从而确信自己永远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服从阿比的统治,从而以为这个制度永远不会出错。我们在《2084》中读到,阿比斯坦的人民没有别的思想准则,只有《噶布尔》这样一本圣书,而圣书《噶布尔》从头到尾宣扬的就是两个字:“盲信”。宗教上的盲信,必然导致制度上的屈从。从《噶布尔》到阿比斯坦国,再到公正博爱会,再到机构局,就形成了一个思想——政治——司法——执政合一的专制体制。而这体制,则完全建立在“盲信”的基础上。我们只要随便一找,就能在阿比之书《噶布尔》中找到这样的“教导”,让人来盲信:
人并不需要知道何为恶,何为善,他只需知道,尤拉和阿比保佑着他的幸福。
神启是整一,惟一,统一,它既不要求增加,也不要求修改,甚至也不要信仰、热爱或批评。只要道义和臣服。尤拉是万能的,他严厉地惩罚狂妄自大者。
狂妄自大者将遭受我怒火的雷击,他将摘除眼球,砍去四肢,被火焚烧,他的骨灰将随风撒扬,他的家人,无论前辈还是子孙,都将经历一个痛苦的终结,死亡本身也无法让他免遭我的制裁。
屈从当然不是信仰,因为信仰是要作选择的,选择则需要人们作比较,学会去区别。而“屈从即信仰”实际上是不要信仰,只要盲信,它不让人思考,只让人背诵口号。法国哲人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另一法国哲人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而在阿比斯坦国,屈从而不思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最根本的特性,妄活在世上,不配为人。
而主人公阿提要做的,其实不是别的,只是怀疑,只是不盲信。他要获得一种质疑的自由,哪怕为得到这一自由,自己会在残忍的世界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阿提总结得非常好:“知道自己是奴隶的奴隶,永远都将比他的主人还更自由,更伟大,哪怕这主人还是世界之王。”当然,只要有人怀疑,国家体制就显现出了纸老虎的本质。靠盲信和屈从而立住脚跟的国家制度,是根本禁不起质疑和批评的。
《2084》与《1984》的互文性还明显地体现在一些词汇的选择与运用上。例如纳迪尔这种电子墙报(电屏),再如,小说最后,作者借研究20世纪古老文明专家陀兹之口,道出了阿比斯坦思想路线的三原则:“死亡即生命”“谎言即真相”“逻辑即荒诞”。这分明就是对《1984》中“英社”政治制度创建三原则“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影射和发挥。而无所不在又始终不露面的神主尤拉,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老大哥”。
但《2084》也很明显地显现出别的互文性,如主人公阿提长期居住的乌拉山区的西恩疗养院,其形象活脱脱就是托马斯·曼笔下《魔山》中瑞士阿尔卑斯山那所名为Berghof的肺结核疗养院;而阿提与柯阿通过老鼠洞穿越阔扎巴德进入到神之城阿比府的经历,让人联想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有趣描写。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读《2084》时,也会发现种种让他们感兴趣的互文性来。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