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1603年,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在入教前的一刻,竟不争气地犹豫了。
按照天主教戒律(十诫),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哪怕你是中国男人也不行。这真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天人”交战了,在上帝与妾之间,中国男人只能选一个。当然,徐光启只迟疑了一会,然后中国教会就多了一个叫保罗的信徒。
在徐光启那个时代,天主教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但自入华以来,天主教就面临着“中国化”这一巨大命题。用现代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西方价值如何与中国传统博弈融合。
当时最有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此问题上是一个“鸽派”。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主张,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扎根中国,必要迎合中国传统,从中国文化的宝库中发掘可为天主教所利用的资源。借后世“红学”的分类,利玛窦绝对说得上是神学“索隐派”鼻祖,对儒家经典寻章摘句的辛苦程度不下于今日的秋风老师。比如,利玛窦成功“发现”原来西方的上帝即中国先秦古籍里那个“上帝”,多感人的破镜重圆啊!中西方虽失散了几千年,其实都是上帝的子民。
既然中西双方在终极信仰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利玛窦甚至堂皇穿戴起了儒衣儒帽,以“西儒”自居,大有“天(主教)儒合流”的意思。由此,天主教很快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可,知识界眼见信教与做孔孟门徒并不矛盾,西方普世文明也很接地气地掀起了一阵信教的文化热潮。
但正如徐光启的两难选择,无论天主教和利玛窦如何迎合中国文化,在娶妾问题上,却未给“中国化”留下任何空间。
更关键的是,不是每个中国男人都像徐光启一样有情操,愿意为了上帝放弃妾。很多明末的知识分子尽管号称心向上帝,但几经摇摆,最终选择了妾。黄一农先生在《两头蛇》中对此有各种盘点。比如南明反清义士瞿式耜,入教后不久就反悔退出,最主要的原因或是娶妾的原始冲动压倒了宗教冲动。更过分的像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教入了,妾也光明正大地娶,而且一娶就三个。他们对教规置之不理,万一被传教士发现了,大不了就被开除。
还有秘密置妾的,如明末知名忠臣王徵入教后,公开声称不再娶妾,因此还被教会塑造为一夫一妻制的英模。但因王徵没有儿子,在“无后为大”的压力下,他终是偷娶一妾。教会获悉后,王徵“痛改前非”,以与妾终生分居以示“赎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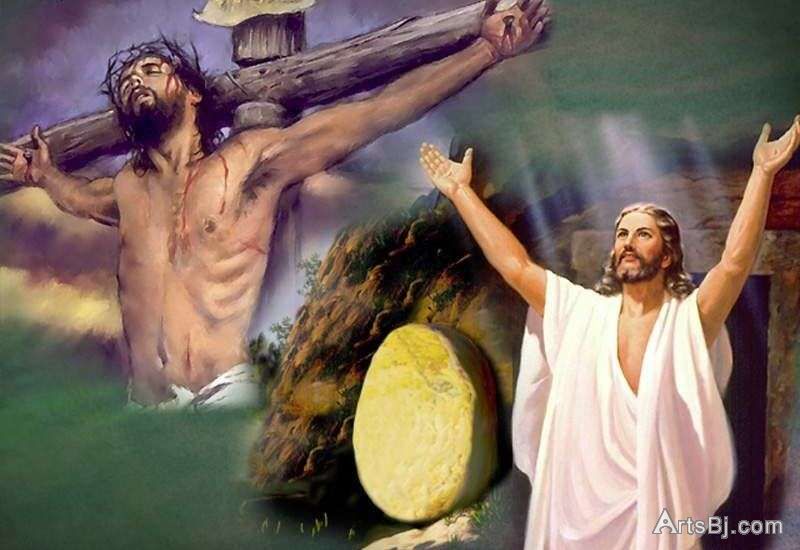
公允地说,当时的士大夫娶妾,固然有好色的成分,但传宗接代或是更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前者属于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那么后者无疑属于中西文明冲突的范畴了。不过,禁妾远不足以毁掉天主教在华的伟大事业,反而是另一涉及中国传统的敏感题材——祭祖祀孔,埋下了日后的祸因。
如果说利玛窦和他身后的耶稣会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采取的是“怀柔”姿态,那么之后的天主教在华势力则属“鹰派”,甚至有原教旨主义的意思,不容许对教义有半点本土解读,将中国文化视作文明冲突中的敌人。在这些鹰派看来,“上帝”这一译名应当禁用,必须和中国古代典籍划清界限,译作“天主”才是正版;更决绝的是,他们将祭祖一类的行为视作偶像崇拜,主张立即停止。
围绕这一系列争议,鹰派和鸽派最后都求助于罗马教廷,这也就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素以热爱西学闻名的康熙帝在此论争中自然是站在了鸽派(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耶稣会士)这边,对于鸽派风格的在华传教完全支持。但教廷的裁决简直是自杀性的。1715年,教廷明确表态支持鹰派,这不仅意味着向康熙和中国传统宣战,更宣告了天主教在华百余年传教事业的终结。
内有禁妾的天理人欲之争,外有教廷与朝廷的双重倾轧,在明清之际那么多著名的士大夫信教家族中,可能只有徐光启家族的信仰一直坚持到了近现代。宋氏三姐妹外祖母,正是徐光启的第九世女孙。
康熙自也不是这场博弈的赢家。彼时,传教士往往身兼“科学家”的重任,左手圣经,右手科学,皇帝要学科学就必须给我传教的空间,这也正是清初帝王与传教士交好的真相。
对教廷来说,禁止“中国化”就意味着告别中国;对中国来说,禁教就意味着告别西学。至此,晚明以来恢弘的中西大交流也成了历史名词。再相见,就得是1840年以后了。
我宁愿这只是一个上帝与妾的八卦故事。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