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5年的李修文曾是中国体制内最年轻的专业作家,25岁时就进入武汉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他的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曾饱受赞誉。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李修文曾说,他提前许多年实现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梦想。

李修文
采访者:臧继贤
被访者:李修文
事实上,李修文所经历的专业作家生活并不像那些想辞职去专职写作的年轻人想象得那么美好。“在中国,专业作家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画地为牢。”在走出门去做影视编剧和监制之前,李修文说那时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再不走出门就要完蛋了。那时的他已丧失写作的热情,那个大量靠审美推动的世界已让他足够厌倦,同时他认为自己严重匮乏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执行力。
十年后,在李修文看来,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本就殊途同归,都属于他创作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从他的经验来看,近些年来,在如何记录和见证这个时代方面,纯文学领域的反应其实落后于影视界。
近10年来,除了电视剧《十送红军》和改编电影《新冰山上的来客》等影视作品的创作,李修文也在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今年初,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出版,集结了他这10年来的纯文学写作。李修文明确表示,他会不断地从事严肃文学的创作,“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救命稻草以及宗教般的信仰。”

《山河袈裟》
记者近日专访了李修文,访谈内容如下。
“创作者不要被伪生活所毁坏掉”
记者:您最近出版了散文集《山河袈裟》,所以您还是在坚持文学创作的?
李修文:我就是一个写作者而已,影视创作和相对严肃的纯文学创作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这两者能够开展的前提,首先即是保持对写作的正信,我完全不觉得两者矛盾,相反,两者都是对彼此的浇灌。相较而言,所谓的严肃文学创作,于我更是救命稻草和宗教般的信仰,以影视界论,我所熟悉的导演,宁浩导演,张一白导演,程耳导演,还有电视剧的毛卫宁导演,在我看来,都是读书人。你看最近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其中的文学性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更迫切的,反倒不是体裁的孰轻孰重,倒是如何在生活意义上还原为一个正在活着的个体,而不是被文学生活和影视生活这样的伪生活毁坏掉的人。我希望重新对生活产生热情,重新知冷热知好歹。
中国文化有个特别显着和迷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很阔大的气象,司马迁也好,苏东坡也罢,无不如此,一个人首先得与自我战斗,其他的就交给命运吧,我倒不是说对司马迁苏东坡心向往之,只是想:如果能够像那样活着,写给山河看,唱给虚无听,这岂止是幸福,简直是尊严;而今天,职业和艺术门类越来越细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囚笼,把每个人僵死在里面。我想,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我还是首先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正在谋生的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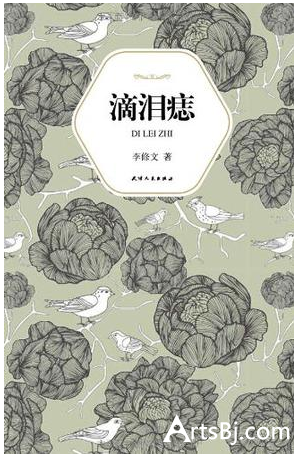
《滴泪痣》
记者:那这是不是中国文坛或者严肃文学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80后作家在内?
李修文:我不太了解80后作家,但对70后作家比较了解。中国的70后作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评价:“他们没有像50后、60后一样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同时他们的商业化程度又不如80后。”——这本身是多么势利而荒谬的两个评价体系。
我根本不认同上述观点,一个写作者和一个农民工并无本质不同,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子就生子,该得病就得病,如果有人得了病,那就得休息好了重新出发,如果有人要泥牛入海,那就该义无反顾地跳进海里。事实上,如果大家公允一点,好好看看这几年所谓70后作家们写的东西,你们真的觉得比50后60后作家差吗?我反倒觉得更好,甚至不止好一点。以常识论:一代人怎么可能出不了几个优秀、杰出的创作者呢?当然,可能真正能够代表这个年代最高写作水准的人还没开始写作呢,就像王小波一样,王小波开始写知青小说,不是就基本宣布了之前那些知青小说的无效吗?

70后作家:徐则臣、冯唐、盛可以、张楚和阿乙
记者:那这个评价体系很混乱是吗?
李修文:不必在乎这个评价体系,我们的怯懦,多半是因为我们没能忠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
记者:而且也不急着做出评价。
李修文:我们今天就是热衷于命名、评价、排行榜、年度总结。我们如此慌乱,如此需要找到一个借口,以赋予自己此时此刻的意义。一切严肃和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在今天都变成了一个借口,反正大家都百无聊赖,总归要把时间打发过去。
记者:您现在对专职作家或者专业作家这种称谓有没有一定的反思?
李修文: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不是那种开笔会或出版社、杂志的邀请——而是把自己还原为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人出门行走。
一个作家如何活着,如何扞卫好匹配写作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项艰险的功课,但也因人而宜,有的人写一本书要读一百本书,有的人则可以一本书都不读,我自己是需要深入一个境地里才能产生体验的写作者,有的写作者则完全不必如此,这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你想想:一个人忙忙碌碌活了几十年,一个人躺在床上活了几十年,难道前者就后者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更加深刻吗?所以还是因人而宜,因禀赋与遭际而异,没有一个标准或统一的药方。
“影视创作不要被文学性所左右”
记者: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说因为特别喜欢戏剧所以才去做编剧?
李修文:对。我一直很喜欢戏曲。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本和现在好莱坞所强调的三幕剧的结构其实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戏曲和中国的文章有个很大的不同,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四个方面,但戏曲剧本往往就是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展问题,解决问题。
但是,做编剧首先还是一种惯性:小说写不出来了,我能做什么呢?我那么爱看戏,于是就想,干脆去做编剧吧,如此而已。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作家的定义未免太狭隘了,在中国古代,何曾有过现当代意义的文坛和文体分类?关汉卿既写过剧,也写过诗。现当代以来,戏剧和小说的分野被过度强调了,我倒觉得:水蜜桃也好,蟠桃也罢,它们都是桃子。
记者:您除了创作电视剧剧本,是不是还在创作电影剧本?您如何平衡影视作品的文学性和商业性?
李修文:我刚刚完成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改编,现在叫做《新冰山上的来客》。的确,在过去的年代,文学性一直是戏剧或影视作品至关重要的因素,极端情况下,戏剧或影视作品到最后是为文学性服务的,有时候,一部戏成了一种文学性的影视阐释。我反倒对此存疑。随着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视觉体系、工业标准在影视范畴里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依我个人的看法,观影体验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我自己看电影,我更喜欢看那种让我产生前所未有的体验或者部分区别于其他影视作品体验的作品,而不是沉浸在文学性中无法自拔。
如果文学性是最重要的,影视的本体性又到哪里去了呢?它们至少应该比翼双飞吧?说得过分一点,如果说电影的本体性足够重要的话,那文学性很有可能就只是一部电影本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再极端一点,可能就是一个素材而已。所以,我自己从事影视工作时,并不觉得文学性是一个负担。
记者:那您怎么定义电影的“文学性”,和“文艺”有关吗?
李修文:所谓的文学性,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标准并无什么不同,我想,那就是去探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作品里,“文学性”这个词就变得复杂了,“文艺”是其中的一部分,完全不“文艺”也是一部分,我想说的是,在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它是否一定就是必须?或者说,它是否就一定要占到很大的比重?
我喜欢那些体量大、视觉系统更为丰富的电影,当然,这纯属个人偏好,在此情形下,我完全不认为文学性要成为一个至高之物,更不要牺牲一部影视作品的工业面貌而去追逐文学性,果真如此的话,那恰恰不是文学性的合适体现,反而是文学性的迷失。
“中国的电视剧是强于日剧和韩剧的”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豆瓣的评分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国内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或重拍现象,比如《平凡的世界》和《神雕侠侣》?
李修文: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重新阐释它的必要和可能。新版《平凡的世界》拍摄之前,我和毛卫宁导演吃过一次火锅,我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写下或者拍下一代人的自我奋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没有错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有一点是很动人的,它非常天真,不是贬义的或带有揶揄意味的天真,就是最初的那个天真,它天真地相信一代人的自我奋斗和自我肯定,也天真地相信我们自身对苦难必然有承受和超越的能力,而新版《平凡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阐释得非常好啊,体贴原着,情感充沛动人,尤其王雷的表演出色至极,我好多次都看到哽咽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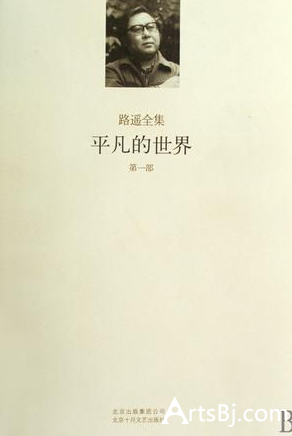
《平凡的世界》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文学作品是适合改编的?是不是有些在文学上特别经典的作品似乎很难改编成功,反而是一些较一般的作品更容易改编?
李修文: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我觉得好像都能改编,因为原着只是一个动因,更多取决于改编者如何构造一个不脱离原着精神的新语境或者解释世界。例如沈从文的《边城》看起来温情脉脉,但我经常想,这也可能有个暴力版的。因为这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使然,他建造的是一个桃花源般的、静水深流、足具乡村之美的故事,但换一个导演,比如昆汀、宁浩可能会赋予这个故事根本不同的气质,产生一种新的可能。我觉得这就像对暗号,对上了就可以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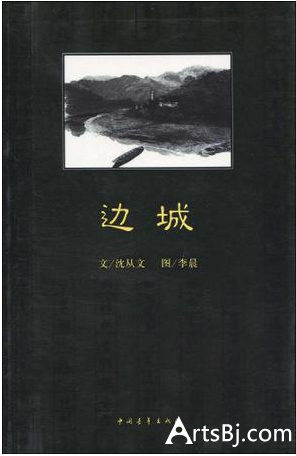
《边城》
记者:特别经典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因为包含的内容很多,而改编起来很困难?
李修文:不见得。电影和电视剧本身从产品的形态上来说是区别于文学的,尽管电影或者电视剧这种艺术门类兴起的时间远远晚于小说,但其实伴随着科技快速进步的这100年,它紧紧植根于工业基础和工业标准之上。对于原着完全忠实的改编是否还符合电影或影视艺术的创作精神?
改编就好像文本原着和影视作品一起向彼此走去,可能在中间的地方相遇,最终呈现出一个改编后的结果。改编如果完全扭曲了原着或完全匍匐在原着脚下爬不起来,我觉得都不是太理想或完美的改编。
像《潜伏》将那么短的原着小说改编成那么优秀的电视剧,连作者都大赞编剧和导演是大才。那这种改编是完全忠实原着了吗?我觉得是完全忠实了原着的精神。它在原着精神的基础上,生发出了另一个世界,但同时没有曲解原着。这就是我刚举的那个例子,一种艺术门类和另一种艺术门类在中间地带相遇才有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品。

《潜伏》
记者:在您的经验中,创作剧本和改编文学作品哪个更难?
李修文:一般情况下我不改编,因为我也是那种比较主观的人。宁浩导演就和我开玩笑,说我最好原创,不要改编,因为我的许多认识和观念实在也是顽固得很。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的潮流?
李修文:其实中国一直有评书、演义、故事会这样的传统,网络文学是丰富和扩大的版本。在今天这个时代,它实际上是文化消费的刚需,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没有缺少对这些类型的需要。我觉得这本身无可厚非,就像我们在过去的时代里需要说书人,今天我们也需要网络文学作家,那么,随着影视的勃兴,网络文学的被改编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地方了。
但我们会看见,即使过去年代里那些所谓通俗文学,经由不同作家的努力,是取得过相当大的进步的。从还珠楼主到金庸,甚至到古龙温瑞安,他们所创建的世界,在人情世故上,在人性上,在一个人如何成为个人上,是有非常深入的拓展和进步的。
再反观今天,尤其是那些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网络文学作品,我觉得很难看见这种拓展和进步,对于类型文学的创作反而是一种集体拉低。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今天电视屏幕非常可怕:一是过度的玄幻,也许是我老了,变得可笑了,但我还是认为,过度的玄幻,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几个词根,比如努力、勤奋和牺牲,它将人活一世最真切的奋斗抵消了,打开电视机,一堆穿着长袖长衫的武侠男女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双掌一推,一座山就倒了,太可笑了。第二个就是那些抗日神剧,原因很简单,他们羞辱了那些牺牲的血肉之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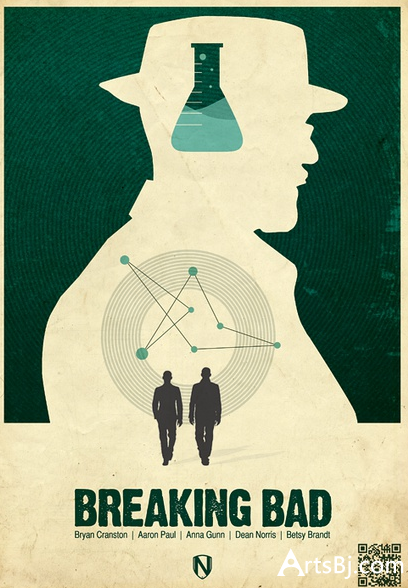
美剧《绝命毒师》海报
记者:有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追国外的剧。目前国内编剧团队的整体水平同国外相比是不是有差距?总体上欠缺优秀的编剧吗?原因在哪里?
李修文:我自己也是英剧美剧控,接下来也会和导演一起开发网络的剧集。在我心目当中,《绝命毒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剧。那么荒唐的一个故事,但背后显露出来那么深沉的爱与责任。我甚至觉得美剧的作者们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卡夫卡,个体命运与处境,在影视工业的本体性激发之下,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
我们今天动不动就说中国要战胜好莱坞,开什么玩笑,好莱坞是全世界所有优秀的电影人和产业基础集合在好莱坞所产生的形态。一己之力能够挑战全世界的行业精华吗?这两者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
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总结过去的那几十年,我觉得很难从中国电影里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的风貌,但中国的电视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电影的不足,在大量的玄幻和抗日神剧之外,还是存在着一批严肃的并且注重娱乐性的电视剧。只有创作者才知道,在今天,写什么和如何写有多么困难,但是,电视剧编剧们还是贡献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我觉得电视剧的从业者们这十年真是对得起这个时代,中国的电视剧也是强于日韩电视剧的,在非常特殊的中国文化属性里,他们艰难而有尊严地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和正在变化的国家休戚相关,反之,我觉得日韩电视剧并没有。
记者:那么,您在乎一部剧的收视率吗?
李修文:至少目前完全不在乎,因为全都是混乱的,到底哪一个数据是真实的?不过,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一个创作者,惟有用创作去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