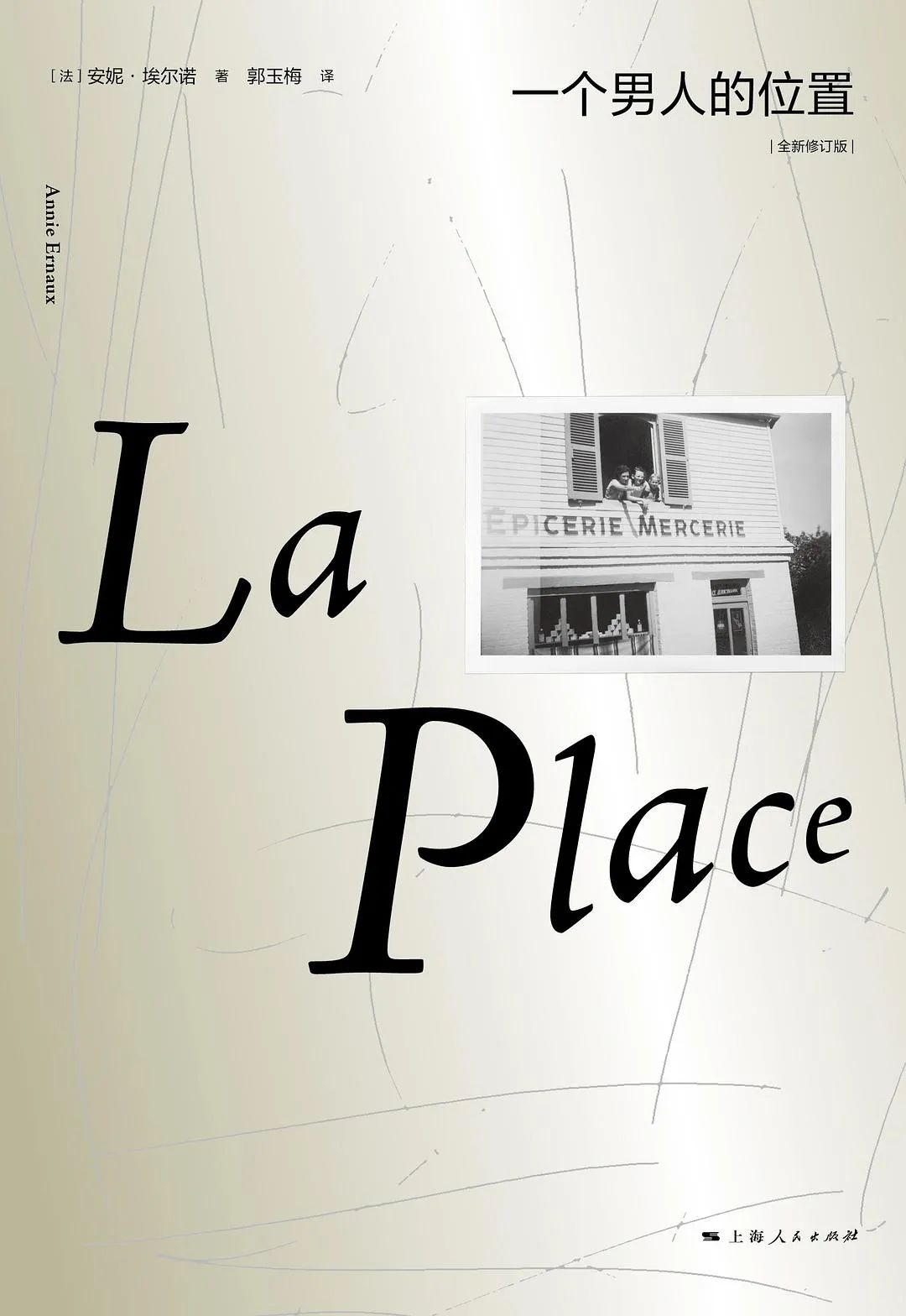
1983年,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位置》(La Place,中译本标题为“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书。这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第四本书,也是其转型之作。在这本书中,埃尔诺放弃了小说体裁,放弃了虚构,承认“我”即是作者本人。在文风方面,埃尔诺抛弃了对美文的追求,转向了用词简单且精确、少用比喻修辞的平白行文。这本书的主角是埃尔诺的父亲,是一位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诺曼底平民阶层男性。埃尔诺以回忆为素材,用冷静的笔调书写父亲一生的经历。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埃尔诺呈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现实,她的个人经验因而有了普遍性。
从小说转向叙述
1967年4月25日,埃尔诺通过试讲环节,正式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capes)。同年6月25日,埃尔诺的父亲阿尔丰斯·杜切奈(Alphonse Duchesne)去世。《位置》是从这两件事讲起的。在这本关于她父亲一生的书里,埃尔诺没有按时间顺序写父亲从童年到老年的历程,而是在开篇就写了父亲的死和葬礼,之后再叙述父亲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这种叙事安排体现了埃尔诺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和疏远:这个男人是埃尔诺的父亲,《位置》写的是她的视角观察的父亲的一生;成为文学教师、用标准法语写作的埃尔诺在文化上已经脱离了她父亲所在的阶层。
在2014年出版的访谈集《真正的地点》(Le vrai lieu)中,埃尔诺与米歇尔·波尔特(Michelle Porte)对谈,她说起父亲的去世对她冲击很大:
我看清了是什么让我跟我父亲疏远了,我和我父亲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我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社会适应过程,我的情况算是非常成功。我爷爷不认字,我父亲最开始在农场务农,后来当工人,再后来开咖啡杂货店,而我成了文学老师。我和我父亲彻底地疏远了,我跟他之间仿佛有一个深渊。没法弥补的深渊。之后,我再也不能用之前那种方式写作了,我要写一些我当时还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很久以后,社会学让我明白了我的情况属于“跨阶层者”。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词。
《位置》是埃尔诺的转型之作,然而这种转型并不轻松,1982年埃尔诺思考了很多。她意识到自己在前三本书里用的是“充满暴力的笔调”,而“这样下去不行”。埃尔诺的写作日志从1982年开始或许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一年,她开始思索自己该用何种姿态写作。2011年,埃尔诺出版了这份写作日志,名为“黑色工作室”(Atelier noir,2022年再版)。正如书名所言,对写作的思索仿佛是在黑暗中打转,试图找到一个出口。在1982年4月22日的写作日志中,埃尔诺写道:“我觉得普鲁斯特的比喻很美、很能说明事物的特点,然而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比喻。对我而言,要表现一种情感、一个场景,不一定非得用比喻。”至此,我们已经能看到《位置》文风的雏形。1982年11月,埃尔诺开始写《位置》,1983年6月完稿。
在《位置》的开篇,埃尔诺在切换时间线、准备叙述父亲的一生之前,用三段文字总结了自己写作姿态的转变。“最近,我意识到了小说是行不通的。”在此之前,埃尔诺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即《空柜》(1974年)、《他们所说的或空无一物》(1977年)和《被冻结的女人》(1981年)。从《位置》开始,封面上的“小说”(roman)一词不见了。埃尔诺放弃了小说的体裁,转向了叙述(récit)。在转变体裁的同时,埃尔诺放弃了虚构,她要写的是记忆中残存的感受,是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位置》之前,埃尔诺也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不同于叙述中的第一人称。在埃尔诺看来,“我”是一种声音,而不仅是一个人称。“我在《空柜》中和在《事件》中的声音很不一样。变化是从《位置》这本书开始的。变化的不仅是声音,还有写作的整体姿态。”
“平白行文”首次出现
在文风方面,埃尔诺选择了既不美化也不嘲讽的风格,如实描写,少用比喻。她在意的“不是写得美不美”,而是“写得对不对”。批评家在讨论埃尔诺的文风时常用的“平白行文”(écriture plate)一词便出自《位置》,这是埃尔诺本人的表达。然而,“平白行文”的字面意思往往引发误解,有人误以为这是一种乏味、无趣的风格。2022年10月19日埃尔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参加电视采访,“大书店”节目(La grande librairie)的主持人奥古斯丁·特拉佩纳尔(Augustin Trapenard)刚提到“平白行文”,埃尔诺就马上反驳:“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她继续解释:平白行文意味着既不是伤痕文学(misérabilisme),也不是大众赞歌(populisme)。埃尔诺在纪录片《词语仿佛石子》(2013年)中也解释过:赞美劳动人民的伟大,等于否认切实存在的统治和异化。埃尔诺认为自己在写《空柜》时把自己放得高于父母,把自己放在了统治者的一边。
埃尔诺的父亲曾说:“书啊,音乐啊,这些对你都有好处。我呢,我活着不需要这些东西。”埃尔诺在《真正的地点》中写道:她父亲读书不多,但读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于科地区(pays de Caux)的人而言,莫泊桑是“他们的作家”。埃尔诺的父亲曾说:“总算有个作家写到咱们了!”当埃尔诺要写自己的父亲时,她开始思考何种笔调、何种方式才能写得公正。“我不想通过写作给我父亲实际遭受的统治再添上一层统治。”埃尔诺最终选择了用以往给父母写信时的笔调。“平白行文”不仅是文学范围内的审美选择,更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埃尔诺不希望自己的书只被所谓精英阶层的人读到。她写的是出身平民阶层的父亲,她希望平时可能没有阅读习惯的、出身平民阶层的人也能看懂她的书。
埃尔诺在上天主教私立学校时一度为父亲的用词感到羞耻,她曾向父亲抱怨:“你们一直都说不好话,你们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师揪出来批评啊?”父母用词粗俗比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更让她难受。在准备写父亲时,埃尔诺意识到她父亲使用的话语反映了一个阶层的现实。在《位置》中,埃尔诺如实记录她父亲的用词。其中一部分是直接引语,另一部分直接嵌入叙述,这两类都用斜体标出。一般情况下,法语写作中斜体的部分要么是书名,要么是拉丁文,埃尔诺打破使用斜体的惯例,用斜体来标注他父亲的话和诺曼底方言。在《真正的地点》中,她强调诺曼底方言中的词对她非常重要。这些词是她所生活过的“第一个世界”留给她的遗产。“诺曼底方言里的词在我嘴边,我不说,可是这些词在这儿。”“诺曼底方言里的词跟我童年的那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环境、嗓音、母亲的微笑,这些词没法翻译。”而埃尔诺写作时用的是她在学校里学会的标准法语,在她看来那是一种“合法的语言”。诺曼底方言中的词力量很大,埃尔诺希望她在写作时用的这套语言也有这种力量,于是她引入了诺曼底方言,引入了她父母常用的表达。她的父母怕“又只能去当工人”,她父亲认为“做生意不该表露自己的观点”,得改掉“那些臭毛病”,得“守住自己的位置”,“不管怎么着,总得好好活着吧”,“别人可得怎么看我们?”……埃尔诺如实地记下了她记忆中父母说过的话。这些话不仅是父母的语言,还是平民阶层的语言。用这些词来描述这个阶层,埃尔诺说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我对此非常有意识”。
文学不是社会学
埃尔诺从七十年代起开始阅读社会学著作,布迪厄的《区分》给了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视角,她注意到自己与父亲的疏远体现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上。她详细地描写她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如:他用欧必奈尔牌小刀把面包切成小方块,然后把小块的面包放在盘子边上,把奶酪或者香肠放在上面,叉着吃;他每周刮胡子三次,而且是在厨房的水槽刮;他喜欢跟客人开玩笑,他从来不去博物馆……如果我们套用布迪厄的理论,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属于“惯习”(habitus)。埃尔诺通过不加道德判断的方式如实地描写他父亲的日常生活。而她之所以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一是因为她读过社会学著作,二是教育和婚姻使她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她在回忆她父亲的一生时已经具备外部视角。
通过描写这些细节,埃尔诺试图展现跨阶层的机制和体验。在她的行文中,隐约透出社会学的视角,她本人也公开承认社会学,尤其是布迪厄学说带给她的影响,但她选择的形式仍是文学的。在《位置》中,埃尔诺描写了她父亲的生活习惯与她在私立学校的同学、她上大学以后认识的同学、她丈夫等的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她努力“破解这些细节”的含义,她“花很多年来‘理解’那些教养好的人怎么只说一句‘您好’就能显得那么和蔼可亲”。她在行文中会用“习惯”(habitude)这个词,却从没有用过“惯习”一词。埃尔诺写跨阶层体验的方式是视觉的、感官的,她的描写围绕具体的事物展开。比如,她写在伊沃托上学时去同学家做客,同学的父母问她喜欢听爵士乐还是古典乐,喜欢谁的电影。这些有关品位的问题一下子让她明白了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
2005年,法国社会学家伊莎贝拉·夏尔邦吉埃(Isabelle Charpentier)与埃尔诺对谈,她说:“您似乎打破了文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在固有的认知中,这两个学科是对立的。”埃尔诺的回答实际上否认了她的写作是文学和社会学的混合:
我在作品中不用社会学术语,而在别的地方我会用社会学术语,比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是用有点野的方式习得这套术语的(笑)。在阅读社会学著作的过程中,有些词会让你觉得这是讨论某个事的时候最合适的词。我在写作时,偶尔会用一些社会学里的词,但我不是全用,因为实际上当我写东西的时候,事情并不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的……比如我现在能跟您在这儿谈统治或者象征性暴力,但当我写东西的时候,我想到的绝对不是学术用语,不是社会学术语;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场景,是感受,我需要用词展现出这些场景和感受,我要用一些能让这些场景和感受被看见的词,通常是非常物质性的词。这些词对应经历过的场景、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话。
个人的也是普遍的
埃尔诺通过对父亲的描写展现出了自己的跨阶层体验,因为这些描写都是通过“我”的眼睛实现的。《位置》一书写的不仅是埃尔诺父亲的人生,更是她本人跨越阶层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有的,埃尔诺看似极具个人性的叙述因此有了代表性和普遍性。她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在与夏尔邦吉埃的对谈时她说:“我一直觉得在我经历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和想到的一切中,有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而这种认识很显然被社会学加强了。我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我是一个可以被客观分析的路径的产物。”“写作的工作就是持续地展现出这些并不是只有我才经历了的事情,把这些事情用文字呈现出来。”
埃尔诺多次在陌生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位置》的结尾,埃尔诺写道:“我在人们在等候室里坐着和无所事事的姿态中、在他们招呼孩子的方式中、在车站月台上与人告别的样子中,寻找我父亲的形象。”埃尔诺在陌生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了父亲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正是这些场景激活了她的记忆,让她能在父亲去世十五年后开始写一部关于他的书。在《外部日记》的结尾,她写到在超市收银台前等待结账时看到了一个女人,那女人的言语和动作让她想起了母亲。埃尔诺也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在中学教书时,她教过一些准备考职业资格证的学生,她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样子。正因如此,埃尔诺相信个人经验具有普遍性。她在《真正的地点》中写道:“我确信那些曾经穿过我的东西也一定穿过了其他人。”埃尔诺曾被问到为何一直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干脆地回答:“因为我是受害者。”她年轻时曾在日记里写过“我写作是要为我这种人复仇”,之后她不断在多处重复这句话。然而,埃尔诺的写作绝不只是个人的复仇,她在个人记忆中挖掘的并非属于她自己的真实,而是诸多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所经历的真实。
《位置》一书的标题也透露出了这一点,这个位置不仅是埃尔诺父亲的位置,也是所有阅读本书过程中思考自己人生经历的人的位置,埃尔诺认为社会地位比性别更显著地影响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她在这本书中要写的绝不只是父亲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而是一种社会机制。她否认她的作品是自我虚构(autofiction),她在《真实的地点》中说:“每次有人说我的写作是自我虚构,我都会反抗,因为这个词形容的是只关注自己的状态,是与世界隔绝。”埃尔诺想写的不是个人经历的特殊性,而是经历的普遍性。“当不可说的东西被写出来以后,它就具有了政治性。”埃尔诺的多本书的标题都体现出了这一点,她写父亲的书标题是“位置”,写母亲的书标题是“一个女人”,写堕胎经历的书标题是“事件”,写第一次性经历的书标题是“女孩的记忆”……这些简短但又具有解释力的标题正是普遍性的体现。
在《位置》中,埃尔诺不仅写父亲的一生,写自己与父亲是如何疏远的,还在叙述中穿插自己写作的心得。开篇时,她坦言自己没法用小说体裁写父亲;在中间,她写道:上述这些对父亲的描写,或许在上学的时候也可以写在作文里;在结尾,她表示:“从11月以来,我感觉我就像被关在一种不变的天气里,又冷又下雨,隆冬时稍冷一点。我没有想过我的书何时收尾。现在我知道我要写完了。6月初,天热了。闻到早上的空气,就知道天气肯定很好。”这些句子让人感觉埃尔诺是在直接跟读者对话。在阅读《位置》的过程中,能清晰地看到埃尔诺写作的轨迹,因此也觉得与她更亲近。
1984年,《位置》获勒诺多奖(Prix Renaudot)。1974年,埃尔诺以《空柜》一书出道时曾入围龚古尔文学奖,当时她非常希望得奖,但最后没得到。到1984年,她的心情已经变了。“十年过去了,我一点都不惦记、不希望拿奖了。”她在意的不再是文学奖,而是持续出版作品。2022年出版的《莱尔纳手册》(Cahier de l'Herne,埃尔诺卷)公开了埃尔诺日记的节选,1984年10月14日,她写道:“每次取得成就以后我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恶心,累得想哭。我头一回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我总想做一些看起来很难、很重要的事,我想被认可。可是我等我做成了这件事,我就不想在这种成功的状态里了。我想重新回到匿名状态,去别的地方做别的事。”这种心情促使埃尔诺继续创作,在《位置》之后,她不断挖掘记忆中的秘密,用在《位置》中打磨出的声音继续讲述女性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经历。现在,埃尔诺有四本书(《悠悠岁月》《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我们一定能跨越语言的界限,作为人,在阅读中与她心意相通。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