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洱 (1966~) 原名李荣飞。河南济源人。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篇小说《导师死了》《缝隙》《寻物启事》《鬼子进村》《现场》《葬礼》,小说集《饶舌的哑巴》,文学对话录《集体作业》(合作)等。长篇小说《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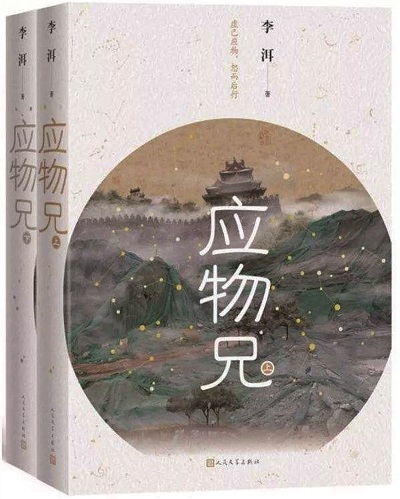
长篇小说《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一、“新的写作”
关于《应物兄》,我们将为它的奇异与驳杂而吸引。在当下浩如烟海、鱼龙混杂的小说创作格局中,李洱的叙述个性而独特,那是可以打上“高辨识度”的“李洱式”书写。对于“知识者”的钟情专注,与身在其中、眼饧耳热的书写姿态,让读者感受到了他手中之笔既描绘破碎又勾勒整体,既委顿于现实又刺向现实,既反叛传统又茫然无期。
李洱说,“由于历史的活力尚未消失殆尽,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鲜的经验也正在寻求着一种有力的表达,如布罗茨基所说,‘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我们是否可以说有一种新的写作很可能正在酝酿之中?”李洱的写作过程及至《应物兄》的出现,正是他始终探索与实践着的“新的写作”,而他也在努力,试图成为那一个负载使命的“骑手”。无疑,这样的实践并不容易,也很有价值,正如《应物兄》磅礴浩瀚的体量、直面时代的勇气与所呈现的纷繁芜杂的问题,李洱的严正与雄心赋予了它无法被忽视的“实感”;但亦如所有带有“新”之属性的事物一样,它也必将是富于争议的,如有的批评家所言,这是一部阐释空间非常辽阔的作品,它将带给批评家们高度的兴奋。
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应物兄》面世后的读者接受似乎也在映照着《应物兄》的殊异,当然,作品完成之后,短期内读者的接受与作品创作成效的考量功用之间并不构成正相关或必然性,因为时代性、社会性、政治性、市场性等不同因素总在制约与平衡着评价标准,形塑着个体接受趣味。但完全忽视读者反应似乎也取消了文本所面对的客体、对象,毕竟真正的“孤独之书”是无法获得存在之重的。而《应物兄》的接受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评论圈的狂欢与大众的接受无力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裂;未出版前的圈内叫好与出版初期的众声喧哗转向客观中和;“作家之书”的诱惑,与诗人、作家对该书的热烈拥护不断昭显着这部作品所带来的多重阐释维度。
二、类型、接受分化及问题
《应物兄》是李洱在创作实践上的集大成之作。以济州大学“太和”研究院的筹建为中心,在应物兄的视角下,三代知识分子洋洋洒洒登场,程济世、姚鼐、乔木、双林院士、芸娘等在机锋交织的言语世界里不断呈现历史、世事、文化,进而通过一些细小的世俗化故事设置,以学界为中心延伸至栾廷玉、雷巴山、铁梳子等政商界人士,形成复杂的社会观察场,情节也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维度里折叠穿梭。小说在以非线性叙述语流、大量的文献知识引证、庞杂浩瀚的问题思辨,融入片段式、分解式的生活感受中,夹杂喷涌而出,形成对当代正面强攻的书写。面对如此复杂磅礴的鸿篇巨制,评论圈普遍报以热情的期待。在《应物兄》刊登之前,历经13年长跑的《应物兄》在作者交际的文友圈内已经获得许多关注,李洱在《后记》中说,小说不断自己生长,“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李洱之前创作形成的良好口碑与身处文学中心的位置,都带给他的创作更多注视与目光。
2018年《应物兄》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刊登时,附带的评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及其他——从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的开篇方式说开去》(王春林)与《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王鸿生)在两卷上同步刊发,由此关于《应物兄》的各种评论在文学圈内正式开始登场。该年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应物兄》单行本。12月24日,程德培、金宇澄、吴亮、王鸿生、何平、金理、张定浩等评论家、作家对《应物兄》展开热烈讨论,首先在上海批评界引发震动。“《围城》升级版”“现象级作品”“注定要长期占据书架”等评价扑面而来。很快,这部小说先登上《收获》年度长篇小说榜首。12月26日,长篇小说《应物兄》发布会在京举行,李敬泽、潘凯雄、周大新、臧永清等作家、批评家围绕该书的写作态度、叙事特质、阐释空间等对《应物兄》作出了高度评价。2019年1月,《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应物兄》荣登榜首;2月,该刊“名家三棱镜”栏目推出程德培《众声喧哗戏中戏》与李宏伟的《应物兄,你是李洱吗?》两篇风格独特的评论文章,程文对李洱从《花腔》到《应物兄》的创作进行了与其小说具有同等诠释特质与哲学思辨的长文,李文则以戏仿的方式直接给“应物兄”写信交流,应物兄、李洱与李宏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再次穿行。随后,文学研究类刊物《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论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等纷纷组织专栏对李洱的新作予以关注,囊括了孟繁华、贺绍俊、谢有顺、敬文东、马兵、项静、熊辉、徐勇、邵部、李音等一众老中青批评家,他们从《应物兄》的知识分子写作题材、百科全书式写作风格、在中西文化融汇创新上的巨大成就、解构主义与忧患意识、诗学问题、世俗生活建构、儒学传承等不同层面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剖析,肯定了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2019年8月,《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带来的话题与关注持续发酵,直至当下。
值得一提的还有,除评论圈的热议外,李洱还获得了作家同道和诗人的热切反应。在《应物兄》之前,魏微写作过的《李洱与〈花腔〉》盛赞其创作。《应物兄》面世后,诗人杜绿绿的《李洱和他才能的边界》再次肯定“李洱小说的出现,对于提升中文品质”的意义。至此,《应物兄》从登场直至摘得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圈内获得了相对较为一致的肯定。
与文学圈与批评圈的拥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应物兄》在普通读者接受上遭遇的滑铁卢。在普通网民云集的读书平台豆瓣和知乎上,对于《应物兄》的评价相对较多地呈现出否定性。豆瓣短评内点赞数最高的短评中,punkpark写道,“李洱的确设下了某种野心版图,但也仅限于此。这是一本专门写给评论家,以至于可以让评论家借题发挥自己理论知识的小说……”;而长评中,宝木笑在《从围城到失败之书:谁动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书桌?》一文中写下“《应物兄》确实很尽力,但天命之年的李洱想要追求那种跃迁——凭一己之力写尽世间百态,实在是个充满暧昧诱惑但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的指标”。其他还有诸如“一部非常奇怪的小说”“难免匠气”“在整体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是先天不足的,并且后程确实乏力”等带有负面色彩的大众阅读评价。当然,也有肯定之语。“对中国传统文学继承与发扬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一部我们时代的大作品”等,但相对还是处于弱势的。
《应物兄》的读者接受的这种鲜明反差本身构成了当代文学“生产—接受”环节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这些批评、叫好与接受中,我们正得以窥见当下文学创作的分流曲线,这既是学院化教育作用的结果,更是文学观念与价值多元化导向的解构与失重。
三、李洱的“文学观”之于读者接受
作为“60后”的小说家,李洱曾被归为“晚生代作家”中的一员,他对自己这一代人以及经由学院式教育造就的明晰的文学意识有着深入思考,而这些思考在其写作风格与写作气质上则形成了坚固的意识堡垒。
他在理解“60年代作家”这一整体时将其定位为“有希望,没确信”的“悬浮的一代”。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叙述方式时,他认为“没有受过现代主义训练的作家,无法成为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这个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一定会具备着现实主义精神”;他放弃“对世界的整体性感受”,认为“作家进行情感教育和道德启蒙的基石被抽走了”“整体性的感受如果存在,那也是对片段式、分解式的生活的感受”。同时,他拒绝线性的叙述,拒绝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他认为,“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所必须依赖的人物的主体性以及主体性支配下的行动,在当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具备典型意义”。他十分钟情于文本间性造成的相互阐释,对于将注释引入小说创作中,他始终乐此不疲。他曾说,“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而他也确切地在《花腔》与《应物兄》中实践了这一理念,可以说,注释这种行为与对非线性叙事的坚信、对反讽的力量认可、对道德书写的摒弃,形成了其形式探索、叙事方式与对小说之“道”、对现实与真实等内外两层的思考。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李洱在以《问答录》为主体的书中所呈现出的文学认识与创作思想,是因为李洱不仅有着清醒的写作意识,同时也有着深刻的阐释意识。他的文学实践与文学观念之间形成了鲜明的交互性,而这种交互经由他的自我认知与阐释,已经在文本层面和理念层面构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在当下的作家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类自发性创作,这类作家经由生活经验、地域性滋养与丰富的历史时代因素催化,最后交由天性的敏感与后天的培植形塑呈现其文学创作的最终景观。而另一类作家,拥有传统主流的写作意识,主动拥抱文学的道德要求,在文学观念上有思考但深度不够,其创作往往也时有与观念不协调之处(往往是观念大于创作)。而李洱显然与前述两类均不同,他的文学经验更多交由理性思考处理,在不断重组、割裂与对话中,将意义与价值“提纯”,并以此提供了一条当代作家超越由经验有限性所造成局限的路径。可以说,这类写作在李洱这里不仅形成了完备体系,同时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上也表现为总体同步,对于文学写作思想与技术手段的思考,在小说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呈现,并使得其小说具有极鲜明的“研究特质”。
无疑,《应物兄》是李洱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提出具有“二重性结构”的文学场域概念,一个专为同行精英进行创作的“有限生产场次”,一个面向普通大众的“大生产场”。“有限生产场次”的自主化追求“通过形式的功能在美学上创造一切”,而这两种场域也会型构文学接受与消费上的二重性特征。李洱的创作正好与布尔迪厄所说的两种文学场域形成对照,即便李洱创作本身无意于割裂作品所面对的二重性结构。但在作家的“形式功能”探索、结构创新与超越道德寓言的“创造力”中,其小说的先锋性是确属无疑的。即便在《应物兄》中他试图通过一个基本的故事内核调和先锋与大众之间的痕迹,并以此完成对世俗百态的反映,但其非线性的讲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性、道德解构完成了“异质性”探索,获得了超凡脱俗的气质——一种区别于惯常的、传统的“新的写作”。这种写作因无法抹却的先锋性,成为“大生产场”的逆子,这也就是在读书平台上所说的“读不下去”“太痛苦了”等评价的根源,同样也是同道、同行高呼的“不可复制性”与“无限延伸性”的根源。但在其文学观中,所说的“故事完整性”与作为手段的非线性叙事是否构成逻辑悖反,小说总体性、道德建构与“情感教育”是否带来小说面对现实的失效,种种命题依旧值得讨论。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6月20日第5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