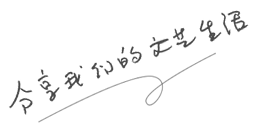彼特拉克《时间的凯旋》(局部)

维米尔作品《天文学家》

利弗·弗斯舒尔作品《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

文泽尔·哈布立克作品《星空:尝试》

卡斯蒂略金字塔在特殊光照时刻形成羽蛇神的“光影蛇形”
今年2月,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包括月掩土星、金星伴月、月掩火星、“七星连珠”等天文现象,引发了大量关注与讨论。古往今来,人们对天空总抱持着浪漫的想象与寄托,斗转星移,周而复始,春秋代序,生生不息。古人们“仰观于天,俯察于地”,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制定历法、设定都城、建构文明。在世界艺术史中,天象是一个重要的母题,艺术作品中的星空不仅是人类探索外部世界的明证,也是观照内在世界的记录。
早期建筑:与天象休戚相关的艺术
建筑是一种注重选址、方位、材质和采光的在地艺术。在中国古代词源学中,“建筑”的“建”字就是从天象观测中发展而来的。一年之中,北斗七星斗柄旋转,依次指向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农历月份即由此而定。在各大文明的源头,早期建筑的选址与建造都与天象休戚相关。
中国的古代建筑大多严格对应天象。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有观星台和呼应日行规律的四方祭坛。以瑶山祭坛为例,方形祭坛的四角方向正好指向夏至和冬至日的日出与日落方向,从祭坛中心,可以无遮挡地观测到完整的日行轨迹。古代的皇室建筑群对天象与方位的测算与遵从则更为严谨,颐和园中的十七孔桥,每当冬至日前后的傍晚时分,太阳落于最低点,阳光照射方向几乎与湖面平行,日落余晖会依次穿透桥洞,将十七个桥孔的侧壁照耀得通体透亮,伴随着日落时空气中的尘埃和水汽,形成“金光穿洞”的冬至奇景。
其他古代文明的建筑群中,基于对日出和日落的精准观测进行相应设计的案例亦有不少。英国南部的斯通亨奇是新石器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历史遗迹,建造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100年左右。虽然现在已经倾颓,但在其原始状态,这个巨石阵最外围有一圈壕沟,内部包含了几层同心圆排列的石圈,最高的石圈原本由30块直立巨石构成,巨石顶上置有相连的横条石。人们对斯通亨奇的建造方式和用途有多种推测,有天文学家认为斯通亨奇是观测天象的实体参照物,最外圈的石阵可等分为8份,八个等分点分别对应了正南、正北、昼夜平分点日出、昼夜平分点日落、夏至最北端月出、夏至最南端月出、冬至最北端月出和冬至最南端月出的方向,内圈的石洞则可用于预测日食。
在美洲,古玛雅人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复杂的文字体系,其天文和历法系统也十分成熟,这在古玛雅建筑中有直观的体现。古玛雅的城市建筑包括宫殿、天文观测台、金字塔神庙等。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玛雅遗迹奇琴伊察的中心,有一座玛雅文明鼎盛时期的金字塔建筑,即卡斯蒂略金字塔(也称为库库尔坎金字塔)。它是祭祀羽蛇神的神庙,羽蛇神在古玛雅文明中是太阳的化身。该金字塔底座为正方形,四个坡面上的阶梯朝向正南、正北、正东和正西四个方向,四面的台阶各有91阶,加上最顶部的一层共计365个台阶,正好是哈布历(以365天为周期)中一年的天数。52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象征着玛雅日历中以52年为周期的轮回。每当春分与秋分日,日出或日落之时,金字塔拐角的轮廓在北面阶梯上的投影如同蛇身,与阶梯底部的羽蛇神头像正好相连,形成完整的蛇形图案,这一切显然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和设计。古玛雅人极为重视天文数据,金字塔的设计处处呼应天文和历法的数字规律,体现出古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念。
说到金字塔,不得不提世界上最知名的金字塔群——位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金字塔。五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天文和数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很早就根据尼罗河涨落规律进行星座观察。古埃及人将尼罗河视为银河在地面的倒影,并在尼罗河畔建造吉萨金字塔群,呼应银河周边的星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座金字塔分别为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20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这三座金字塔的相对位置与猎户座的腰带三星(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相似,提出了“猎户座关联论”,认为金字塔的选址参考了猎户座的星象位置。21世纪初,人们发现除了排列位置上的呼应之外,这三座金字塔的高度正好对应了猎户座腰带三星的亮度,也就是说,最亮的那颗星所对应的金字塔高度最高。
无论石阵、祭坛还是神庙,它们的建造都反映了人类先民对天体观察的高度热情与精准计算,这是从基础的生存需要出发的。因为在尚未发明电力的时代,正是太阳、星空和火带来了光明,使先民们得以“看见”,这也成为人类活动的基础与前提。
纸卷、泥板与石刻:古老的星图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天空的想象与探索从未停止。从最初的肉眼观察到星盘、日晷和浑天仪等观测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古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天空的视觉图像和文本记录,星图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人类对恒星观测的一种形象记录,也被称为“星星的地图”。它既是人们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记录,也是人们对遥远星空的艺术表达。
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平面星图是一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中国纸卷。这卷“敦煌星图”又称为《敦煌星图甲本》,是敦煌经卷的一部分,绘制年代可追溯至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敦煌星图”客观且精准地展示了北天极附近的星空,描绘出包含1339颗恒星、257个星座的排布,比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借助天文望远镜完成的星体观测早了800多年。
长沙马王堆的三号汉墓中发现了精美的天文学著作,后被天文史学者称为《天文气象杂占》,该文本图文并举,绘制了包括恒星、彗星等各类星象图约250幅,其中包括31幅彗星图像,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关于彗星描述的珍贵史料。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带着尾巴的彗星用象形文字刻在了龟甲上。
19世纪末,在尼尼微(亚述都城之一,位于今伊拉克境内)亚述巴尼拔国王的地下图书馆,人们发现了一块盘形黏土泥板,泥板表面有极大损毁,据分析,现存的刻纹绘制的是公元前33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上空的星象,体现了古苏美尔人对星象的观察和理解。代表星空的泥板圆面被均等地划为8等份,其上猎户座和“V”字形的金牛座图案清晰可见,旁边的楔形文字则记载了相应的星座信息。这是两河流域文明对星图的较早刻画。
在古埃及文明留下的关于天空的视觉艺术中,位于丹德拉哈索尔神庙顶部的黄道十二宫雕刻作品是较为特殊的作品。这是已知最早的黄道十二宫图像。黄道是指地球上的人观察太阳一年内在恒星间所走的视路径,黄道两侧的区域就是黄道带。黄道十二宫是沿黄道带分布的十二个星座区域,起源于古巴比伦人对天空中星座的长期观测和占星术应用,他们将黄道分成各30度天区的12等份,称为十二宫。哈索尔神庙的这块黄道十二宫浮雕出现于古埃及的托勒密时期,有学者断定浮雕的年代为公元前52年。在浮雕中央圆盘中,核心位置画有北方星座,四周围绕着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符号,符号外围周边手持物件的小型人像代表着行星,圆盘最外围有序排列的是拟人化的36个黄道带分区。由此可见,彼时的古埃及天文学早已趋于标准化与精细化。
虽然星图的出现最早起源于各个古老文明的天象观测,计算方法和绘制方法各有不同,但在同一片星空下,它是人类智慧的共同见证,也是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视觉艺术。
绘画:科学带来的激情
伴随着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航海大发现和人文精神的觉醒,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被强调,看似遥不可及的天空逐渐褪去了神性的光环和玄秘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去神秘化的客观记录与自由的艺术创作。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中,星空呈现出不同的视觉面貌。
第一次对彗星进行忠实描绘的作品来自意大利画家乔托。据载,乔托在1301年见到了哈雷彗星,并于1305—1306年为斯克罗威尼礼拜堂南墙绘制湿壁画《东方三博士来朝》时,对其进行了精准描绘。这颗巨大的彗星出现在画作上方的蓝色天空中,被乔托描述为伯利恒之星。和日食月食一样,彗星的出现在整个中世纪都被人们认为是不祥之兆,往往与战争、瘟疫和死亡相关联。虽生于中世纪晚期,但鉴于乔托对自然的精确表现,艺术史家也将其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一位画家。
手抄本是中世纪时期重要的视觉艺术载体。在大量手抄本案例中,来自林堡兄弟的《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它是国际哥特式泥金装饰手抄本,大约完成于1412—1416年间,书中包含66幅大型细密画及65幅小型细密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12幅月令图,画作描绘了从一月到十二月人们的劳动场景。月令图的上半部分是半圆形的苍穹,对应当月的星座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天神。以《十月》的上空为例,驾着马车的太阳神阿波罗正将太阳托举至天空,外圈的星空图像中是天秤座和巨蟹座的星座符号,每个星座对应天空圆周的30度角,最外环的数字代表了刻度。作者另外绘制了一幅黄道十二宫星座与人体部位的对应图,从位于头部的白羊座到位于脚部的双鱼座,星象与人体彼此呼应。在当时,人们认为黄道星座主宰着身体各个部分的健康,这幅插图也成为中世纪医学占星学的重要图像文本。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天空的描绘和对星座的痴迷在艺术家群体中更为盛行。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诗人和人文主义学者,很少有人关注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位技法卓绝的画家,在寓意体长诗《凯旋》中他就加入了自己的画作。在一幅名为《时间的凯旋》的插图中,太阳在满天繁星中运行,横跨天空的黄道带上绘制着十二星座的对应图符,这是一个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想象性描绘,表达了人类的辉煌与天空中众星的狂欢。
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文艺复兴时期与达·芬奇齐名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也是第一位绘制古典星图的画家。1515年,他在数学家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和天文学家康拉德·海福格尔的帮助下,完成了欧洲第一部印刷星图的绘制,在其中两幅木刻版画中,他全面展示了黄道带以北及以南天球上的所有已知星座。虽然这两幅星图依然基于托勒密编录的星座体系,但海福格尔更新了这些星体在1500年出现的位置,丢勒根据坐标系统作了准确制图。这两幅天体图是在欧洲公布的最古老的版画星图,它们并非出于地球上的观测视角,而是基于天球外部的俯瞰视角完成,因此在北天体图中出现的星座形象都呈现为人体背部,南天体图则出现较多的空白区域,表明当时人们对南天星空知识的相对匮乏。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崇尚理性与科学的风潮涌动,视觉图像中的星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人们对星空的描绘趋于标准化和科学化。作为天文制图的高峰期,17世纪出现了《寰宇秩序》《赫维留星图》等精美的星图集与天文著作。这一切都与天文观测工具的发明有着直接联系。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将人类目力范围延展至云端之外,使曾经遥不可及的星空变得真实而具体。当年年末,伽利略根据观察所得完成了一幅《月球素描》,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月球表面各种凹凸结构及明暗对比下的盈亏状态,第一次让人类看清了月球的真实面貌,这也是艺术史中的第一幅天体素描写生。次年,伽利略出版了《星空使者》一书,书中收录了他观测到的月球图像。
到了17世纪中叶,天文学家乔瓦尼·多梅尼科·卡西尼在长期观察后发现木星上的风暴时,也同样选择以手绘的方式记录了1665年、1672年和1677年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些绘画记录的正是人们熟知的木星大红斑,但此观点仍具争议。1666年,卡西尼被路易十四任命为新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次年担任新成立的巴黎天文台台长。当时的巴黎地图销售商之子尼古拉斯·德·费尔刻制了一组巴黎天文台的版画。我们在其中一张画作中看到当时天文学家们的观测景象,大型天文望远镜架在天文台外的平地上,天文学家们正在观测月食的发生。
彼时的艺术家们对天体包括对地球本身都充满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以“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维米尔为例,他在光学、制图学、音乐、地理学和天文学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积累。绘制于1668年的油画作品《天文学家》,从命名上就体现了他对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关注。也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绘画作品中出现彗星的场景不再伴随着人类的惊惧、疾病与死亡。相较于托勒密时代所认为的不详预兆,彗星在1705年得到了天文学上的正名,哈雷发表《天文学对彗星的简介》,将其解释为一颗具有周期回归特性的天体。所以在另一位荷兰画家利弗·弗斯舒尔绘制的油画《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中,一颗从天而降的彗星出现于鹿特丹上空,城市中的人们并未惊慌失措,而是井然有序地驻足观望,甚至拿起了手中的望远镜观察。
如果说启蒙运动时期是星空图像的理性化与科学化时期,那么艺术创作进入现代世界后,则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视觉形式,太空美术、星空艺术、宇宙电影等层出不穷。脱离于理性的标准和规制,艺术中的星空重新成为艺术家笔下带有浪漫色彩和主观意趣的图像主题。
艺术史上最知名的星空当属梵高的《星月夜》。比梵高小10岁的蒙克,同样曾生活于巴黎并深受印象派影响。他的油画作品《星空》是对梵高《罗纳河上的星夜》的致敬,只是蒙克笔下的星空闪现着如同极光般的大面块绿色,整体呈静谧与深沉的基调。与蒙克同为表现主义画派的文泽尔·哈布立克也绘制了星空主题作品,他的《星空:尝试》使人仿佛置身星群,众多星辰与天体在银河中的旋转律动体现出一种神秘的秩序感。
随着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成功,天上的星星成为可以抵达的彼岸,艺术家们不再甘于像伽利略或卡西尼那样,只是将星体视为被观看的客体或他者,而是将人的形象安置到星体之上,强调人类自身的“在场”。例如,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月球行走》定格了阿姆斯特朗登月的经典历史瞬间,以波普艺术的风格化处理,强调人类与星体的共在。某种意义上说,“登月”是一个人的小小一步,却是人类的一个巨大飞跃,“登月图像”也是漫长的世界艺术史上,人类星际巡游和天空想象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从建筑艺术对天象的呼应,到视觉艺术对星空或理性、或感性的描绘,天文学与艺术形成了如同双子星般的共生关系,我们头上的这片星空逐渐褪去未知的面纱,图像中的星空也不再只是一个被遥看的对象,而是成了可知、可探、可及的宇宙。
(作者:陆颖,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