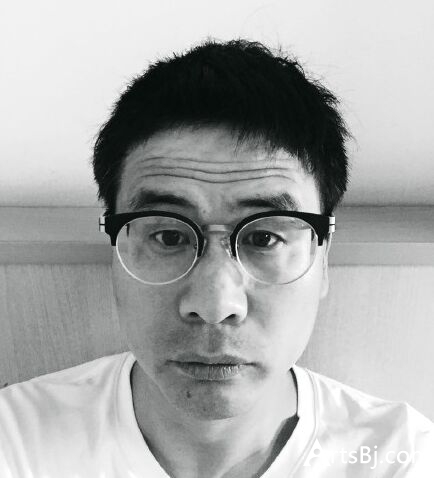
哥哥,
已經有超過十年的時間我沒有再這樣叫你。我還記得,有一次從教會出來,討論起應該怎麼叫你,我們都喜歡“緒林哥哥”這個名字,再到後來,就叫哥哥了。
哥哥,多年前,當我們分開時,我在憤懣之下寫了一篇文章。只放了一天,便刪掉了;而你似乎從來沒有就我們三年的關係寫過隻言片語。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都不敢肯定這段感情在你生命中的位置,或許,你到最後也不曾明白你對我的意義。然而,你留給世界的背影是那麼孤獨寂寞,我總覺得應該把我們的故事寫下來,成為你在世界上帶有溫情的一闕記憶。後來,網上慢慢出現了越來越多關於你的回憶,我們的那段往事又被提起。微博上,也開始有陌生人來問我,甚至感謝我。看到崇明的紀念文字,我才忐忑地相信,在你的心裡,我們的過去並不總是你想遺忘的一段往事。2006年一別,我刪掉了關於你的一切聯繫,義無反顧地往前奔去;在你離開後,我開始慢慢去經歷你的生活,看你的微博,你的博客,你的信,聽你聽的歌……這一個多月,仿佛活在兩重平行的現實裡。過去的細節突然重新被喚醒,我又再次經歷著快樂,心酸,埋怨,憤怒,悲傷,歎息……在這篇為你而寫的文字裡,我盡可能地記錄下我們生活的點滴;像所有關心過你的人所希望的那樣,你的存在和離別都如此獨特,固然是悲劇,它也不應該僅僅只剩絕望,而更應該是一個得到理解和救贖、充滿啟迪的故事。如果說,我未能在你生前全然明白你(那曾經是我所期待的),那麼讓這一次對你文字的不斷重溫中,我能更貼近你,讓你在我的記憶裡再活一次。
2002年末,我們相識於北京的北大團契。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個初初接觸信仰的小姑娘,憑著一腔熱情往教會去。我留意到你是因為每次崇拜結束,我幫忙搬凳子時,你常常會背靠在後牆上看著我。我禮貌地向你點頭示意,你卻又不怎麼搭理;我心裡有點小慍怒,慢慢也就不了了之。我們真正的交往始於2002年聖誕交換禮物,你剛剛好抽到我帶去的禮物,是一個深紅色的小相冊,在回家的公車上,我們交換了電郵,並且知道你學哲學。通過郵件,我們開始了交往。從一開始,本能的,我似乎就明白我們氣質上的相似之處:追求純粹天真的生活品質,進而衍生出一種近乎冷酷的自我審視和剖析,那其實也是強烈自我中心的反映;另一方面,卻是常常在現實生活中的手足無措,脆弱而無助。在日記裡,我記下了看見你文字時的感動,你說:“在逐漸戰勝自卑和盲目的道路上,我只能默默地掙扎和前進,時時抗拒著被日常生活吞噬的危險,又忍受著最終一事無成的危險,並告誡自己,單單是真理之路就值得向前走”。於我而言,在我20年的生命裡,第一次遇到一個這麼清澈的人,在你裡面,我好像看到了一個小小的自己。慢慢地,我也知道了你在北大三角地點蠟燭的事,看到你寫的《愛的和解》,以及那一篇敲骨食髓的《非徹底之自我澄清》。時隔多年,我也不記得信裡的很多具體內容了,但我卻記得讀完時的無力感,一種遇到同類的慶倖與惶恐,仿佛在突然間被洞悉。我曾說過,固然文字中的你與你給我的孱弱模樣有出入,卻也並非你想像的那麼讓我驚訝。那些你對自我的殘酷剖析也常常出現在我的自我審視中,那些在自卑與驕傲雙重碾壓下的艱難掙扎也注入在我的生命底色。 只是我把自己的心保護得很好,從不曾毫無防備地交出去,以至於常常覺得它已經被凍結在一層冰冷堅硬的外殼下。
2003年春節,我回家探親前,你突然有一天來找我,拎著一大袋零食要我回家的路上吃。你的饋贈幾乎是魯莽而粗暴的,而我卻看見一個單純如孩子般的你。我當然知道,你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是可以灼傷人的,對於遠遠觀望者而言,這或許也可以稱之為浪漫;但對於你熱情所及的對象,那種熱情帶著讓人無法理解的爆發力量,讓人驚懼到想要逃走。然而,對我,哥哥,你正是帶著這樣的熱情,消融了包裹著的外殼,直直地闖到我心裡來。或許你並不知道,於那時的我而言,接受比饋贈更艱難,因為前者意味著放下防備,把自己放在一個弱者的位置上。
我們的關係便是在那一個假期確定的。我依然清晰記得當時的情形。我躲在臥室的床上給小侄女念童話,你打電話過來,我便念給你聽,正是《海的女兒》。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來童話也是可以這樣美的:彷彿金色的陽光照進藍色的海裡,那些語句就像“金色的字符”,像你說的那樣,輕快又帶著點淡淡的憂傷。然後……你說,“我可以照顧你嗎?”,我輕輕地回答“可以啊~”,是極為平靜的,以致於我後來常常疑惑自己。停了好一會,你接著說“我可以照顧你一輩子嗎?”,我心裡有點驚異,喃喃地說,“不知道呢!” 那時的你多傻呀,如此輕易地說一輩子,何曾知道一輩子是那麼遙遠的事情??假期結束回到北京,你來車站接我,送我回學校。快到宿舍時,轉角處,你突然抱住我,親吻我,一如既往的急切,那是一個尷尬而粗魯的吻;我一直沒有告訴你,當下的我是有小小不悅的,然而,心底也知道,那是你孩子氣的一貫表現。
我們開始戀愛了。還記得那次我們掉進未名湖的事嗎?那應該也是一個初春的日子,我們沿著未名湖散步,湖裡零零星星地有滑冰的人,我們沿著結冰的湖面往湖心走去,大約冰開始化了,快到中心的時候,一下子踏破了冰面,跌進了湖底的泥濘裡,齊腰深。心裡不是沒有恐懼的,我們一腳深、一腳淺地沿著冰面往岸上爬去,承受不了重壓,冰面不斷地碎裂;我在前面,你在後面,時不時還托著我;走了好一會,才終於走到冰面比較結實的地方,靠著別人遞來的一根掃把,爬了上來。然後,兩個人穿著濕答答淌泥水的衣服,可憐巴巴地站上公車,回你的住處。那時你已經工作,就住在離我學校不遠的地方。到了你的住處,我換上你寬大的白球鞋,擰著自己的一雙泥鞋,再走回自己的宿舍。傍晚的時候,你又跑來找我,說邵荊責怪你不會照顧女孩,既不讓我換身衣服,又不送我回去。可是,你也有他不瞭解的溫柔:我走路的習慣不好,常常不自覺就往馬路中間靠,你怕我出意外,只要我們一起,你就一定會走在外面,把我擋在裡頭。而關於掉進湖裡的這件事,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你覺得這是個不好的兆頭,心裡悶悶地頗不開心;我安慰你,說自己其實是有點高興的,甚至覺得我們也算是一起經歷了生死。
如果說我們的愛情有什麼特別之處,或許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極度坦誠,既是對自己,也是對彼此。即使在我們最相愛的時候,也常常互相提醒,要坦承並守護最真實自由的自己與對方,就算那可能也意味著殘酷。比起愛情中的呢喃,我們更像是在反覆的審視和確認中摸索前行。我們深知你的孱弱,卻也懷有希望:你會長大成為我的牧者,做彼此靈魂的傾聽者。我們就像兩個學習相愛的孩子,急赤赤的把自己的心捧給對方,太過用力,不惜割傷彼此。我對愛、對信仰的許多理解,便是在你的影響下塑造而成。我們的戀愛從一開始,就伴隨著你對信仰漸行漸遠的猶疑和我初涉信仰的各種問題。那時,我最糾結地便是“神存在的確據”以及“愛的本質”。因著我們的關係,“愛是什麼?”變成了我常常追問你的問題。你坦誠無法給我直指靈魂的答案,卻也包容我的疑惑,引導我在文字中找尋。當然,最重要的是小德蘭的《一朵小白花》。現在想來,我對這本書的喜愛完全來源於你。你說,這是寫入你靈魂深處的;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你心中信仰最純粹的模樣,也是你心中愛情最純粹的模樣,更何況,它還曾以現世的模樣出現在你的生命中。是的,也許和很多人想像的不同,你的感情經歷遠非白紙一張,甚至比很多人經歷過的更豐富。你過往對信仰的虔敬裡也交織著對昕怡絕望的愛慕,在那時的我看來,是一個神聖的、我永無法企及的高度。還記得有一次崇拜時,講者讓我們回憶生命裡最重要的三件事。我把我們的相遇當作其一;然後,偷偷看旁邊的你所寫的答案:考上人大,接受信仰,以及在北大點燃的蠟燭。我理解,也不無感傷。所以,哥哥,你可曾察覺我在這段關係裡也有過的自卑之心。小德蘭說,“本質上愛是一種俯就。” 它安慰了部分的我,卻不足夠。固執的理性讓我無法毫無芥蒂地投入委身在上主的俯就中,成爲他園圃中的一朵小白花,全心等候著他偶然的駐足。事實上,你也一樣,終究無法虔信。我最大的安慰來自西蒙·薇依,那個遊蕩在現代社會裏的孤獨自由的信仰掙紮者。永遠的異鄉人和旁觀者,這是我願意接受的標簽,抑或它們更適合你,甚至這或許就是你那如影隨形的不自在的源頭。薇依的《在期待之中》是你給我的另一本小書,晦澀難懂,我看得艱難。然而,她寫到:“愛是一種方向,我們即使在絕望中,也要朝著那個方向,等待上帝愛的長釘刺穿我們的靈魂……讓世界的兩個盡頭相遇。” 那是我躲在熄燈後昏暗的水房裡看到的句子,深夜三點,它抓住了我。我愛這句話,不僅僅因為在薇依身上找到更強的認同感,更因為這裡的愛是一個動詞,比起上帝俯就的垂憐,動詞的愛更有掙扎的生命力。在你離開後,這句話又一再的浮現在我腦海裡。我悲傷地發現,在你對上主的期待之中,終究沒有等到愛的長釘刺穿你的靈魂,彌合你在自然與信仰之間的艱難掙扎,終竟撕裂自己。
在疑慮和審視中,我們仍在慢慢地走近彼此。就像你說的那樣,儘管“問的是‘愛是什麽?’,而目光中仍滿是柔情。” 我想,我迷戀你溫柔的聲音和你的文字,不論何時。如果說文字真的有力量的話,你的文字就是現實中曾經最能打動我的力量之一。我慢慢走進你的生活,你帶我去見兒時的玩伴,夏夏和他太太在北京買的新居。因為裝修的一點意外,夏夏還進了一次醫院,我們去看他,順便還嘲笑了他一把。還記得從他們家出來,我們坐在樓下的長椅上,你抱著我,我們談論他們的故事和我們的未來。知道你的未來裡有我,讓我溫暖而開心。和你分開後,我也斷了和夏夏的聯繫,你離開以後,夏夏在臉書上找到我,我們重新談論起你和我們共同的過去,恍若隔世。
伴隨著2003年的還有我的畢業和蔓延全國的非典。學校被封了起來,禁止出入。你也搬回到黃村去住,每天我們只是在電話裡瞭解彼此的生活。後來,疫情趨於穩定,戒備也沒有那麼森嚴了,你便坐著空蕩蕩的300路公車穿過大半個城市來看我。一兩個月不見,我們坐在黑色欄杆的內外,傻笑著望對方。有陌生人走過,好奇地問,“你們在做什麼?”。我望著他,笑盈盈而理直氣壯地大聲回答“談戀愛呀!” 哥哥,你還記得嗎?非典帶來的驚恐慢慢散去,我們卻日漸趨近地面對另一個難題,那觸手可及的分離。我已決定去香港讀書,而你仍需留在中華書局工作。我們也談論現實的未來和在即的別離,我決定離開前搬去黃村和你一起生活。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是對情欲的妥協,我們並非不知;然而,那時我更視之為一種委身的承諾。即便後來有過懊惱,也從未真正後悔過。事實上,那20天的生活是我們現實中唯一最接近的時候,你曾稱之為 “Golden Time in Beijing”;在那以後,我們再沒有如此親近過。其實,我之前去過黃村一次,你留我吃晚飯,害我錯過回城的最後一班公車。後來在張繼海的回憶文字,說起你拿著廚具奔向公共廚房的慌張樣子,應該就是那次。想著你當時的情形,我仍然忍俊不禁。我還記得你那簡陋的房間,猩猩紅的法蘭絨窗簾,靠在牆邊的小床。因為回不了城,我便霸佔了你的小床,你只能睡在鋪著塑膠墊的地板上。淩晨的微光裡,我在睡夢中感到注視的目光,睜開眼,見你坐在床邊,癡癡地看著我,然後就定格在我記憶裡。
經過記憶的沖涮,留下的都是美好,在黃村的日子也是如此。我記得多少次你在半醒半夢間,抱我,迷糊的呢喃:“我的愛人”, “愛你”;也會在清醒的時候望著我,然後溫柔地說:“好美!”,常常飯也吃得不安生。 因著身體的孱弱,你夜裡睡得不太好,可我害怕空蕩蕩的走廊,起夜時總要你陪。就算你難得地安眠了,我要你陪時,你總是溫順地爬起來,迷迷瞪瞪地牽著我,穿過房間,站在黑暗的廁所門外打瞌睡。我特別愛看你的側臉,尤其是你看書的時候,常常不自覺地咬著下嘴唇,便流露出一個倔強小孩的模樣。我甚至不知不覺間學會了你慣常的歎息,你心疼地笑我,我卻高興說,“多好,我可以代替掉你一半的歎息呢”。我毫不懷疑,那時的我們是全心全意地愛著對方的。你也會陪我逛超市,只是不再負責做飯,只管洗碗了。我也知道了黃村的早市,便宜新鮮,就是要早起。你睡得不好,有時會想偷懶。一天早晨,我趕著早市出了門,你還賴在床上。結果,買雞肉的時候,一雙手從背後蒙住了我的眼睛。我轉身看到一臉笑意的你。你終究不願我一個人,從床上爬起來,追著我跑了出來,找了好幾圈,才找著我。你的孩子氣是那麼讓人心疼和好笑。大約你數學不太好,對於學物理的我有點毫無根據的盲目崇拜。我們偶爾也會討論些數學問題。忘記有一次討論起什麼來,應該是一個很小的數,我隨口說了一個“十分之一”,你胡縐了一個“百億分之一”,我去做飯了,你還在那裡興致勃勃地算了半天,結果發現自己竟然蒙對了,可把你得意壞了!洋洋得意地沖進公共廚房,向我宣佈自己的準確,開心了好久!那段時間,你不太肯去教會了,星期天我就自己去。你掛念我,在房間裡呆不住,寧肯跑到公車站來等我,一邊看書,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實這件事我已經不太記得了,但在你的記憶裡,卻是你等我的一次經典回憶。留在我印象中的倒是有一次你在師大物理樓等我的情形,我還記得看見你時的開心,飛奔著跑過去,抱著你。還有一次是在香港,我去深圳,你就坐在大學站外的花臺上,看著書,等了一個下午。在記憶裡,那是個陽光明媚的傍晚,我從深圳回來,看見你,望著我笑,歲月靜好。但就像普魯斯特說的那樣:“我們相互間的看法,以及友好的關係和家裡的關係,只是表面上固定不變,實際上卻像大海一樣時刻都在變化。” 在香港的我們其實並不好,早已不復過去。
離別在即,你拖著我去過一次西單,非要買一枚戒指給我。那時我覺得貴,要100多塊,不想你買,你堅持。如果非要相信命運,在我眼裡,這才是命運之輪讖言中的第一個暗示。那枚戒指在我到達深圳姑媽家的第一天就不見了,洗衣服的時候,戒指脫了出來,被沖進了下水道。幾天後,我的錢包在公車上被人偷走,裡面有我們一起拍的大頭貼。你對此極為不安,可讓我不安的卻是你信裡蔓延著的脆弱。我沒有想到,或者你自己也不知,我的離去會對你造成如此之大的危機。你對自己的不幸以及隱藏在你秉性中的潛在危險有著極為敏銳的直覺,你所有的激烈感情裡都天然地攜帶著尋求拯救的希望,它們既讓你投入,也帶給你恐懼。你甚至無法在黃村繼續住下去,搬去了北大。我在香港開始了新生活,挫敗也充滿新奇;你在北京獨自煎熬,準備著來香港的申請。我們的思念維繫在纖弱的電話線兩端,以及往來的書信裡。哥哥,你是柔弱的,而你也是堅強的,如你期望的那樣,不論多麼艱難,你仍然用努力維繫著自身的尊嚴。你努力地工作、學習、準備考試,也忍受著內心敏感的不安;我一次次向你確認我的感情,擔心著你的身體,然而我必須要承認,你的緊張不安也帶給我脅迫和壓力,我的心裡不是沒有委屈的。可是事情終究向著不好的方向發展而去。
2003年聖誕,你來香港看我,興沖沖地來,卻傷心離去。我還記得來之前,阿敏托你帶信給我;她看著你那鼓鼓囊囊的行李裡全是給我帶的零食,自己卻凍得連一副手套都沒有。後來她叮囑我,要好好愛你,記得給你買一副手套,可是我卻不記得;你看,哥哥,和你一樣,在生活裡,我也是一個糊塗蟲。你來的時候,我室友不在,我卻把你安置在訪客區。你悶悶不樂,總覺得那是我對你的疏離。我想把你介紹給我的同學和新朋友,你也不樂意,甚至不願意和他們一起打球,你不喜歡我和他們一起打球。我們倆跑去上環找一個有著美麗名字的教堂;也在學校裡面轉悠,在未園湖畔留下我們親昵的照片。十幾年了,那一叢翠竹還在,我常常會從它們旁邊經過,你離開後,我才如此真實地感覺到物是人非。可是,你仍然不開心,你的笑也鬱鬱寡歡,我們為著毫不起眼的小事爭吵。不,你不喜歡爭吵,只是沉默……
帶著這些不快,你回到了北京。之後便是不安中的猜疑和追問。敏感的你能捕捉到我的任何一絲逃避和保留,你痛苦地追問並要求我的坦誠。我不得不告訴你對別人曾經有過的一絲好感。那是一起打球的同學,和孱弱憂鬱的你剛剛相反,他是一個健康陽光的男孩。對我而言,這僅僅是情緒的一種波動,更多的是出於少女的好奇心和虛榮心,甚至也像是一種思想實驗,從而來探索愛的可能性。我從來沒有想過背棄自己的愛情;我明白自己對你的意義,也明白你對我的。不告訴你,是對你孱弱身心的擔憂;告訴你,是因為你對坦誠的要求。然而,對你來說,這卻是致命的:你說,“我們都能體察到某種一閃即逝的意念,那對過去的生活構成顛覆地意念。” 你在痛苦中寫給我許多的信簽,即便十幾年後,我再讀時,依然淚水漣漣。哥哥,我無法體察你當時的孤獨掙扎,你的失眠、嘔吐和心灰意冷,而我當時也沉浸在自己的小委屈裡。你在痛苦中重新轉向上主,祈求他的醫治。可是,哥哥,你卻並不知道,你所以為的我的疏離,也是我轉向上主的舉動呀!一年以後,我們的關係重新進入短暫的親密,某次長談之後,我才驚覺這件事與其是說我們感情裡的一次事故,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場誤會:你把我擺脫情欲糾纏的努力看成是我對你的離棄,更何況還夾雜著我對他人好感的確認。然而,它確實地攪動起你情感甚至靈魂中的驚濤駭浪,也動搖了我們感情的根基,至少是屬於你的那一部分。你最終從打擊中恢復過來,而代價是對我的盲目的愛,我不再是你所迷戀的那個女孩;我在日記裡留下痛悔,為自己不經意間失落的愛情悲傷,也再次確認人的軟弱失信,包括我也包括你。那時的我堅信,軟弱如我們,唯一出路只在上主的恩典裡,我匍匐在主前,渴望把它重新找回來。十幾年後,當我再次回憶起這段往事,當時空得以拉開距離,允許我審視你的整個生命時,我才能更清楚地看見這件事對你的顛覆意義:它比我曾經以為地更致命。我仍然低估了你那理想主義的對純粹的極致追求,這種追求寫在你對小德蘭、對昕怡的傾慕中;寫在你對信仰的掙扎裡;寫在你對學術、對自我品性的要求裡。當你把我納入你的世界,作為一種尋求生活救贖的方式,你對純粹的追求就必然地加諸在我身上,因為親近,愈加濃烈。而我卻讓你失望了~這種失望伴隨著我們關係中的第一道裂痕,崩裂在某個深不可見之處,我幾乎可以聽到那從你靈魂深淵處傳來的巨響,最終坍塌了我們的愛情。我甚至覺得,正是這種對純粹的追求,讓你無法面對家鄉的姐姐,那裡固然有你無力面對的生活之艱難,更有與你所追求的純粹精神世界無法匹配的凡俗。因為是至親,你才愈發不能面對這種衝突帶來的撕裂。正是靠著追逐這一抹理想主義的光華,你超越了童年時期的現實苦難;然而,也正是這同樣的理想主義的光華,在你和現實生活之間劃下了一道鴻溝;它的純粹終究無法延伸至生活,因爲生活本身就是從泥土裏生長起來的。你追逐著它而去,把我、把姐姐劃歸到你夢想的世界以外;然而你終不能擺脫自己,你與自我的鬥爭驚心動魄,最終竟至熄滅了生命之火。
表面上,我們熬過了這一次情感的波折,進入平淡的2004年。你如願來到香港求學,我們還一起去過我的家鄉,一個偏僻的小縣城。在那裏,你見到了我那楚楚可憐的小侄女,她在無知中見證了我們的愛情,你憐惜她眼裏過早的憂傷;如今,她已長大,馬上就要考大學了,只是,她終究沒有長成我們期望的模樣,還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劇便被生活吞噬,或者這正是她的幸運之處,和每一個幸福的平凡人一樣。除了學業,我的生活重心轉移到信仰上。告別了北京那半地下式受到壓制的家庭教會,我可以在正統的教會下得到牧養,可以光明正大地進入團契生活。如果我的靈命曾經有過些許的增長,那便是在香港的日子。我曾那麼確信香港是上主放在我生命裡的旨意,而你,我的哥哥,便是上帝讓我學習愛和順服的功課。早在我們結識之初,儘管你在信仰上漸行漸遠,也曾盼望著我能像耶穌愛罪人一般地愛你;縱使口裡常有悖逆的話語,你卻也真心盼望著上帝能將我們的Eros洗淨成為Agape。 我和薩薩一起在主裡學習成長,她是我在香港最親密的姊妹,或許也是唯一見證了我們分離的朋友。現在,她仍然保有對主的熱情,而我卻已遺失了信仰。在你離開後,我們通過一次電話,她記得你曾提過喜歡《約伯記》,還給了我有關於此的一段講道,只是,我現在已不願再聽。
現實地看,我們正在步入生活,可同時,日常生活的瑣碎和庸俗也帶來精神上的麻木和遲鈍。你甚至不再耐煩我們每日的電話,也覺得兩個學校間的奔波浪費時間。儘管我努力在主裡成長,我也知道,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是遲鈍而遠離聖潔的。我會不滿你對生活的無措,也會發脾氣,會為你的偶然疏忽不快,也不再對你的感受保持高度敏感,甚至也不再無條件接納你在信仰裏的掙紮。那一年我們之間的書信明顯地減少了。到了11月,就在我生日前幾天,你終於不耐生活的瑣碎,向我提出了分手。我不解而失措,去浸會追問你原因。你不肯見我,我坐在你宿舍樓下的長椅上泣不成聲。你告訴我,你已失去對我的感覺,只想專注於學業。我接受了你的解釋,像我們曾經承諾的那樣:當彼此不再相愛,無法助佑對方成長時,給對方自由;因為我們視彼此的自由幸福為超越愛情之事。我一邊流淚,一邊叮囑你注意身體,在黃昏的日影下擦乾眼淚,孤身回家。才走到又一城,你的電話就打來,你在電話的那端如孩子般地痛哭失聲,讓我回去;我轉身往回奔去,在你宿舍外的街道上撞見迎面奔來的你。在異鄉的街頭,陌生的人流中,你不顧一切地抱著我,旁若無人地親吻我,淚流滿面,讓我不要離開你。哥哥,我後來常常覺得,在你如孩子般的痛哭中,流盡了對我最後的愛情。你雖然文弱,卻極少哭泣;在痛苦中,也只是讓人心疼地倔強沉默;這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眼裡,你為我而流的眼淚是我們愛情的高潮,也是結束。我無法抗拒。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你極為眷戀我,仿佛又回到了初戀的時候。也是在那一段時間,我才知道了一年前你的痛苦,更定意將我們的感情交付與主。因為不忍分離,我們決定結伴回家,甚至真實地談論起訂婚來。你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了,我們便一起先去了紅安,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姐姐。那時,你儘管長年不回家,對姐姐卻一直保有溫柔深厚的孺慕之情。姐姐讀的書不多,但和你一樣,有一種天生的對世情的敏銳感受力。她和我談起你們童年時候的艱難,也不過是淡淡的憂傷。我還記得,第一天夜裏,我和姐姐一起睡覺的時候,她略帶卑微地表達自己的熱情,讓我永遠銘記在心。我因為血液循環不好,冬天手腳冰涼,姐姐摸到我冰涼的腳,有點心疼得把我的腳摟在懷裏,幫我搓暖它們。她說,很高興我們能一起回去,很高興看到我們在一起。姐姐心裏一直擔心你,看到我們在一起,她就放心了。你離開以後,我給姐姐打過幾次電話,但似乎已無言以對,我不知道姐姐會不會對我也有埋怨,我們現在只能空洞地祝願彼此好好生活。
但那時,姐姐和你都對我很好。你的家鄉在一個美麗寧靜的鄉村,你帶我去看童年遊蕩的地方,一條几近荒廢的石壕溝,你告訴我童年時多少次在那裡看書或發呆,對面山坡上到春天或許就開滿了你記憶裡漫山的映山紅;你也指給我童年時愛藏身的一塊大石頭,在某個偷偷溜出來的夜裡你躺在上面,癡望著滿天的繁星,在胡思亂想中睡去,一邊還憂懼著從山裡隱隱傳來的狼嚎,一覺就睡到晨露打濕衣襟。我們去看村子裡的人打糍粑,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糍粑,姐姐把它們用油煎了,放上些紅糖吧,軟糯粘口,臨走我們還拎了一大包;你也帶我翻山越嶺去看各式各樣的親戚,把我展覽給他們看,後面跟著忠實的小跟屁蟲,你的小侄子。他和你一樣,倔強好強,也是個小書蟲;回來之後,我還為他和我的小侄女寫過一篇文章,叫《兩個小孩子》,那是我難得被你稱讚過的文章。哥哥,你可還記得我們的孩子氣?在姐姐家裡,我們實踐耶穌所說的彼此洗腳與服侍,兩雙腳淘氣在一個洗腳盆裡,你幫我洗,把我的腳抱在膝蓋上,擦得乾乾淨淨,我也幫你做同樣的事,小郭倫就在旁邊,捂著嘴不懷好意地笑。因為怕凍,你們不肯起床,我就鑽進你們的被窩,三個人坐著聊天。哥哥,你一定不記得了。後來偶然問起姐姐和你侄子的情況,仿佛你們已經日漸疏遠,你自責對侄子的苛責與嚴厲,不知道他現在諒解了你否?
離開了你家,我們再一起去我家。現在想來,這遠非一段開心的旅程。有時我想,如果沒有當時的不快,我們會不會已經結婚?然而,那時的我們太過年輕,不經世故,拎著從紅安帶去的一包糍粑就去了我家。我爸爸媽媽很不開心,覺得你不懂禮,新年拜訪卻沒有準備像樣的禮物。我知道了他們的抱怨,逼著你送給他們1200塊錢。以你的性格,一定不快極了。在彆扭中,更多的不快接踵而至,我處在你和父母的夾縫裡,終於把委屈都發在了你身上,在大街上,在表姐和她朋友面前沖你發了火,拋下你一個人,徑直先回了家。和往常一樣,你只是倔強地沉默,但我能夠想像,當時的你有多麼難堪和無助。從我家回香港以後,你再也沒有提起過訂婚的事。你離開後,我曾經裝作無意地和父母說起你的離世,他們不過簡單地慨歎了幾句,早就忘了當年發生的事。他們永無法知道,也許就是那1200塊錢的堅持,就斷送了你進入婚姻的念想。是啊,對他們而言,你只是見過兩面的陌生人;事實上,作為一個女兒的父母,他們並不喜悅你身上流露的敏感、憂鬱和孱弱,僅僅是因為我的原因,他們不情不願地勉強接受了你。我並不怪他們,只是慨歎生活的無常與殘酷。
命運之輪終於駛進2005,在這一年裡,伴隨著我再一次畢業的是我們間冗長反復的分分合合,一點點削薄著我們的感情,最終輕得像風一樣,消散在時間中。生活還在繼續,我們仍在其間顛簸。我仍會在禱告裡交托並紀念我們的關係,而在生活中,我開始迷上護膚這件事。可笑的是,我們最後的一點聯繫竟然也跟護膚扯上了關係。你離開前的一個星期,在微博上提到了我寫的年度護膚總結,在你離開後,很多人從你的鏈結裡找到了這篇文章,大概這是我寫的所有文章裡,最多反響的一篇。生活的冷酷常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現,讓人措手不及。我想沒有人知道,也是因為護膚這件事,我忘記了你的30歲生日。2005年的3月14日你滿30歲,那時正是我剛開始沉迷護膚的時候,我拖著你陪我去中環看皮膚科醫生,一直弄到夜裡8、9點才回到九龍塘。我想你是故意的,突然說想去看又一城正在進行的車展,我心裡正惦記著去買心儀的護膚品,便耍著小脾氣拖走了你。你也不說什麼,悶悶不樂地陪著我。分開後,直到夜裡,我在睡夢中才突然驚醒錯過了你的生日,半夜急匆匆地打電話給你,再三向你道歉。你不置可否,我問你為什麼不提醒我,你辯解說以為我是想給你驚喜。我想,你心裡還是怪我的,後來,你在BBS上發了篇帖子,輕描淡寫地抱怨這件事。有時候,人的記憶真的是很奇怪,直到今天,我還能記起你那篇帖子的內容,甚至你的用詞和字句,仿佛隨時都能浮在記憶裡。十年後,你的40歲生日,你說自己鼓起勇氣發了張自拍,我第一個留言,希望也是第一個祝福你生日的人,至少是在微博上。可誰又會知道,這竟會是你在世上的最後一個生日。
在那之後不久,我們便進入2005年的第一次分手,為著一件可笑至極的小事。當我翻開日記,嘗試去追尋那段記憶的痕跡時,卻發現在那幾個月的情緒糾纏裡,早已理不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留在日記裡的,是一大段一大段糾結的情緒,痛苦的禱告,反復不定的信心。我們分分合合,好好壞壞,有時是我提出分手,更多的是你。我們仿佛又退回到對愛情的猶疑和審視中,只是這次不再是為了接近對方,而是為了看清我們關係的真相。或者,這就是他們說的在步入與你更親密關係上的舉步維艱。而我們性格中的弱點和分歧也在這些掙扎中不斷被強化。回望過去,我的決絕中總帶著上主的希望,更指向一種有距離的審視,仍期待著美好的重逢;如果說你的信仰裡天然地攜帶了對昕怡的戀慕,那麼我的信仰裡也融進了對你的愛情。或許是本能的,也可能是在你的影響下,我不由自主地把我們的愛情和你的得救聯繫在一起。我也是這樣來看待自己對你的意義。而你的決絕中總有無法擺脫的自我厭棄:情緒的麻木、對自我經濟前景的不安,對責任的恐懼。你說:“當我一刀斬斷的時候, 切去的只是壞的肢體, 妳是好的, 我是壞的. '義與不義怎能同負一軛'呢?” 我傷心失望,“你還愛我嗎?”,這是我唯一關心的問題。在對你的不斷追問裡,從你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言語間,我努力去捕捉你的本意,那時的你對我已不再透明:我既無法接受你僅僅出於責任的愛情,也無法忍心讓你在失望中自我放逐。哥哥,可還記得,你曾說過:“珍惜我,在乎我。不要讓我在曠野中迷失,因爲甚至回音也無從尋找。” 我不是不能明白你的掙扎,但仍需要時間來沉澱真相。時至今日,當我可以抽離情緒,用一種旁觀者的眼光再來理解時,才能更深地明白你當時的掙扎:那是你嘗試自我安頓,進入生活的又一次戰爭啊!在理想與現實間,在自由與羈絆間,在恐懼與期待間,你肩負著命運的創傷,努力地辨別自我救贖的道路。這就是你自我爭鬥的戰場呀!而那時的我,卻陷在自己的痛苦裡,視若無睹!不!更準確地說,那時的我,也在愛的痛苦裡,尋求自我的救贖。在日記裡,我也不斷而冷酷地審問自己,追問天父,是什麼讓我仍不肯放棄。我所堅持的是什麼?我還愛你嗎,我可憐而脆弱的哥哥?穿過由生活的細節和瑣碎填滿的距離,我們早已模糊了對方的面目;縱然如此,可我永遠記得在時空的某一個瞬間,我們看到過坦然無偽的彼此,在那一瞥間,我們找到了失落的另一半靈魂。我曾經相信,我們可以成為彼此的靈魂傾聽者,你深達我內心,那是世間難得的奇遇。你仿佛我在茫茫人海間自己找到的一粒珍珠,是別人未曾發現的,而唯有我的眼裡才看得見那美好的光華。你的搖擺猶疑,與我的固執堅持,不過都是來自驕傲又自卑的靈魂的掙扎,是這掙扎的一體兩面而已。
然而在掙扎中,我們終於身心俱疲,筋疲力盡。這場分分合合的拉鋸戰持續了三個月,到了6月底,我們在疲累中進入又一次的分手,只是這一次,我不再挽留,不再糾纏,也不再兒女情長中追問你每個字的意思。也是在那時,我決定要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我也面臨著畢業的壓力,將自己投身到學習中,我渡過了平靜而感恩的一個月。一個月後,你又來找我,帶著你的懺悔和一個貴重的禮物。我們又在這平靜曖昧中開始了交往;但我心裡恪守著距離,我不願再拾起過去的關係,對你說,“讓我們從朋友慢慢開始”。你溫柔地適應著我的步調,跟我回教會團契,也接受了我強加給你的疏離。我還記得,一個星期五的晚上,結束了團契我陪你等車,你輕輕拉過我的手,讓我靜靜的靠在你肩上,帶點距離的擁抱,溫柔而深情,昏黃的燈光打在我們身上,拖出濃濃的一片陰影。那是我印象裡我們最後一次甜蜜的親昵。
在這緩慢平靜的修復中,我們的愛情終於迎來了最後的致命一擊。8月下旬,你參加了香港大專聯合舉辦的一次活動,去遙遠的西藏旅行。那時,正值我論文寫作的最後階段,我無法抽身陪你。你帶著思念離開香港,10日之後,等你回來時,卻把對我的思念遺落在了西藏,帶著新的玫瑰色的友誼和感動歸來。事實上,在你旅行期間,我們也保持聯繫,甚至你在八角街還為我買了一顆兩眼天珠,你說,兩眼代表著愛情。這是命運讖言的第二個暗示,仿佛命定般地,和那枚戒指一樣,天珠也遺失在了賓館,你回去尋找,卻再也不見。你回來之後,仍沉浸在巨大的感動裡,興奮地給我看你的照片,那裡有你和許多美麗女孩的合影,你告訴我他們是如何接納並喜悅你,也談起你特別欣賞其中的一個女孩。我為你高興,可也漸漸不安。慢慢地,你越來越多地參加團友的聚會,我在打給你的電話中知道你們一起打球,一起聚會,卻從無意讓我參與。你越來越多地提起美珠的名字,我的心慢慢沉下去,知道或者到了該道別的時候。8月的倒數第二天,我論文答辯結束,也是我和你說分開的日子,我仍不忍心和你切斷最後的關係,逼問你的選擇。如果你不再愛我,我就放開你。那天,我去你宿舍,哭著讓你選擇,你不語,我知道你在掙扎,你試圖擁抱我,親吻我,你試圖在身體的溫暖裡找到肯定;而我只是哭,如槁木死灰般;你尷尬痛苦地坐在床尾,看著在床頭痛哭的我,不知所措。在你離開以後,我所有的悲傷和追悔中,常常會想起那時的情景,我只後悔沒能給你更多的屬於世界的溫暖;或許,對你的脆弱而言,擁抱間肌膚相親的溫暖就是最簡單有效的解藥。
沒有等到你的答案,帶著未知的痛苦,我獨自去旅行,去北京,也回四川。在北京,我去了爺爺奶奶的家,才知道爺爺已經離去的消息。奶奶平靜地告訴我這件事,他們在神看顧下的相濡以沫的愛情早已經超越了死亡,不過等候著下一次相會而已。在師大門口的一個天橋上,我遇到了一個賣天珠的藏族女子;或許就是在同一個天橋上,你在兩年多前,第一次拉我的手,我滿臉通紅;而如今,我為自己買下一顆兩眼天珠,為著紀念一段生死未卜的愛情。我也痛恨過你,不是為了你愛上別人,而是為了你的軟弱和背棄。我並不懼怕分離,早在初中讀三毛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愛情無法勉強的道理。但我身上和你一樣的驕傲自卑決不允許自己成爲你感情天平上可有可無的砝碼,在旅行期間,我仍打電話追問你的決定。你的判決下在10月2日,那是一個輕浮的決定。那天晚上我打給你,你正在參加團友們在KTV的一次聚會,等聚會結束我再打給你時,你說我們分手吧。你不無得意地向我炫耀其他女孩對你的關心,在虛榮與輕浮閒做出了這個決定;彼時我正在九寨溝一個陌生而殘破的小賣部裏,向千里之外的你求取決定。電話中的你同樣讓我陌生,就像你曾經擔心的那樣“我們不怕嗎?在某個瞬間,看見對方眼裏如此空洞的彼此。” 那時,你讓我空洞而絕望,或許也讓我準備自己,再次孤身上路。
和曾經的你一樣,我把自己隱藏在天父的恩典裏舔舐失戀的傷口,爲此留下許多的懇切禱告;也是在對上主的仰望中,我仍保留了一份模糊的盼望。如果說在過往的分分合合中,在對天父的傾訴中,我仍勉強維持著自己的尊嚴;那麽你這一次的背棄終於刺傷我驕傲自卑又尖銳的靈魂。在屬人的血氣和衝動裏,我做過許多的荒唐事。我沖進你的博客,刪掉了所有與我有關的東西;也曾歇斯底里地把憤怒和指責拋給你。回到香港以後,我把所有帶著你印記的東西都退還給了你,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你,11月16日,你拿走了裝滿你我回憶的行李箱,留給我的最後印象是一個悲喜莫辨的笑容:你讓我好好學習。送你走後,我坐在大學站外,吹著風,流著淚,模糊地盼望你仍會像以前一樣,跑回來,用力抱著我。然而,你並沒有,坐到黃昏散盡,我回去後在博客裏記下:“這就是我們的結局,愛,或是恨,太過涇渭分明的東西,除了無奈,還是無奈。”
我做的最後一件瘋狂事是在2006年元旦,不顧你的阻攔,我把日記寄給了你,那裏有我為你而寫放在神面前的無法訴之於口的所有情緒。而你無動於衷,繼續著新奇而充滿希望的新生活。儅我試圖將我們的感情重新建基於上主的恩典裏時,你早已定意在現實世界裏找尋救贖的新希望。你把自己博客的簽名檔從 “Waiting for Godot” 改成了 “Staying on the surface”。是啊,與我身後沉重的歷史,破碎的情感,以及有意無意閒卷挾著上帝而來的指責相比,你的新生活裏是玫瑰色的友誼,無辜而坦然的快樂,是你被徹底接納而享受的放鬆。那時,你對基督徒僞善的評價裏,何嘗不包含著對我的諷刺。我享受過你極致溫柔的眷戀;可是也同樣承受過你冷漠決絕的痛楚。你曾經那樣地愛我,可也只是曾經。你曾打開過靈魂深處的小木屋,歡喜地讓我進去:“你是失落的我的偶像,我的上帝!瞧,我愛你是多麽的盲目!雖然並不是每時每刻,但只要你願意喚醒我的時候,我將馬上向你跑去。” 可如今,我傷痕累累,跌坐在你小木屋的門外哭泣,你卻背過面去,不再顧惜。我曾經是那麽愛你,把自己低進了塵埃裏,卻並沒有開出花來。但那也只是曾經。值此以後,我不再去打擾你,3月份通過教會的姐妹,我拿囘了自己的日記,刪掉了你的MSN,從此往前奔去,不再回頭。我們終於把彼此遺失在時間裏。
離開你以後,我並非傷心慾絕。事實上,那幾個月看上去是我在香港最活色生香的日子,我努力讓自己不要太狼狽:更積極地投入到教會,更自由地去旅行,甚至也享受他人的關注。我把傷痛埋在心裏,不去攪動它,甚至很少提起。我的快樂也是真實的。離開我的日子,你也是快樂的。在你走後,我去翻看你那段時間的博客,你並不隱藏自己的快樂;這也是我喜歡的你,自由而忠於自己,有時也不無殘酷。我不得不承認,那時候的你是極富生命力的,現實生活突然像敞開的新世界,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讓你流連其間;你輕靈地跳躍在各種新的愛好裡:攝影、旅行、數學、經濟、政治哲學、羅爾斯,還有友誼。你留下許多俏皮而靈動的文字,是很能唬住人的。你原本就有著極為深刻的洞察力,和很有點天才的文字能力。我有時也問自己,如果可以選擇,最後步入絕境的你,和那個甘願留在生活表面充滿生命力的你,我更願意哪一個是你?在悲傷哀哭的夜裡,我無法回答。或許,唯有不悲不喜流淌著的時間,才能沉澱出最後的答案。只是,香港那段快樂的生活似乎沒有最終浸入你生命的悲傷底色;在你所珍視的友誼裡,文化間的隔膜讓你只能停留在funny DVD的角色;於你而言,也足夠甘之如飴。在你離開以後,我從臉書上找到美珠,問起你們後來的故事。她說你們只是朋友,你曾跟她去過幾次旺角的教會,後來便不再去了。直到最後,你都沒有告訴我分手的原因,讓它成為我生命裏永遠的一個秘密。或許,你只不過是遵循了心靈的軌跡,選擇了遺忘的幸福。
在之後的好幾年,我們完全斷絕了聯繫。你只是偶然地出現在我的記憶,攪動起情緒,或是巴士轉角的某一個瞬間,某部電影,某段模糊的夢裡,也是淡淡的。但對我的信仰而言,這段感情終究造成了緩慢卻沉重的打擊。我說過,我的信仰裡不自覺地已融進了對你的愛情,在學習“什麼是愛”的功課裡,我慘敗收場;在痛苦、憤怒、歇斯底里之後,我似乎接納了這個永不可純粹的自己。之後,“神存在的確據”終於成為我無法迴避的理性難題,我最終也沒有勝過。在美國的日子,把自己投擲在自然世界的秩序之中,我彷彿安頓了自己的身心。哥哥,和你一樣,我也未曾虔信——別道我孤燈默守,只一瞥就揭示了內心的沉迷。知道永恆,卻隨時準備讓自己迷失在溫柔之鄉——你曾說過,這篇小札記可以當作你留給世界最後的遺言。當我最近重新去翻起舊文,才發現2008年我的掙紮裏,也有著與你相似的哀嘆和遺憾,我們終究是同一類的人,也終究錯失了彼此。縱使我忘記了你,你也總在我心裡的某個角落裡,因為部分的我也就是部分的你。去年看Inside Out,當所有的核心記憶球在Sadness的觸碰下蒙上一層淡藍色時,我便想起了你,你就是滲入我生命的那一抹憂鬱,伴隨著我的成長,讓所有的幸福快樂都抹不掉一絲酸楚的哀傷。還有一次與你有關的回憶,是2014年和同事去看話劇《教授》,我無法自抑地失態哭泣,在微博裡記下:“這是一場完全意外的邂逅,卻毫無預警地擊中我的淚腺。許多遠去的人事突然撲面而來,在追求個人價值與社會公義的撕裂中,許多人無奈地奮爭。必然的失敗,然後是孤獨中鬱鬱不平地憤懣和自我放逐。然而,斯人已遠去,最好地祝福是勇敢的生活。只希望初心不改,在面目模糊地世界裡看清自己的模樣。 ” 那時,你鬱鬱獨行在華師大的校園,艱難地維繫著自然、理性與信仰閒搖搖欲墜的平衡。
2010年之後,我們恢復了斷斷續續的聯繫。我知道你去了華東師大,甚至也知道你去約會,相親,妳也愛上了其他的女孩子。你把她們的照片發給我看。我從沒有問起過你與她們的細節,我的驕傲不會允許,再説我也不那麽喜歡略帶輕浮的你。我只是半開玩笑地問起過,可有後悔與我分手;印象裏,你也不過含糊其辭,大略覺得這是無可奈何、自然而然地決定。因爲這樣,縱然有不甘心,我總相信你早已放下我們的過去,更不願太多過問你的感情生活;我們後來的交流也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我從沒有真正相信並體會過你的孤獨,早知如此,或許我應該更積極些。那時候,你給我的印象仍是開朗並努力進入生活的,夏夏也這樣覺得。你們2011年應該見過一面,那時你一無所有,可還有單純的快樂和充滿希望的日子。
我們有多一點的聯係是從2013年開始,因爲工作的原因,我需要涉獵一些哲學的書籍。去豆瓣,常常可以看到你的讀書筆記,我感傷又不無安慰地想你終於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因此關注了你的微博。到8月中的某一天,你突然聯係我,讓我幫你捐1萬塊錢給騰。我問起你和姐姐的生活,你說很拮据,過得不好,但希望努力擺脫身份帶給自己的平庸、窮困,去追求一些東西。我很高興你這樣努力,十年前那個執著堅持的你好像又慢慢活起來。於是,我偷偷代你捐了5000塊錢,把剩下的5000塊退給了你。我拜託騰不要告訴你,可他後來還是跟你說了。那時候,我剛開始工作,很不適應。中港關係的惡化加劇了這種不適感,為此我也向你諮詢過意見。大約,你感覺到我對你的信任和善意,過去糾纏間的所有不快、埋怨都終於消散在時間裡,你也願意與我保持更多的聯繫。2013年9月,你第一次在微博提到被招待所驅逐的事,也提到了離去;因為擔心,我和你有過簡短的交談。3年後,同樣的這件小事,還是成了你生命尾聲一個不愉快的註腳。到了年尾,你計劃去長州的思維靜院退修,後來這裡成為你喜愛和流連的地方;你問起我在香港住宿的事情,我那時還調侃過你,開玩笑地說你可以去見美珠了。臨行的前一天夜裡,你突然說要到香港請我吃飯,躊躇間我拒絕了你,既是過於突然,我沒有準備好自己;也是身份的尷尬,我已為人婦;還有一個原因,我沒有告訴你。網上看見過你的照片,不再是我熟悉的哥哥,我害怕面對你。我寧願保留你在我記憶中的模樣,有點模糊了,卻是輕柔溫順的孩子模樣。你眼裡慢慢有了我不熟悉的驚懼,與日俱增,最後兩三年看你在網上的照片,我常常不敢直視。也是因為這樣,我心裡其實抗拒去參加你的追思會,不想去見你最後一面,只想保留著你在我記憶裡的模樣。可是,2月19號的那個晚上,當你離開的消息終於傳來時,那時的拒絕突然像把刀一樣插進我心臟,我痛哭失聲,就這樣,我們永遠地錯過了重逢的機會。後來,我一遍一遍地去看你的照片,重新把你的模樣印在我腦子裡。2015年2月,你還來過一次香港,到過中大,3月份才告訴我。我問你為什麼不與我聯繫,你說:好久不見~怕見了! 現在想來,你是故意的,可遲鈍的我卻傻呼呼地認同你的想法,那也確實是我的念頭。其實,如果你來找我,我一定會見你的。2016年你再來的時候,就不再同我說了。我不敢、也不願去揣測你的心思;在我們分手時,我曾給你寫過一封長信,說我期待著重逢,就像你第一次去北京車站接我時一樣,應該也可以是美好的吧。可我們,終究沒有再見。
我們在世界的兩端繼續著自己的日子,一天又一天??你在微博裡時不時流露出憂鬱,看到時,我也會簡單地安慰你。但我已有自己的生活,並不會密切關注你。像你的很多朋友說的那樣,你常常提起死亡與你的孤寂,我們眼見著你掙紮,可都沒有意識到它會那麼突然地來臨。即便有人安慰你,你也常常狡詰而輕描淡寫地唬弄過去。我當然知道你不是傳統意義下的良人,但你有自己古怪獨特的魅力;我並不真相信你的感情生活是一片沉寂,也從沒有認真去體察過你的孤獨;我也覺得自己不再合適去追問你,提起也不過是淡淡的帶過。我想,也是真的放下了我們的過去。我甚至想,現在這樣很好,過你想要的自由的日子,孤單時談談戀愛,你身上的孩子氣總讓你更適合青春亮麗的年輕女子,卻無需承擔婚姻的責任。只是,你對真理、對知識的追求太過耀眼,讓我們都忽略了你更重要的缺失與渴望,就算知道了,也無法接近,你同自我的鬥爭從沒有停止。其實,我大約也知道你有點抑鬱,也想過你最終會自己選擇離開的方式,只是我以為那會是很久之後的將來,你也是這樣告訴我。可為什麼,它就嘎然而止! 時間就這樣無知無識地滑進2016年2月,命運的讖言給過我第三個暗示,以一種殘忍的方式。19日是一個星期五,正是我一個星期裡忙碌的時候。上完課,一個學生突然來找我聊天。我並不很喜歡他,聰明、驕傲而張揚,卻對人缺乏基本的尊重。他說自己是基督徒,想問問我對自殺的看法。那段時間,香港連續有學生自殺,一個星期以前,在我上課的那棟樓上,就跳下來一個女孩子。我們聊了很久,其實很膚淺,而那時你正在生死的邊緣掙紮。之後,馬不停蹄地去聽了一個讀書會,結束後已是8點,我在快到家的路上看見了你的微博,和你最後的話,已是你發出最後一條微博的10幾分鐘之後。一切都太遲了。何老師後來告訴我,你選擇了一種很決絕的方式,只需要3分鐘,一切都結束了。你說,“哦,正義?我接受?”
我們在此世的故事就停在了這裡,之後便只剩下我的故事。你決絕地驟然離去像擊入我記憶之海的一粒石子,逼我重新面對你,去審視你生命留下的奧秘。你剛離開的那幾日,網上很是喧囂了一陣子,而我只想知道你與我分開的十幾年裡,你生活的點點滴滴。我重新閱讀我們的書信,別人為你寫下的文字,你留下的一切痕跡,那個乾淨單純輕飄飄的你再次讓我心疼不已。哥哥,他們為你的死亡附加了太多形而上的含義;我也同意,你的死亡是形而上的,是意義的全面崩潰,可它的坍塌正是源自形而下的缺失,正如你最後發出“渴望愛”的呼籲一般。我當然也知道,一個不那麼友好的大環境會侵蝕你追求自由和正義的生命活力;但你一早洞悉了生命的廣闊維度,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與美好幸福的個人人生之間有著遙遠的可被填充的生命厚度。你所追求的,是有尊嚴而被安頓的靈魂救贖,是在艱難困頓的個人命運裡仍然可以彰顯出生命的靈光。縱然沒有最終勝過,你依然掙扎奮爭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也是我最愛的你,是你留給世界最大的意義:因為政治或會如癲癇般偶然發作,而對生命品質的追求卻是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的決擇。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不斷回憶起你,我常常想起張國榮(他也是哥哥)在《阿飛正傳》裡說起的那隻不死鳥:生來就沒有腳,一輩子不停地飛翔,但也有停下來的一天,因為停下來,就意味著不再飛翔。你也彷彿是一隻不死鳥,我或是你飛過的某個枝椏,曾想棲息休憩,但終究無法全然委身。後來有人評價你:“所唯一匱乏的是意志”,儘管尖銳,卻也是事實。只是我們都願原諒你的這一匱乏,因為深知背後是沉重的命運:它既先天地缺失在你細膩敏感的天性中,又未在你艱難悽苦的成長過程裡得到滋養。你的可貴之處正如崇明所說,過往的艱難並未將你壓進汲汲營營的功利市儈;而是讓你對正義、自由、良善、救贖生成了更矚目的渴求。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昇華裡,你把自己的生命鍛造成一縷輕煙,再無法回到健全的現實世界裡。如你所願,你用閱讀、思考、知識,用自由、正義、良善,為自己的靈魂搭建了一個靈光閃閃,華美而尊嚴的居所,甚至成為他人眼裏審美的存在。只是,你的靈魂呢?世界已成為廢墟,世界是你的世界,而你是亡靈。
那麼,於我而言,你的意義呢?我想,你從不知道。我很幸運能在此世與你相遇,被你愛過,並愛過你。和你一樣,我曾經以為自己會孤寂一生,但是在與你的愛情裡,縱然失敗,我仍然學會了愛與被愛。如果說我曾經盼望過一個靈魂伴侶的話,那只能是你。這並非是說我無法再愛,只是每一段用心過的愛情都有其無法代替的獨特之處。清明前,我偷偷去過上海一次,去看你,也再次見到姐姐。我原以為她總會怪我的,因為我弄丟了你;可是她和你一樣的溫柔善良,只是緊緊抱著我哭泣,讓我好好生活。我也拿回了當年送給你的小相冊和我們的照片,裡面還有那時拍的大頭貼,我不知道原來你一直保留著。表姐說,你心裡或許一直有我;我不知道,我只記得以前叮嚀過你,“哥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愛我了,一定要告訴我,我會給你自由”。我只知道自由對你的重要性,我希望你幸福,從來都是。我去了你的辦公室,見到了你的學生,他和你一樣的帶著孩子氣;那天晚上,我其實特別想抱抱他,因為他身上有你的氣息,不過終究也沒有。第二天是清明之前的一日,我去墓園看你。姐姐很愛你,用你剩下的幾乎所有錢為你挑了一個如此美好的安眠之處,要是靠海就好了。那天,只有我一個人,很好,我只帶著我的行李箱。原本是想帶一束白色滿天星去的,可是太倉促,墓園裡賣的花太鮮豔,我不喜歡,就沒有買,我想你也不會介意。我本來只是想在你墓前坐一會,可是我看到你,那是我為你拍的照片,在上環的海邊,那時候,你其實不那麼開心。我看見你的時候,心裡的悲傷席捲而來,無法抑制,我只能蹲坐在你的墓前痛哭流涕。我翻開我們的小相冊,全是年輕時的傻樣子;也翻開從你辦公室拿走的《理想國》,很破舊了,被你補好。後面寫著 “香港中文大學”,“TOEFL, GRE”,我知道那是你準備申請香港時留下的筆記。很好,陳綺貞也唱:“眼淚灌溉,不枉愛過”。你或許也會喜歡這樣的紀念方式。天在下著小雨。
哥哥,過去的一個多月裡,我縱容自己的情緒,任性地把自己埋進記憶,與你慢慢作別。在我們那漫長的分手過程裡,我就抄下過一段文字,現在我還把它抄下來給你。那是楊降與錢鍾書告別時,寫在《我們仨》裡的一段話:
“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會的時候,他還問我做夢不做。我這時明白了。我曾經做過一個小夢,怪他一聲不響的忽然走了。他現在故意慢慢兒走,讓我一程一程送,盡量多聚聚,把一個小夢拉成一個萬里長夢。這我願意,送一程,說一聲再見,又能見到一面。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遠,愈怕從此不見。或許,這也是他們的心意吧,讓我慢慢地,將離別拉成一個‘萬里’長夢。但是,我只變成了一片黃葉,風一吹,就從亂石間飄落下去。我好勞累地爬上山頭,卻給風一下子掃落到古驛道上。一路上拍打著驛道往回掃去,我撫摸著一步步走過的驛道,一路上都是離情。”
哥哥,我也願意把我們的離別拉成一個“萬里”長夢,只是,我們之間隔著超過十年的時空距離,你不肯入我夢裡。我無數次地邀請你,連不相干的人都能夠夢見你,可我的夢裡沒有你,我只能在半夢半醒的記憶碎片中,去捕捉關於你的記憶。把我們的故事寫下來,是想在世間為你存留一份證詞:縱然孤寂,你也並非枉然到世上一次,你曾誠摯地愛過,也曾為人所摯愛。縱然有過犯、錯失,我只希望,我們的愛情不會玷污你已被上主洗淨的靈魂。在他的希望之門內,你仍可以坦然地憶起這段往事,此刻,你並非生活的渣滓,而是神的珍寶。
當寫好這段文字,哥哥,我會再一次把你掩埋進記憶裡。或許,在未來某個不知名的時空,就像小馬德萊娜蛋糕之於普魯斯特,它突然刺入記憶,揚起時光的塵埃,模糊的微光裡,有你,是我熟悉的輕靈而孱弱的笑容。這樣,很好,你說呢?
再見,哥哥。
2016年2月20日-2016年4月7日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