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陈辉
被访者:文洁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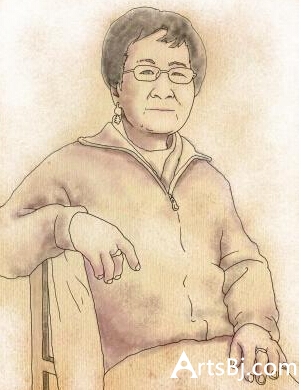
文洁若:著名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是中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一百岁才会写自传,还12年呢,着什么急?”与5年前相比,文洁若先生腿脚利落多了,每天依然在看书、翻译和写作。
刚看完几本书,准备捐出去,拉开抽屉,小本上有铅笔登记的捐书目录,已经2100多本了。小本下面压着傅光明写的《胡适图传》,文老说:“特别喜欢的就不捐了,比如这本,文笔好。”
突然聊起cut这个词的翻译,文老说,不全是“砍”的意思,还可以当“漠视”讲。她迅捷地从矮柜底层拎出超大号的字典,果然,在第17个义项中印证了先生的说法。
拿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出版的《丁玲传》,文老说:我要看,看完还要写书评。“文革”结束后,萧乾(文老的先生)最早在媒体上编发了丁玲的文章,人们这才知道:丁玲还活着。
文老喜欢丁玲的豪放、大气,还有她的小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文老说:不理解为什么今天年轻人这么喜欢张爱玲,她觉得丁玲好得多。
聊得时间长了,文老有些疲惫,几次要打哈欠,都被她忍了回去。面对外人时,文老永远戴着耳坠和项链,怕听不到别人来访,在上锁的防盗门后,她一直开着房门,并刻意坐在门口的写字台边。
但,你不打扰这个世界,不等于这个世界不来打扰你。
几个月前,文老又差点儿上了当,一个冒充燃气公司的年轻人上门检测燃气灶,称泄漏严重,随时可能爆炸,需立刻掏几千元换灶。好在,文老把钱都放在亲戚那里,她已判断不出世道人心究竟如何了,所以只在身边留几百元。
“我在日本住了一年,从没遇到这种事。”文老说,“可我还是喜欢住在中国。”儿女都在国外,为了这份“喜欢”,文老忍受着寂寞,自己洗衣服,自己买菜做饭。
1949年,英国人何伦几次登门力劝萧乾接受剑桥大学的聘书,何伦是捷克人,后加入英籍,他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事,以为一定能打动萧乾,但萧乾还是决定回大陆。在那一代人的心底,有一份特别脆弱、特别执拗的地方,正如问文老丁玲的小说究竟好在哪,她会说:丁玲爱国。
三岛由纪夫不如董竹君
记者:您译的《奔马》、《晓寺》刚在重庆出版社出版,在这套“丰饶之海”四部曲中,您译的前、后两部早就出版了,为何中间两部拖这么久?
文洁若:因为不喜欢,所以一直没译。“丰饶之海”四部曲是三岛由纪夫的绝笔,大家都认为是他的顶峰之作,但第二部、第三部里写的净是些杀人、自杀的东西,太残忍,三岛这个人总写“毁灭的美”,想在破坏中找到美,这多可怕啊!这样的书有没有翻译的价值,我一直在犹豫,毕竟这个作家很有才华,文笔特别好,书中很多很精辟的句子,写人也是活灵活现的,像那么回事。
虽然译了这套书,但我觉得价值还不如我刚看完的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我写了一个书评,董竹君这人不简单,家境贫寒,父亲把她送到妓院,14岁逃跑嫁给了同盟会员夏之时,到了日本,此前她只有6年私塾的基础,在日本受了4年教育,便达到过去大专的水平,回国后接触共产党,办锦江川菜馆(锦江饭店前身)掩护革命活动,解放后将它捐给国家,她活了97岁,直到1997年去世。
小说应该反映积极向上的东西,董竹君这本书有教育意义,三岛由纪夫的没有。
不喜欢一些年轻作家
记者:三岛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写作风格独特,他的作品也许中国文学创作有一定借鉴价值?
文洁若:中国也有很好的作家,只是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近年来刚刚开始重视。比如巴金,他的《寒夜》法国人就很喜欢,如果他能再写出这样几本书,他也能得诺贝尔奖,可他后来被迫去写“应命文学”,领导喜欢什么他就得写什么,这怎么成?其实咱们不也还有个莫言吗,他的写法比较特殊。
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当下的一些年轻作家,中外文都没功底,看不到大时代,专写小时代。当然,今天年轻人也有很好的,办奥运会时,石原慎太郎来北京,他是个极右翼的作家,可他都说被中国年轻的志愿者感动。总之,他们还年轻,将来有机会。
记者:很多人觉得,三岛由纪夫比川端康成更有资格获得诺奖。
文洁若:但川端康成家有钱,请诺奖评委到他的故乡大阪去玩,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川端康成笔下的那些美景确实存在,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写。
不明白日本作家为何爱自杀
记者:您翻译这么多日本文学作品,您比较喜欢谁?
文洁若:我译过松本清张的《黑雾》,他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我刚译完他《小仓日记》等四个短篇,是纯文学,水平很高,可见他写作路子很广。此外我翻译过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还有我翻译的一个日本女工叫山田歌子,她写了《活下去》,讲的是个人经历,都比较喜欢。
但我不太喜欢村上春树,比如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人请别人把自己的舌头割开,装了一个小钻石,多难受啊,这个好看吗?我觉得丑死了,我对很多日本小说都不太喜欢。
日本小说中杀人、自杀的东西特别多,作家自杀的也很多,比如刚才提到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中国人精神比较健康,很少会想到自杀吧?
记者:中国作家也有自杀的啊,比如三毛。
文洁若:我还见过三毛呢。那是在新加坡,此前不知道这个人,过去后才发现她粉丝这么多,大家都围着她转,她挺怪的,吃饭时什么都不吃,只是抽烟和喝酒。这倒像写《人啊,人》的作家戴厚英,她年轻时是体育健将,忽然开始吃素,别人请我们吃饭,做了好多菜,可她就吃一点米饭,喝一点汤,后来碰到暴徒,人家都没用刀,就把她打死了,放在过去,可能她一抡就把对方抡死了。
关键时刻人要克制
记者:在“文革”中,萧乾先生好像也曾自杀过?
文洁若:那是1966年,我和造反派吵了架,被禁止回家,三姐带着两个孩子被吓得待在自己屋里不敢出来,萧乾写好遗书,在小厨房门口大缸里放满水,准备拿着通了电的台灯扎进去,为减少痛苦,他喝了半斤白酒,吃了安眠药,结果没走到水缸便醉倒在地。自抄家后,我家就不许关门,人们从街道上看见他躺在地上,觉得不正常,这才把他救了,正好是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一天。
还好了,萧乾至少没挨过打。
记者:您为何与造反派吵架?
文洁若:也不算吵架,而是挖苦了几句,抄家前,我们买了10张毛主席像和1张刘少奇像,贴在名人字画上,那时我们也不知道刘少奇被打倒了,心想这下“红卫兵”该不敢乱来了吧,没想到被说成在毛主席像后衬“黑画”,是诅咒毛主席,名人字画被统统没收。抄家这拨人走了,又来了一拨,其中一人把书包直接挂在毛主席像上,我讽刺说:你们不让在主席像后面衬东西,可你们倒好,这么脏的书包直接挂主席脑袋上了,这算什么?
这下“红卫兵”急了,忙找来学校的“红卫兵”,如果是工厂的“红卫兵”,也就无所谓了,我进了“牛棚”,所谓“进牛棚”,就是不许回家。
所以说人得克制,萧军后来和我说,他会武术,撂倒几个不在话下,可家属也就倒了霉了。萧军平时任性,但在关键时刻忍住了。
学习语言应趁早
记者:您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为何后来翻译的日本作品更多?
文洁若:我7岁起随父亲在日本生活了2年,刚开始是请家庭教师教我日语,每天也就2小时,很快我就掌握了,我后来学了10年英语,可英语水平还是没日语好,所以说语言一定要从小学起。
翻译没什么诀窍,就是勤学苦练,多读书,此外要提高写作水平。我上小学前,父亲让大姐教我,可大姐懒得管,让我自己背唐诗,刚上学时,老师让写作文,我当然不会,甚至不知道作文是什么意思,就把平时背的唐诗抄了上去,结果老师给了个大红叉。
在辅仁学校上中学时,陈垣校长有个规矩,必须用毛笔写作文,这比用钢笔困难多了,因为错了不能改,必须先想清楚再写,这对我写作有很大帮助。有一次写作文,老师批了句“努力吧,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拿了两张大学毕业文凭
记者:您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为何晚年才拿到文凭?
文洁若:我高考时正赶上抗战胜利,清华大学8年没招生,竞争特别激烈,我们班就两个人考上了,我是其中之一,在清华校园中我还见过林徽因老师2次,她英语特别好。我在清华上了三年,第四年去了贵州大学,因为我父亲此时在贵州老家,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照顾。我祖父当过20年县长,在那里置了100多间房、300多亩地,解放后地分了,房子只留了两三间,其他都算“还剥削债”,人没被打死就算很不错了。萧乾也到农村采访过,他说他最受不了是逼儿子打父亲,不过他没在报道中写这些,他的报道后来得到毛主席的夸奖。
到晚年时,我和萧乾正在翻译《尤利西斯》,闲聊时提起我退休后想回清华补上最后一年,没想到人家回去一查,发现我当年的学分已经够了。因为我大二时就过了大三的课,大三时过了大四的课,只差一篇论文。我就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论文,清华大学决定补给我毕业文凭。这样我有了两张本科文凭,一张是贵州大学的,一张是清华大学的。
当了一辈子顺民
记者:您和萧乾先生曾遭遇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萧乾先生是否对当年回来的选择感到过后悔?
文洁若:没有。其实在当年《大公报》记者中,他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很多人后来再也写不出东西了。我觉得我能挺过“文革”,因为我这辈子经过的一些事比这还严重。比如我父亲1936年从日本回来后就失业了,全家只能靠房租维持,可那时房客比我们还穷,经常拿不出钱来。“文革”时虽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但两人加起来还有140元,总还有点收入。后来,我们从自己家中被轰了出去,全家挤在一间小房子中,萧乾取名叫“难民营”,那时也有人挺高兴的,说:没有“文革”,我们怎能住上大北房?
我当了一辈子顺民,那时别人问我什么,我从来不说。可不是么,我有右派想法你拿我没办法,可一说出去我就成右派了,幸亏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机器能扫描出人的真实想法,爱迪生也没发明出来。过去右派是按比例的,150人中出8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冯雪峰、聂绀弩等都被划进去了,名额满了,所以没拿我凑数。
我母亲没工作,三姐有病,还有3个孩子,萧乾又被划成右派,我再出事,这个家不就完了?民主不民主的我也不敢想了,只要别来害我们就行了。
吃点亏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
记者:您状态比5年前还好,有什么养生之道吗?
文洁若:5年前那是刚从医院出来,因为在家摔了一跤,那时我常凌晨两三点才睡,后来觉得太不划算了,住院花钱不说,护工也欺负我,朋友送了一斤熟牛肉,才给我3片,其他都拿给她老乡了,我还不好说出来,护工说还有病人给护工买手机的呢,我想我要说出来,不成笑话了?请护工一天150元,这也不便宜啊。
从那以后我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中午还要补2个小时,所以这几年身体好多了。
我这人想得比较开,吃亏就吃亏了,别再把自己给搭进去。有一次萧乾去买菜,听说有个老太太也买菜,顺手把装了6000元的包放在别人三轮车上,等三轮车走了好久她才想起来,急得用脑袋撞墙。萧乾说他不在场,不然真想帮帮她。那是上世纪80年代,6000元确实挺多,但生命不比这个值钱?我觉得她有点想不开。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