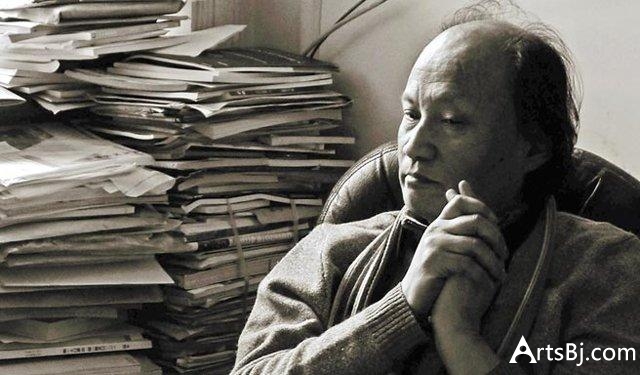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金宇澄
当编辑容易挑剔别人的文字,写作则是要全力来鼓励自己。要么做作家,要么做编辑。
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城市题材不多。金宇澄的《繁花》则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这部在2015年几无悬念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屡次加印。直到今天,《繁花》的话题依然被屡屡提及,金宇澄缓慢细致的城市叙述在碎片化阅读的多媒体时代征服读者,自有他的原因。
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之后,金宇澄很快推出散文精选——《洗牌年代》,据称是《繁花》的素材笔记,某些来来往往的人与场景——对熟悉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既是《繁花》的背影,也是这部散文集流连忘返的内容。
或者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繁花》热销的一些答案。
记者:初版于2006年的《洗牌年代》,在《繁花》获奖后重版,据说在上海书展首发时“排队等待签名的人绕着书展中央大厅的楼梯一圈又一圈,丝毫不会计较这其实是一本将近十年无人问津的旧着。”(张定浩语)《洗牌年代》此前是真的“无人问津”吗?此次重版有无修改?您是否认同张定浩所说,“新的作品会改变过去作品的命运,麻将牌重新洗洗,又是一副新牌”?
金宇澄:他说的不完全对,这本随笔集《洗牌年代》,初版印6000册,几年里也卖完了,网上很少有这个版本。当时这套文汇出版社“中年客”丛书另三本的作者是陈村、沈宏非、程小莹。原文我是在《海上文坛》的专栏,一月一篇,配西方摄影照片,比如《二十五响连发》讲的是中国土铳等等枪事,配了普鲁士军官或苏联女战士持枪照,《苏州河》配的就是塞纳河或意大利小巷搬运旧船的照片,初版的单行本也是这样做的,本国内容对比西洋照片。它在影响力上当然无法跟《繁花》比,我的朋友(《洗》的责编)朱耀华哪会放过我?一定要重版,但总得给读者新内容,因此我去掉全部照片,自己改画27幅插图,结尾加有两则“手工细节”对话,再次出版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是《繁花》的“素材”本,《繁花》有一些章节我当时写得飞快,事后想起是随笔上已经提到的。张屏瑾最近也说,《洗》比《繁花》有趣。也许是因为,它完全是用普通话写的原因吧。
记者:您的绘画颇具专业水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您认为在作品中增加自己的绘画,是必须的吗?
金宇澄:没学过画,早前我和朋友通信,比如解释具体的细节方位,喜欢画图说明,图画有时更明白。《繁花》20幅图、新版《洗牌年代》27幅图,不是通常的文字装饰,而是说明。人物在哪几条上海马路上活动?具体建筑的变迁、已经被遗忘的用具,包括怎么打制一把镰刀的步骤,觉得有趣的就可以配图。我常常被问为什么画图?文字有时真不如图,比如上海老弄堂房子内部是如何的?就是写两万字、三万字也不清楚,可以画示意图来补充。
记者:《繁花》在网上发表时曾暂名《独上阁楼》,您是以游戏而喜悦的心态写的,是非书斋、非功利的一种状态。能谈谈您在网络上写作的体会吗?
金宇澄:2011年5月,有朋友在“弄堂网”写真人真事,我看后觉得,写普通老百姓会更有趣,就开了一个闲聊的帖子,非功利,用“独上阁楼”的网名,很是新鲜。没想到以后每天就被读者催了,要我多写。陈丹青讲一个上海小孩翻斤斗,假如大家围观鼓掌,他就能不知疲倦地翻个不停,可以说是这样的环境成就了《繁花》。还有就是,网络特别的自由自在,就好像你完全脱离了圈子和自己,有陌生名字,同很多陌生人来往,触角特别灵敏,6个月里,这闲聊成了长篇初稿。
连载文学的传统,至少在圈内是被遗忘的,我个人觉得,写作不一定就是私密、高深的,可以很平凡,可以直接面对读者,可以经受精神、环境双面的压力,这里边有“书斋写作”难以感受的责任感,非常清醒,也经常让人陶醉。说老实话,我们所谓的小说,就是给读者看的,我们的作者也都希望看到更多的读后感,但常规意义上,你写一个长篇比如两年,你只会看到一个读后感,也就是编辑谈论的读稿感受。但是你网上每天写每一节,都会得到反馈。最近评论家吴亮也在我熟悉的“弄堂网”洋洋洒洒大写小说,半年写了二十多万字了,有时我上去看。他曾经在80年代也写过小说,之后已憋了几十年,等于尘封的古董级茶砖,沏出来特别浓。有次看了他写的一段,心里忽然有跳起来的感觉,我是想到了自己曾在网络上写作的感受,非常自由自得。那是众目睽睽之下,高度警觉中的一种超常的挥洒,这个过程,现在想想非常奢侈,很怀念那个时期。
记者:能否谈谈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有哪些人或事?
金宇澄:16岁去东北,一直和上海一个朋友通信,他比我大几岁,说我能写小说,也是他信里的话。记得1970年他在读《小逻辑》,读叔本华,虽然这都是我不喜欢的书。在东北农场也有这类朋友,喜欢和他们交往。回上海探亲,也是找这类朋友。
这种寻找,是记忆里的瘾。等前些年看到陈丹青的回忆文字,包括遇见了陈建华教授——他给我一本诗集,才知道他是1964-1968年上海的地下诗人,写颓废诗歌。这种时刻,我心里冒出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当年不认识他们?认识他们就好了。应该说,属于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孤独的。
记者:能回顾下80年代中期您的写作状态吗?
金宇澄:在《萌芽》发过几个短篇,得了“上海青年小说奖”和两届《萌芽》奖。之后参加上海青创班,短篇《风中鸟》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同期发在《上海文学》,得了《上海文学》奖,再以后就调《上海文学》当编辑。在1990年前后发的小说,包括《收获》发的那些个中短篇、散文之后,就感觉不能再写了。当编辑容易挑剔别人的文字,写作则是要全力来鼓励自己,那时我经常晚上写一节,早上起来就觉很差,挑剔别人,也挑剔了自己,很分裂,感到很难继续真正的写作了。
记者:正处于写作的上升时期,果断地“觉得不能再写”——为什么会对自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
金宇澄:简单讲就是,要么做作家,要么做编辑,我当时是徘徊的,也没把写作当成重要事,不觉得写作那么重要。刚到编辑部,老主编周介人让我编个稿子,结果被我改成了大花脸,当时都是手写稿,满篇都改成红的了,周老师很吃惊,这稿子确实很差,但他也真没见过能这样改的。那阶段我自己在写,白天挑剔他人晚上鼓励自己——写作得有百分百的自勉,后来就觉得做不到了,做不到“真正的写作”,遇到了“极点”。记得有一次我收到一本《世界文学》,那时都关注西方文学,一打开目录是“越南小说专辑”,本能就扫兴。之后我自问,为什么这样扫兴?也就想到我们的小说在西方读者眼里,就是看这专辑的态度吧,仿佛从那时起,我就解脱了,平静了。总之,那时期我遇到了瓶颈,然后找理由退出,自我退出。
记者:谈到“那时期我遇到了瓶颈”——感觉您面对瓶颈并没有急于改变,还是曾经也试图拿出更好的作品证明自己?瓶颈的突破,是经历多年积淀之后自然而然解决的吗?
金宇澄:当然也有过希望自己“越写越好”的阶段。有一年,我天天待在家里写,吃饭马虎,形容枯槁,邻居有一位老大夫,偶然见我大惊,警告说,我再这样下去,身体肯定出问题。然后就是编辑工作对写作的干扰。那期《世界文学》给我在心理上一个退却的理由,这过程是复杂的,也因人而异,既可以攻城略地,柳暗花明,也可能一直是败走麦城的。记得当年青创班一个朋友,坚持写作到什么程度——家里一大堆一大叠的稿件,那时都是手写,一个都发不出去,后来老婆见他写字,就上来撕碎,因此他只能到邮局写信的座位上写,他这样努力,仍然收效甚微……年青作者往往容易逼迫自己,向自己索要灵感,无视种种局限,良性的获取是水到渠成的,牵涉到条件、方法等等无数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通常所谓的焦虑是,写你难以把控的内容,人不能逼自己写一个陌生的东西。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