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者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在于,作者崔莹费时八年,跋涉万里完成的这部作品《访书记》,我们足不出户,若集中精力的话,一整天便可以读完这本五百三十多页的书。在她的问访与受访者的回答中感受谈话的精彩与感动,若碰巧喜欢写作,那么,这就是一本最全的“创意写作”指南,无论是虚构类的还是非虚构类的。这本书分了类别,汉学、史学、文学、非虚构类、社会学等等,所以可以从喜欢的类别开始读,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作家开始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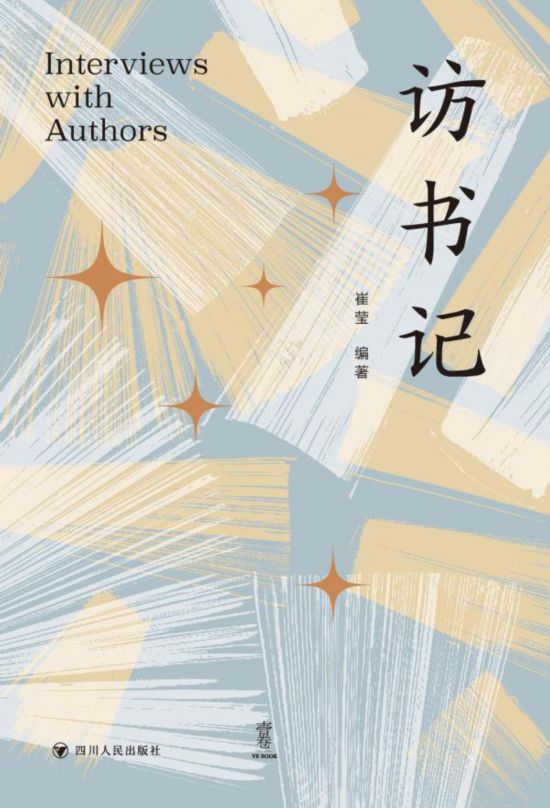
《访书记》
笑与自由
读这本对诸多作家的访谈录,最打动我的一篇是文学类中作者对以色列作家大卫· 格罗斯曼的采访。访谈发生在耶路撒冷格罗斯曼的家中。在对话之前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的介绍中,崔莹提到了一点,说如果不下雨,他每天都是5:45起床,然后与朋友在山里碰头,徒步四公里,看狐狸,羚羊和太阳。回来后,在8点钟准时开始一天十个小时的创作。这本书在后面会告诉我们,社会学家齐格蒙· 鲍曼也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开始写作。我想起在刁克利教授的《诗性的对话:美国当代作家访谈与写作环境分析》(以下简称《诗性的对话》)中,他采访过的美国曾经的桂冠诗人泰德· 库塞(Ted Kooser)也是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从4点半写到7点,然后穿戴整齐去上班。刁教授在那本书里特别提到可能因为库塞大部分诗歌都是写于早晨,所以诗歌读来别有一番清新与灵动。在习得成为作家的其他经验之前,格罗斯曼也好,鲍曼,库塞也好,都告诉了我们勤奋与自律的必要性。

大卫· 格罗斯曼
崔莹提到了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中,用玩笑或幽默的方式去表达或展现类似大屠杀这样的悲剧主题,她问作家这意味着什么,格罗斯曼并没有说要如何如何笑对这样的鸡汤语言,他回答的是,“只有在笑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呼吸……在那一秒钟,你是自由的。”在写《到大地尽头》时,他的小儿子牺牲在了战场上。像以色列的很多同样失去过或将会要失去孩子的家庭与父母一样,他与孩子的内心最惧怕也是最习惯的情绪便是恐惧,对他所言的“野蛮而残暴”的现实世界的恐惧。在试图化解恐惧的窒息与悲伤的沉重时,有什么能比笑,幽默做得更好呢?
格罗斯曼不是唯一一个被作者问到“幽默”主题或现象且回答精彩的作家,英国布克奖获得者美国黑人作家保罗· 比第在其获奖作品《背叛》中也是用了大量幽默,作者问他本人是不是幽默的人,以及那些幽默桥段的灵感。比第在回答这一点时表示说,幽默能让他更轻松地谈论自己的弱点,他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能讨论别人的脆弱。另一位受访者,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谈论他喜欢的杜甫时,也特别提到了杜甫以幽默的方式对自己的弱点进行自嘲的一面,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曾想到的杜甫所具有的一面,让这伟大的诗人更加真实生动。在崔莹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和白人作家相比,黑人作家是否更容易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黑’与‘白’?”时,保罗· 比第在引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即,奴隶对主人的了解要多于主人对奴隶的了解时,说,这并非和种族有关,而是和权力有关。他说出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有权者对无权者的了解很少。”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英国著名喜剧作家伍德豪斯(P.G.Wodehouse)的“万能管家吉夫斯”系列作品中,对主人了若指掌的管家吉夫斯,以及对吉夫斯知之甚少的主人伍斯特。睿智的奴仆,愚蠢的主人,虽然不一定是所有主仆的形象设置,但十九世纪的伍德豪斯用一种让人捧腹的形式揭示了这令人心酸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比第也是在这个传统中,以幽默的方式揭示了这一严肃的主题。《困扰种种》的作者莉迪亚· 戴维斯被问到作品中的幽默元素时,也说,当这个世界令人失望时,她会尝试看到其幽默的一面。克里斯· 威廉斯谈到自己特别欣赏的漫画家布鲁斯· 班斯法瑟时,他崇敬的这位漫画家是参加过一战的士兵,其幽默的漫画不仅给枯燥乏味,黑暗危险的士兵生活带去快乐,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战争中士兵的遭遇。面对个人、他人、众人的苦难时,这或许是作家们能做到举重若轻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谈论《到大地尽头》的义务兵役制度主题时,格罗斯曼表达了对巴以和平的愿望,希望双方的协商与让步能带来和平,打破人民对暴力的恐惧。他说谈论政治时,我们要记住的是,对方是我们一样的人。这样才有利于摈除偏见达成共识,迈向和平。他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他们不是一定要生活在战争与冲突中,他们是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越是绝境处,文学的力量就愈能彰显。文学所启迪的选择,所给人的慰藉。同是犹太人的以赛亚· 伯林在《柏林谈话录》中回答贾汉贝格鲁的问题“您认为必须跟巴勒斯坦人和解吗?”时,回答说“当然要和解。和解是对的……是迫在眉睫的事……要理解反对自己的人,这是赫尔德教导我们的。”这个对话早在格罗斯曼之前发生,同为犹太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理解对方、和解、和平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或许不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也代表了那个民族大部分人民内在的渴望。如果可以,谁愿意终生生活在对战争与暴力的恐惧中呢?因为一直渴望以色列可以和邻居,尤其是巴勒斯坦保持和平的关系,所以格罗斯曼说自己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接受采访。而且我在格罗斯曼这里也看到了作为人、公民的无奈、绝望、希望,以及承载希望的行动:不停地发出声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说,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读完作者对格罗斯曼的访谈,更加觉得如此。像格罗斯曼这样的作家,他们不自觉或自觉地承担起这个使命,是人类正义的使者与召唤者。
如果说格罗斯曼告诉我们,笑等于自由的话,另一位受访作家,畅销书《岛上书店》的作者,加布瑞埃拉· 泽文,这位对书店情有独钟的作家,被对书店情有独钟的崔莹问了一个关于书店的问题,作为对书店同样情有独钟的读者,我在这几个问题里读出了特别多的快乐与共鸣。四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泽文的这本书中提到的镇店之宝,爱伦· 坡最早作品的珍本,所以对她这个与书店有关的谈话尤觉亲切,也产生了特别多的共鸣。泽文说她喜欢书店的味道,而且,小时候父亲给她五美元让她挑自己喜欢的书。所以在她的记忆中,书店意味着自由。这种感受不仅适用于童年的泽文,所有的爱书人都会有共鸣吧。读了她对书店经历的心路历程,最初的爱,因商业化而生的远离,再到后来因写书而复得的爱,以及她由此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先成为一个好的读者,才能成为好的作者,会让人慨叹,书店不仅对于读者,对于作者而言也是一种福祉。崔莹让泽文介绍几家印象深刻的书店,她特别提到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格罗利尔诗歌书店,让我想到了英国唯一一家的诗歌书店,位于世界第一个书镇海伊小镇上的“诗歌书店”,而我在那里也确实遇到了一位女诗人。她应该像泽文一样“渴望住在这样一家书店里”,居于自由之中吧。
格罗斯曼与泽文所特别强调的自由,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对难以挣脱的强大现实的对抗与释放,这种现实有个人的,也有民族的,简言之,在这种对抗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某部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疗愈。
写作与疗愈
即是说,无论是面对个人的创伤,还是民族的伤痛,这些受访的作家们都在传递着写作的疗愈作用。乔布斯的女儿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在以父亲乔布斯的传记为载体书写自己成长的作品《小人物》中,治愈了与父亲曾经别扭的关系,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伤痛与耻辱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她自己所言,她甚至可以自信地书写其他书籍了。布克奖作品《狼厅》的作者,2022年9月去世的希拉里· 曼特尔,曾经面对婚姻危机、手术病痛时,也是在写作中避难。曾经担任企鹅出版社与英国《卫报》的童书编辑的朱莉娅· 埃克谢尔提到,童书作者的童年大都有创伤。他们书写的童话或许不仅疗愈了他们自己的童年,还会给万千童书的读者带来快乐。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同情者》的作者阮清越在民族创伤的苦涩伤痛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在书写中去探索和疗愈。在书中书写个人伤痛也书写民族伤痛的格罗斯曼更是表明,写作对疗愈个人悲痛与民族内心的伤痕都在发挥着作用。著名学者乔治· 斯坦纳也曾告诉《巴黎评论》,他一遍遍的书写,就是为了从各种层面上“走出大屠杀……走向别处”。不仅要走出伤痛,还要走向某处,这是写作所能带来的超越疗愈的所在。同样,在《访书记》中,《孩子,你别哭》的作者,非洲作家恩古吉· 瓦· 提安哥更加直接地表达说,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尝试把殖民主义带给民族的创伤转变成财富。这种财富或许就是在疗愈中带来的对自己民族的更健康正向的发展。

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同父亲
被问及“回忆会不会对你造成二次伤害?”时,丽莎· 布伦南· 乔布斯的回答让人深感写作所带来的疗愈所在。她承认有些回忆很难下笔,但当她最终写下并且揣摩这些内容时,她意识到,当时关系出问题的父母比正在回忆与写作的她年龄还小,这个角度完全不同于她自己身为小孩子时所看到的种种。她多了一层理解,她看到了,当年充满激情的年轻父母也在努力解决问题。是这样的意识让她少了很多痛苦,亦如她自己所言,这个写作给她带来的意义是,她的童年并没有她曾认为的那么悲惨,也有不少的美好时光。英国的评论家,艺术家与思想家约翰· 拉斯金,在他的自传《过往》(Praeterita)中也特别提到,他没有想到,在回忆并且书写过去的生活时,它们远比自己期待的要有趣得多。这些快乐当然能有助于疗愈自己以为的成长过程中的创伤。英国当代女作家珍妮特· 温特森同样是在书写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时,也是在对曾给自己带来很多创伤的养母的回忆中,在对几乎让自己选择了结性命的曾经恋人的回忆中,在不断对这些创伤的书写中,理解了那些曾经伤害她的人,在这种理解中放下了与过去的挣扎,完成了对自己的疗愈与救赎。这就像是丽莎所说的,“很多人的内心千疮百孔,需要自我救赎……只有弄明白过去,才能停止和过去 ‘搏斗’”。
我在丽莎· 乔布斯的访谈中看到了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来的疗愈性自传的传统。虽然《忏悔录》是宗教性的,但奥古斯丁在对旧我,伤痛,新我的回忆,描述与沉思中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带着全新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与自己。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华兹华斯的《序曲》,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自传》,拉斯金的《过往》,温特森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与丽莎· 乔布斯的自我疗愈性的传记《小人物》也是对这个传统的继续。而且,虽然她的《小人物》被别人看作是她父亲乔布斯的传记,但她自己的成长其实才是真正的主题。丽莎· 乔布斯可能并非有意把作品安排成这样,更多由于她父亲的知名度,被解读成了这样。但这种现象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著名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 斯坦因。她的《艾丽斯·B· 托克拉斯自传》就是以女友的自传形式写自己生平的范例。不同的是,丽莎无意如此,而斯坦因有意为之。这多么有趣的巧合啊。作家们在写作中不仅疗愈了自己,也为可能有相似经历的读者提供了看待过去与伤痛的方式,在阅读中得到疗愈,又或得到灵感,拿起笔,开始自己的疗愈之旅。有些作家会有意识如此,比如,拉斯金说,自己会尽可能详细地回忆,描写可能会对读者有用的那部分过去,新闻学科经典作品《宣传之路》(Road of Propaganda) 的作者,同时也是有着悲惨的童年经历的诗人,凯瑞· 道林(Karin Dovring),在写给刁教授的书信中说,“诗人最大的快乐是他的作品能够对生活在我们这个艰难世界上的另一个人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有些作家或许初衷只是面对自己的伤痛,但幸运的是,他们的伤痛与疗愈刚好也是哪些读者的良药与出口。这并非一种臆想,这种双向的疗愈甚至是有一定的神话根据的。两千多年前,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所写“如果有人因心灵刚受创伤而痛苦,或因受打击而恐惧时,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他就会立刻忘了一切忧伤,忘了一切苦恼。”(张竹明 蒋平 译)所以,得缪斯灵感吟咏的歌者对听者和读者是一种疗愈。无论是神话还是现实,无论是几千年前,还是今时,于创作者和读者都是如此,这多么令人欣慰!
写作是一种靠近
以写作作为疗愈,在作家们走进自我的同时,无论于有意还是无意间,他们也在靠近着这个世界。
泽文以《岛上书店》作为读书是一种孤独的行为的隐喻,但她也说,正是因为读书,很多人因此联系在了一起。泽文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帮助读者理解世界。当享有国际声誉的挪威戏剧家约恩· 福瑟,被问及反复书写的孤独时,回答说,“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靠近,对他人与整个世界的靠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 托尔卡丘克被问到伟大作家与伟大心理学家的关系时,也回答说,文学写作“是一种深刻的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凯瑞· 道林说:“诗充满了和别人交流的需要,不只是一对一的那种交流,而是把我的个人情感和对人类经验的观察与全社会所有的人分享。”有趣的是,写作,如阅读一样,是一种孤独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撤离,从喧嚣的现实中的撤离,但这完成于孤独中的行为却又是一种热情的靠近。他们同受访者宇文所安所描述的杜甫在诗里“抱怨蔬菜不好,向给他送豆酱的人道谢;……称呼仆人……写诗给他们……”,他的诗也是他靠近世界的方式。斩获诸多非虚构写作奖项的迈克尔· 麦尔的《东北游记》《再会,老北京》更是作家在书写中对异域世界的一种靠近。他们让我意识到写作除了因使命感而发生时,也会因为爱而发生。除了对世界抽象的宏大的爱之外,还有更加具体的爱,比如麦尔在受访最后所言,《再会,老北京》是献给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的父母。《东北游记》是他献给儿子的,他希望儿子能够了解自己妈妈,即作家的中国妻子成长的地方。《卧龙之路》则是他献给妻子的。

闵福德
说到爱,这一点在对汉学家的采访部分最为突出,很多汉学家对汉语文化的热爱,以及因此而生的热情与投入特别有感染力,让人感动。《红楼梦》的英文译者,汉学家闵福德在被问及翻译是否存在技巧时,回答说,并不觉得存在什么技巧,但他特别提出说,译者要对翻译的文稿有感觉,要喜欢这些文章,才能全身心投入。在此基础上,他把译者与翻译对象的关系比喻为恋爱关系。所以,他认为,如果足够喜欢对方,即使出现或者存在问题,也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虽然喜欢无法成为胜任翻译的唯一条件,但这一点一定会为翻译的进行助力,为其质量增色。受访时,宇文所安阅读杜甫已经50多年了,当被问及在不同阶段对杜甫不同作品的喜好时,他说自己依然喜欢五十多年前喜欢的诗作,而且更加欣赏杜甫的广度与多样性。而且他特别提到有些诗到特定年龄阶段才能读。这种持续半个世纪而且依然还会持续下去的对同一个诗人的热爱,以及更深的爱,化作他持续多年对杜甫的翻译与研究。而且,也一定是带着深深的爱,闵福德才有激情与耐力用16年翻译了《红楼梦》,用12年翻译了《易经》,他才能表达出美丽的比喻,把《易经》和《红楼梦》比作是“彩虹的两端”。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所言,没有什么比激情更有感染力。读着宇文所安对杜甫的热爱,闵福德对《红楼梦》与《易经》的热爱,作为读者,尤其是一个中国读者,我是没有办法不受感染的。应该也是因为热爱,所以王德威坚持把《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编著成“很有意思的”内容,而非枯燥无生命力的教材。
苏格兰插画设计师乔汉娜· 贝斯福,《秘密花园》的作者,被问及,随着同类成人涂色书的出现,会不会担心失去市场时,回答说自己不担心,因为销量过千万的《秘密花园》就是她融入了自己的爱和激情的产物:“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作品、我的激情,希望他们和我一起涂色。只要这个想法不变,我就不怕失去读者。”当然,并非所有向世界的靠近都会如贝斯福的作品一样获得销售方面的成功,但是大都如她的作品一样,这种靠近是基于爱和激情而生。
写作与生计
包括柯勒律治在内的很多作家无论对自己哪方面的才华有信心,都很少会对自己作为畅销书作家的才华有信心。《访书记》中的贝斯福也是在自己意料之外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从而得到一大笔收入。关于写作与生计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也在这本书中被频繁问及。
闵福德回忆参与《红楼梦》的翻译的过程时,特别提到,当时自己还是一个学生,非常穷,但是放弃了其他工作,全心投入。事实上,写作也好,翻译也好,它们与生计的关系不仅是每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本书中被频繁问及的问题之一。两百多年前,当济慈告诉自己的监护人他决定以写诗为生时,他的监护人理查德· 艾比认为济慈不是疯了就是傻子。与济慈这个对话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中也记录了诗人对自己早年开始从事文学时,在这方面的清醒。他回忆说,自己在二十三四岁时就已经非常明白,他无法依靠文学来维持生计。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曾经抱怨说哥哥写了几十年的诗歌连一根鞋带钱也没给自己赚到。
多萝西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以写诗或文学创作为生,即使是在今天,也并非容易的事情。这些被采访的作家们,尤其是非虚构的作家们都提到了这一点。乔纳森· 哈尔在写作的八年期间,几乎主要是在靠妻子挣钱养家。他的朋友,另外一个获得过普利策非虚构类奖项的作家特雷西· 基德尔,在崔莹问他“做非虚构作家的日子好过吗?”时,回答说,“做这个工作不够养家糊口。”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在美国,任何能以写作谋生的人如果不承认自己很幸运的话,都是在误导。”他甚至开玩笑地说, 他爸爸曾经建议他如果要写作的话,最好娶一个有钱的妻子。当然,现实是他并未如此,但在自己和妻子的努力下,生活与写作也是极其和谐地并存着。在流行文化部分,崔莹问美国著名科普漫画家兰道尔· 门罗“你怎么谋生?”时,对方也说只靠刊登漫画是无法挣到钱的,他摸索出“靠在网络上售卖和漫画有关的产品”谋生。刁克利教授笔下的库塞也是主要做保险业的工作,只不过确保这份工作在精力消耗上不会影响他写诗,而且也能维持生计。
虽然从事文学或其他类型方面的创作,对大部分作家来说,很难维持生计。但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受访的大作家们没有一人因此放弃写作。无论以任何工作为生,创作是可以进行的,甚至还可以取得一番成就。英国著名的随笔作家查尔斯· 兰姆几乎一生都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自己的《伊利亚随笔》以及他和姐姐玛丽合著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在两百多年后依然还是经典之作。刁克利教授在《诗性的对话》中提到,美国诗人华莱士· 史蒂文斯也是在保险公司工作,且他的诗歌两度获得国家图书奖,在1955年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当文学艺术的资助人这个概念与现象渐渐淡去时,我想,谋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是大部分作家们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卡夫卡、佩索阿、T. S.艾略特等这些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与诗人们不都是在从事维持生计的工作之余创作且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吗?《访书记》中的作家们面对这个最现实也是极具历史性的问题的真诚回答,以及他们对此的应对及其取得的成就,对于有写作梦想的人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让情节自然发生
除了写作与生计之间的关系,《访书记》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是关于作家们创作时的状态,是勤奋地努力书写,如英国作家毛姆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每天自律性地书写数千字,还是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言,让“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铸就好的作品?又或是,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赫塔· 米勒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说,“语言知道打哪儿起,打哪儿落……那些句子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到达那里。”
《访书记》中很多受访作家被问到是否提前规划写作时,大都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们或者选择把作品交给潜意识,或者交给人物,又或者交给某个场景,让它们引领故事的行进。
曼特尔被问到是否先计划好情节时,回答说,她从未事先设置好,而是随时想到的,之后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托卡尔丘克被问到如何为写作准备时,也回答说自己的潜意识会告诉她怎么写作。莉迪亚· 戴维斯同样回答说自己不会提前列提纲,而是“顺其自然”。普利策小说奖作品《奇山飘香》的作者罗伯特· 奥伦· 巴特勒也是把自己小说交给其中的人物去决定,而非事先决定好。他甚至说自己在动笔之前,不知道能写出什么。关于这一点,美国作家威廉· 福克纳曾经说自己“拿着一张纸、一支笔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紧跟着记下他的一言一行。”多么生动!小说《华氏451度》的作者雷· 布拉德伯里甚至说是他的主人公蒙泰格创作了这本小说,而不是他。而且他说,“如果你赋予人物生命,别挡住他们的路,你就可能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了。”(于尔根· 沃尔夫,《创意写作大师课》)巴特勒也是在他的这些前辈作家所属于的传统中。巴特勒说,自己创作人物不需要过多准备,只需要把情感注入人物,让自己的情感,欲望与人物保持一致。当然,在仔细阅读完他们的访谈之后,你会发现,这并非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等待,这些作家们的信心,或者是来自自己的大量阅读,如曼特尔,托卡尔丘克,戴维斯,西蒙· 沙玛和特雷西· 基德尔也都提到乔治· 奥威尔的作品对他们创作的启发与影响;又或者是相信自己的经验,如巴特勒身为演员的经历,让他们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些感觉是读过的书,揣摩过的角色,都化作无意识,引领作家们的创作。
因此,这也说明,这种被动与消极中存在着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迈克尔· 麦尔虽然说,“我没有主动改变我要写的内容,是我遇到的现实改变了我的故事。”但在此之前,他无数的观察,笔记,访谈,阅读,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在为敏锐的观察力添砖加瓦。也是因为如此,他在一次中美领导人的政治宴会上,因为偶然惊讶地发现本杰明· 富兰克林签署了《1783年巴黎条约》,对这位他只知道在雷电中放风筝的科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他的研究中,发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可以展开与所有富兰克林传记者不一样的角度,从中国文化,思想对富兰克林的影响开始一本书的创作。如若没有平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了解,我想麦尔在这方面的灵敏度也不会如此。他就像托卡尔丘克所说的在独自旅游的状态,“用眼睛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且要全神贯注。”这似乎就是一种以积极方式发生的消极感受。
结论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会让人一方面沉浸于作家们的谈话中,另一方面产生很有趣的联想。比如,约恩· 福瑟被问到剧本中的人物没有名字的现象时,他说,他写的是生活的本质,与名字无关,而且名字可能是一种干扰。读到这里,我想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若泽· 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也是没有一个角色有名字,但在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却能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物。我似乎在福瑟所说的“生活的本质”这里找到了答案。原来伟大的作家,即使不赋予角色名字,也能让人对这些角色印象深刻。福瑟被问到剧作中的沉默与孤独时回答,有些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让我想起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所写,“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查良铮 译)赫塔· 米勒也说,“因为不管我们在说什么,没有说的总是比说的多。”(《巴黎评论:作家访谈7》)在小木屋里写作的巴特勒让我想到有同样写作习惯的塞林格,塞林格甚至告诉妻子,除非家里着火,不要打扰他。
总之,读到一本好书,像是同时读了很多书。思绪会如作家们的谈话一样自由行走,打破时空。足不出户,却像走遍了世界,看尽了风景。所以很难不感谢被访谈者的智慧,思想,幽默,情感,有时候还有诗意与慰藉。但在内心更默默无声感激的是访谈者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在阅读中会忘记问题沉湎于被访谈者的语言中,但访谈者是推开那扇门让我们看到美、智慧与共鸣,同一个、另一个世界的人。在这样的问与答中,我感受到了问者与答者的思索,也在这思索中为自己心中曾存有的疑惑找到了一个答案,一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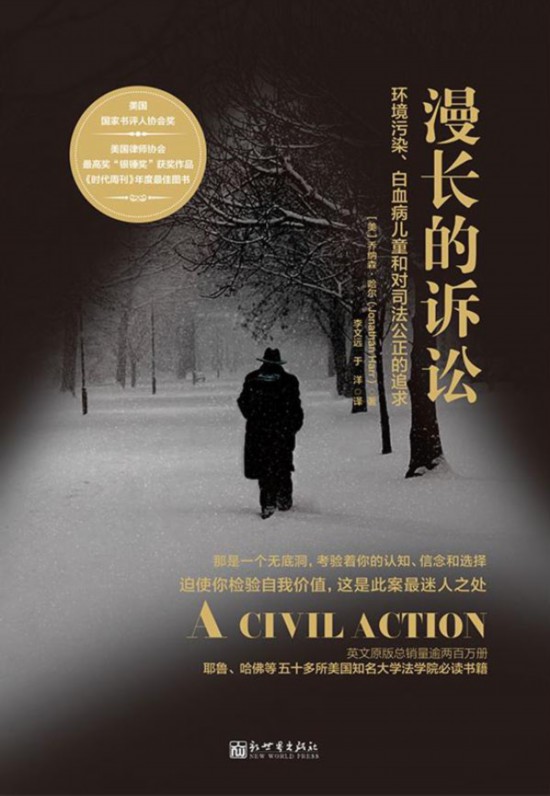
《漫长的诉讼》
崔莹在访问乔纳森· 哈尔时,问他“怎样的采访才算是成功的采访?”哈尔的回答是:“我在采访中寻求事实、感受,希望捕获受访者的个性和反应。”当然,这个问题与上下文有紧密的关系,采访在哈尔本人历时八年完成的《漫长的诉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让这个问题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崔莹本人在这里是一个采访者。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在问哈尔,在这里,它是关于采访的采访。在文学中,关于小说的小说被称作元小说,所以我不自觉借用这个概念在书页空白处写下“元采访”。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对话,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准确地帮我表达了读这本访谈录时的感受与收获。
我深知,把这本书当作创意写作指南去读会极度简化这本书的丰富所在。这里更吸引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这是人对人与世界的思索,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回顾,思索与展望;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一起把最幽微处的明亮探究与分享出来的尝试。保罗· 比第告诉作者,虽然他身为黑人,但他的世界里从来不是简单的黑白两色,而且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对啊,黑白的二分法何尝不像是思想领域一直以来的二元论,过于武断并且无味地简化了这丰富的世界。同样,《访书记》比我能写出来的更丰富,更生动,更感人,更发人深省。
世界知名的文学批评家乔治· 斯坦纳在《漫长的星期六》中说,好的评论是一种感谢的行为。愿我很恰当地表达了对崔莹这本《访书记》的感谢。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