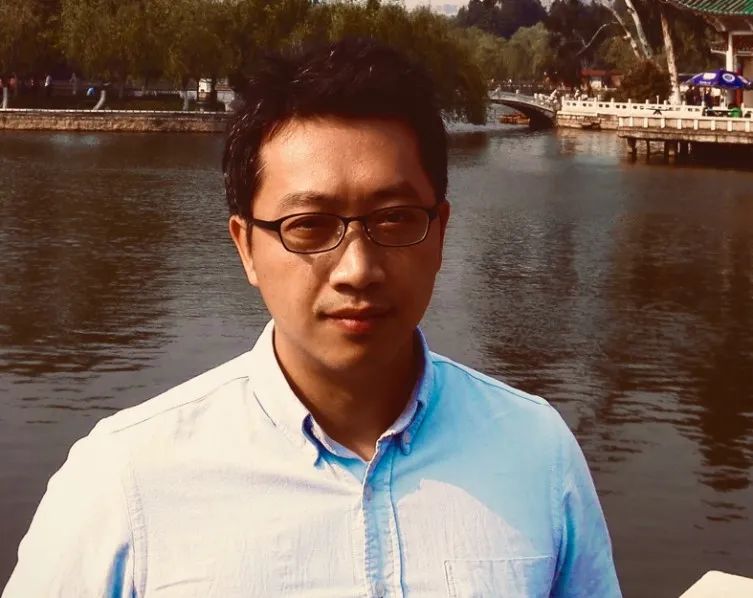
楼河,江西南城人,
尽管陈家坪的诗在同行那里广受赞誉,但它们的目标读者却应该是那些不写诗的人群——一个社会意义上需要启蒙的“大众”。
陈家坪的诗在批判中同时伴随着悲伤。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清醒者,但他显然并不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群的对立面上,而是认为这个人群和自己一样遭受着痛苦。
诗歌终究是关于爱的,并且,诗歌与爱的关系并不止于它是爱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爱的创造,就像我们通过对语言的运用而重新发现了语言一样。

爱的私有与普遍
陈家坪是个有多重身份的人,在所有的这些身份中,诗人这个角色既是显著的,又是隐晦的,导致这一结果的是同一种原因,即:由于一种社会身份,作者的诗人身份被增加了内容上的重量,但与此同时,诗在形式上的重量被减轻了。换句话说,在普遍的同行印象里,陈家坪是个价值观类型的诗人,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本探索的先锋诗人。我们会去关心他的诗歌主题,但并不会怎么关心他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种情形是,在形式服务于内容的观念下,当某一个主题足够重要时,有人还会反对形式上的精雕细刻,而希望表达这一内容的形式是直接的,以及粗犷的。形式上的重量被弱化,其实也是对诗人的一种遮蔽,但这种遮蔽也许是作者有意制造的,很可能,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价值观的内容同样是他更加关注的重点,他的诗也许是一种致力于由内容决定的形式。对于诗人的同行们来说,他们同样关注的是陈家坪作品中的这一点。这样的作品不无道德上的态度,对于陈家坪,这种道德态度更是一种启蒙的意志。所以,尽管陈家坪的诗在同行那里广受赞誉,但它们的目标读者却应该是那些不写诗的人群——一个社会意义上需要启蒙的“大众”。因此,这种同行的赞誉事实上隐蔽着某种轻视,准确地说,是对他的作品作为一种文本上的轻视。对于陈家坪,他的同行也许更加关注的是作品的隐喻所指的内容,而不是隐喻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陈家坪的诗在同行中的赞誉里满足的是后者作为知识分子介入世界的心理需要,是种道德满足,而不是语言的愉悦。这当然也是一种遮蔽。作为他的诗歌同行中的一个,我并不想否定这种需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当形式主要由内容决定时,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拥有明确的主权,这展示了主体的能力,使我们对自己的写作拥有一种坚实感。
细致分析陈家坪诗歌中的具体内容,既有一种风险,同时也容易陷入空洞的重复——因为它的内容已是显学。所以,为了追求一种安全地带上的新意,我更愿意去讨论陈家坪诗歌中的形式,或者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在我看来,尽管遭到同行甚至诗人自己的轻视,但我依然看到了某种纯粹的特征。我认为它属于诗人,而不是它的外延知识分子。但很可能,正是诗人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性,构成了陈家坪诗歌的内容以及写作的动力,就如他的诗歌标题(也是他的诗集名字)“囚室与鸢尾”一样,我认为这两个名词的并列既是意象上的冲突,也是两种身份的冲突。这两种身份是相互作用的,就像“囚室”对鸢尾形成了压力而同时鸢尾将对囚室产生解脱那样,正是由于压力的存在,解脱才具有了力量感。正如哈贝马斯在他的《认识与兴趣》里对人类知识的三种类型的分析中所表明的那样,审美兴趣朝向了解放,但它必须与对真理的认识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真理与他者对主体制造的限制,使得主体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既充满挑战,但也在挑战中获得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陈家坪的诗是被他的身份塑造的,是经验之诗,也是期望之诗。
事实上,尽管诗人身上的那个知识分子性质具有话题性,但当代诗日渐封闭的竞争导致的诗歌风尚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化和趣味化的倾向,这种趣味化不是说它反对了诗歌中的道德内涵,而是说它幽默地对待了道德,以中立或客观的姿态将主体从事件中分离,从而能够毫无顾忌或者毫无负担地运用或展示形式。用一个比喻也许是,诗歌里的道德内容变得像是诗人们的学术对象。换句话说,诗人语言的自由是以牺牲掉道德张力为成本的,通过这种舍弃(有意的忽视或无意的忘记),形式化的诗人们让作品从社会意义的背景中脱离出来,从属于一个诗歌的可能性世界里,形成了诗的纯粹性。本人对这些诗歌态度没有立场,但我想指出的是,陈家坪的写作与此相反,他的诗不仅是以参与而非以分析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同时将诗歌的世界主要定位在个人与体制之间,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或者生动的自然。正是因为这种方式,他的诗具有了重量感,而不是趣味化的轻盈。在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轻盈是他的诗歌重量中必须被牺牲掉的代价。某种意义上,这种重量感实际上也是诗歌的一种形式,但它并非由语言独立完成——譬如通过增加节奏的阻断,使用沉郁的意象等方式,比如诗人多多——而是通过与内容的结合,在隐喻的暗示中获得的。也因此,陈家坪的诗歌语言被它的内容挤到了边缘。边缘是一个不受关注的位置,但并非不存在。为了让这篇文章有所揭示,我认为陈家坪的诗歌特征除了具有一种与社会紧密相连的重量感之外,实际上还有他对语言的掌控能力,这种能力平衡了内容而让作品保持了光润。也就是说,如果去除掉诗的内容,其形式也足以支撑作品的完成度。换句话说,我认为陈家坪的语言能力可能超出了许多诗人,但它作为一种代价被牺牲掉了,至少是被限制住了。
在我看来,陈家坪的诗歌语言同样具有生成的特点,我们会发现,他的诗有着很强的流动感,其中的想象如同气泡从河水中涌现一样,自然流动的同时制造了新颖的形象。譬如在《娣亚曼吐和阿卜苏的对话》这首诗里,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语言流动状态下的想象力涌现:“我是咸的,你是甜的;/我是阴性的泥土,你是阳性的/天空——始于天地分明,/众神之母与众神之父,/死于众神的子孙。/父亲的神权在儿子的手中结束,/妻子,有失去丈夫的仇恨。/分裂情感与智识,一种野蛮的/力量,催生一粒种子的根芽,/身体有被分裂的辉煌,/把我分裂成你和他——而我/和你隐藏在一切人世关系中,/我们的过去是神话,/我的未来是寓言。/我不是可以叙述的故事,/如果死亡把我们分开,/对话又让我们在一起。”诗的节奏自然而流畅,毫无生涩,其中想象力的转化也显得十分纯熟,新颖中绝不突兀。娣亚曼吐和阿卜苏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创始者,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一首诗如何对一个现成故事进行的改写,诗人选择了其中的死亡与爱欲的部分,使它变成了一首既具有私密感的情诗,同时又成为一首具有普遍性的沉思作品。就后者来说,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矛盾的性质:欲望是生命的源头,但来自于对死亡的抛掷,而死亡同样纠结了爱与恨的双重历史。就我的个人偏好而言,后者的沉思并不是我关注的部分,我更关心的是一首诗如何创造了私密的感受,并在这种感受中形成一次对爱这一概念的新鲜体验。爱的概念与具体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但表现出情感的随机性,我们能够在这首诗的语言生成特征中读到这种随机性的流动感和自由的体验。在我看来,这是一首写给妻子的情诗,它同时还有一种隐晦的、被知识所溶解或者转换的性描写,从而使这首诗在一种情欲的空缺(渴望)中被心灵理解的需求所填补,进而变成了呼唤,呼唤出一个来自爱的赞同。换言之,这是一首向爱人表达爱的诗,同时是向爱人剖白心迹的诗,而剖白的方式——那个要说出的道理——因为加入了性的私密性而形成了心理连接的预设立场。并且通过剖白,面向个人的爱欲被升华为普遍的爱的感情——某种博爱,或者大爱,有着创世般的蓝图。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陈家坪诗歌中的道德态度里,使其变得坚实可靠的因素就是一种对世界的爱,它容纳了私密的个人爱欲,同时也借助于后者的具体性而使这种大爱变得更加坚实。因为这种爱的存在,陈家坪的诗在批判中同时伴随着悲伤。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清醒者,但他显然并不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群的对立面上,而是认为这个人群和自己一样遭受着痛苦。因为具有这种怜悯,陈家坪的诗始终具有情感上的真诚,我认为,这种真诚是稀缺的。和陈家坪拥有相似的价值立场的诗人不在少数,但我们会感受到其中不少诗人有种精神上的傲慢,他们以一种道德优越感凸显了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稀缺的真诚构成了视角沉潜的约束,从而使得陈家坪的诗在相似的道德化的写作中超越出来,让作品免于被道德说教所害。换句话说,由于立场的下沉,同时因为经验的坚实,使得陈家坪的诗即使可能同样有种价值宣扬的意图,也变成了充满真诚的表达。而只有在诗人的真诚里,诗歌才具有独立于作者和任何中心性观念的主体地位。在说教的作品中,诗是观念的工具,而观念成为显示作者主体(甚至仅仅是一种个人名声)的工具,由此诗歌的语言也变成了信息的载体。我曾经有个观点,认为评价一个作者的才华可以去考察他在类似于命题写作中的能力,因为在命题作文里,写作的目的被明确地预设着,在此情形向下,作品的内容要求大于作品的形式要求,将更加清楚地考验作者对语言非信息属性的把握能力。换言之,当作品被要求了一种工具的性质时,作者是否还能显示出作品的主体性而让自己处于一种被动的写作姿态中,这成为了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陈家坪作为诗人的敬意实际上更主要地来自于他在陈述了某些强势的观念之同时,还保留了语言及作品的自主性,而不是其中的思想立场。在我看来,这种自主性就是诗性所在。
作者保留了作品中的自主性,这不是一种写作策略,而是一种写作态度。当作品的自主性得到伸张的时候,作者的自主性实际上是被控制的,因此,在这种态度里,实际上意味了作者对作品的尊敬,以及对自我的克制。我认为,这种克制可以类比于因为爱而产生的让步甚至自我牺牲的冲动。所以,陈家坪诗歌中的关键要素在我看来并不是某种价值观念,而是一种建立于具体性基础上普遍的对世界的感情。正是情感上的真诚,让他的诗避免了因为观念上的相对单向而可能导致的失真危险。陈家坪诗歌中的价值观念不是某种存在策略,他是言行一致的,抵制了中国文化中常见的虚伪。这种真诚也避免了他对极限性质的诗歌形式的热衷。由于诗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原因,诗的真诚观念很容易产生对自我的浮夸,由此,诗人也经常在写作中引入强烈的事件、新奇的意象和语言构成等,以张扬自我的独特性。陈家坪的诗避免了这种姿态,因此,尽管他拥有许多诗人不具有的经历,但我们依然在他的诗中能够读到一种和平。这种对自我的克制使作品在对意义的寻求过程中始终处于清醒的状态,而从未陷入迷狂。在这个意义上,对世界的真诚保证了认识上的真实。由此,我们在他那些看似谴责的诗歌中,似乎也读到了谅解;在他的自我认同中仿佛也同样感觉到自我否定。换句话说,诗人即使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依然没有放弃通过分析以尝试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可以这样说,尽管作者对他想要论述的世界持有预设立场,但他对世界的真诚(它包含了爱)避免了这种立场对世界真实的过度解释。
爱,经由特殊的经验进入普遍的意识里,这在陈家坪的《爱》这首诗里有着更加显著的体现。诗的副标题“给妻子”已经表明它是献给妻子的作品,爱欲中的私密性因为这一公开的申明而被略去了,但诗人叙述的姿态依然十分亲密,在我看来,这种亲密性不是由肉身的接近所形成的,而是由于事件的重大性被包裹在了一起:通过一个需要共同应对的严重事件,一种情感上的连接被照亮了。这显然丰富了爱的内涵,它不再是愉悦的代名词,而是包含了深刻的痛苦,并经过对这种痛苦的共同承受,升华了爱的连接与私密性所产生的愉悦。但是很明显,事件的严重程度是被掺杂在一个背景中得到体现的,从而使得这个事件不仅是“我”和“你”之间的事件,同时也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事件。这个“他们”含义复杂,既可能是一个需要抗争的对象,也可能是一个需要拯救的对象。爱因此从一个家庭单元弥漫到了世界中,从特殊进入了普遍;同时从对爱这个概念的感受,上升到了对爱这种观念的理解。由于概念转化为观念,情感的随机性在对某种世界秩序的解释中归纳出了必然性:“我们”必然是爱的,这爱也成为了一种必须。
如果说《娣亚曼吐和阿卜苏的对话》写的是“我”对“你”的爱,那么《爱》这首诗实际上让一个事件成为一次诗歌的机遇而写出“你”对“我”的爱。尽管在诗的第一人称方式里,它看起来依然像是“我”对“你”的爱,但当诗人说——“白天,我想你,我很奇怪,/你居然没有进入我的梦乡。/某些时刻,一想到你我就猛然会/哭泣——但是,我得维护我的尊严”——此时他显然渴望的是被爱。被爱是爱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形式。在主动的爱里,爱不需要理由;但在被动的爱(的需要)里,爱却必须有个理由——“我”需要“你”的爱,但“我”凭什么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需要解释。这种被爱显然是卑微的,深刻于卑微的自我解读,因此当诗人这样说——“我不知道,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你将会忍受多么漫长的孤单。/终于,看见你写的字,我深深的陷入/那些标点符号——我理解中的停顿。/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心安,/因为你始终在,别的不重要。”——之时,一种复杂而细微的情绪向我们呈现了极为矛盾的对现实的解读:这个现实是个痛苦,这个痛苦因“我”而生,但连累到了“你”,然而在另一个角度里,它未尝不是“你”真实地爱“我”一次的机会。对爱的信念中实际上隐蔽着失去爱的担心,它以一种愧疚感表露出来,并通过对普遍之爱的提出而消除其中的忧虑。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们的爱”不仅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同时内含着“你”对世界的真诚善意时,“我”对“你爱我”这一事实充满了信心。
渴望被爱在卑微中压缩了自我在相爱关系中的地位,但同时在爱的亲密过程里重新点燃起信念,从而具有了超越性的爱世界的余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真诚的爱意一方面扩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情,又在另一方面缩减了我们对世界的占有。换言之,如果一首诗是一次爱的呈现,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担心与愉悦并存的体验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真实:只有在与他人或世界的联系中,我们才能感觉到幸福,但这种联系却不是完全主动的,因而并不意味着我们因为拥有了这种主观的感情而在人际关系中拥有了优越性。说得更清楚一点,爱产生的是这样一种机制:它让我们感到富足,但这种富足感不是因为我们占有了世界或者掌握了某种关系,而是因为我们为这个世界或者这一关系有所付出与承担,从而确认了我们与世界的亲密。极端地说,爱产生的体验感是对主体真实的一种浮现。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终究是关于爱的,并且,诗歌与爱的关系并不止于它是爱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爱的创造,就像我们通过对语言的运用而重新发现了语言一样。
附:
陈家坪的诗
娣亚曼吐和阿卜苏的对话
我是咸的,你是甜的;
我是阴性的泥土,你是阳性的
天空——始于天地分明,
众神之母与众神之父,
死于众神的子孙。
父亲的神权在儿子的手中结束,
妻子,有失去丈夫的仇恨。
分裂情感与智识,一种野蛮的
力量,催生一粒种子的根芽,
身体有被分裂的辉煌,
把我分裂成你和他——而我
和你隐藏在一切人世关系中,
我们的过去是神话,
我们的未来是寓言。
我不是可以叙述的故事,
如果死亡把我们分开,
对话又让我们在一起。
2018年
爱
(给妻子)
我想我肯定会回来,这一生,
这一次我们只是短暂的别离。
我想象着你将以什么方式入梦,
那是我们唯一可以见面的方式。
我听见你在笑,是的,我们没有
任何哀愁,尽管醒来我越发沉默。
我突然感到,我应该给你更多的安抚,
无法接受你在夜里,却没有我的陪伴。
白天,我想你,我很奇怪,
你居然没有进入我的梦乡。
某些时刻,一想起你我就猛然会
哭泣——但是,我得维护我的尊严。
在没有人性的地方,没有任何
监督的黑暗之处——我不能哭。
我不知道,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你将会忍受多么漫长的孤单。
终于,看见你写的字,我深深的陷入
那些标点符号——我理解其中的停顿。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心安,
因为你始终在,别的不重要。
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输过,
尽管我们赢得的并不是金钱。
再见面时,我会捧住你的脸,
不是看你有没有变,而是弥补
我似乎从未认真的看过你一眼。
临走时,你为我戴上了口罩,
回家后,我们摘下脏脏的口罩,
把它镶进一个白底黑边的相框。
2020.9.26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