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印工序大体是这样:先用尖头铁笔在钢质垫板上刻写蜡纸,然后把蜡纸挂上墨网,用滚筒蘸上油墨碾印,于是油墨透过诸多刻痕,一张张传单或小报便大功告成。这种活很奇妙,干得多了,少年们免不了别出心裁再干出一些花活,比如用多机实现多色套印,或在蜡纸上下足功夫,时琢时磨,时剔时刮,居然能捣腾出木刻、工笔线描一类图像,甚至印制出深浅不同的水墨层次,与铅印的正规报刊相比,效果难分高下。可以想象,要是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再闹上几年,一代铁笔艺术家茁壮成长,就靠那些侏罗纪风格的老装备,蜡刻印象主义或蜡刻浪漫主义也许要流派纷呈的。
多年后,徐冰说起当年,出示自己的一些油印插图,我一见就会心。想必这位大腕当年也是脸上常有油污,指头磨出硬茧,上街只看墙头张贴的小报,看小报又全然不在乎内容,目光直勾勾的,只是留心标题、版式、配图的艺术高招和创作心机。惺惺惜惺惺。他肯定注意到街头最精美的那几家小报,隔空神交了许多同道好汉,恨不能千里相会聚首把臂一吐衷肠。
我也在这个江湖里混过。
其时年满十四。
本人最大的从业污点是伪造印章。说实话,既然铁笔下能有艺术流派,刻出印章效果就只是小菜一碟。全国学生免费大串联历时约半年,终于被叫停,但同学们心痒痒的还想出去逛,于是盯上了铁路系统的内部车票。在他们怂恿之下,我借助一把放大镜,在蜡纸上精雕细刻,再用抹布蘸上油墨轻轻涂抹,很快就制作出铁路局的什么函件,其大红印章看来看去,几可乱真。有同学一见就乐坏了,“你索性再刻一个中央军委的公章,我们坐上轰炸机出去耍耍呵。”
以这种假印章骗车票居然多次成功。就这样,这一年夏天,好友们一伙去了广州,另一伙去了北京,再不济的也去畅游岳阳或衡阳,校园里变得异常安静,只有绿树深处蝉声不息。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我早已去过了,便留校守家。我所在的长沙市七中与烈士公园为邻,校园北部的山坡外就是浏阳河。如果同学们都在,我们常去河里骚扰民船,以满船的西瓜或菜瓜为目标,讨不成就偷,偷不成就抢,图的是一个快活。后来还有更神通的战法,那就是一齐对船老板大喊“陈老板——”或“樊老板——”。“陈”谐音“沉(船)”,“樊”谐音“翻(船)”,都是美丽江面上最狗血的咒语。有些船民一脑子迷信,一听到这种叫喊就叫苦不迭,就急得跳脚,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往船下丢几个瓜,算是堵上小祖宗们的臭嘴。
可惜我眼下孤身一人,构不成声势,没有预言“沉船”或“翻船”的威慑力,只好怏怏地提一条游泳裤提早回家。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1967年这一天的回家之路实在落寞得很,无聊得很,一路走得郎里咯郎。我走过飘飘忽忽的体育馆,摇摇晃晃的公交牌和米粉店,在白铁作坊前还没把弧线剪材看出个门道,忽听身后一声暴响。
事后依稀分辨出来了:枪声!
事后我还回忆起来了,街面顿时大乱,人们像一群无头苍蝇惊慌四散夺路而逃。如果我拍拍脑子,掐一把皮肉,还能回忆起一个老太婆摔跤了,另一个汉子盯住我的左腿大惊失色,于是我看见自己裸露的大腿上,有一个扣子般大小的血洞,开始往外冒血。这是什么意思?这红红的液体不就是血吗?我的天,刚才那一枪是打中了我?世界上这么多人影,我招谁了惹谁了,竟然如此背运,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要在这一刻回什么家,千辛万苦把自己往那个黑洞洞的枪口上凑?
我没感觉到痛,而且发现自己还能行走,便用游泳裤紧紧捂住了伤口,跟随人们闪避到路旁。我撞开了一张门,有用没用先求上一句:“我受伤了,请帮帮我!”说完才看清面前是一老一少两个惊呆了的女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一位女同学的家。她比我高一届。她肯定没想到,我们日后还有机会在同一个知青点共事多年。她肯定更没想到,她再后来移民美国,经商成功,与伙伴们天各一方,只是一份音信渺茫的模糊。
她是否还记得,她外婆找来草纸烧灰要给我的伤口止血时,两只手颤个不停,好几次都划不燃火柴?是否还记得包扎伤口时,她俩全身都软沓沓的使不上气力?……好容易,门外消停了,枪声和狂喊乱叫没有了。一个男声由远而近:“刚才那个伢子呢?那个受伤的……”大概是受邻居们指引,一个人敲开了房门。他瘦个头,还有点驼背,手里提一把驳壳枪,冲着我们裂开生硬的笑纹,“不好意思,刚才我们是在抓公检法那些忘八蛋,妈妈的,一时枪走火,枪走火。”
他说的“公检法”,是司法系统某个群众组织,大概是他们的对头。那时正是“文攻武卫”高烧期,每个城市都闹成山头林立,你争我斗,一旦红了眼便兵戈相向。连中学生手里也少不了苏式骑53、汉阳造79、转盘帕帕夏……说实话,多是些民兵训练用的破铜烂铁,子弹也不好找。谁要是扛上一支56式半自动,那才有几分正规军模样,有脸挎出去招摇过市。大家对此其实意见不小:北京那边说“武装左派”看来也是半心半意呵,要不然好枪都去哪里了?不是被一脸又一脸假笑的解放军早早藏起来了?
接下来的事较为简单。小驼背抱上我出门,送上一辆货卡,是他和同伙刚从大街上截来的,然后一路驶向湘雅医学院附属二院。看着呼啦啦的梧桐枝叶在天空中刷过,我已开始感觉到伤口裂痛,而且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弹孔,在大腿侧后,是子弹的入口。进入医院后,痛感更加猛烈的狂暴。不知什么时候,白大褂晃来晃去,一位女护士问我一些问题,爱吃什么菜,爱唱什么歌,爱玩什么游戏,是不是放过风筝或做过航模,诸如此类,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她这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瞥见手术台上那一大盆一大盆的血纱布,防止我大叫一声吓晕过去。据她说,手术时间稍长,是因伤口离枪口太近,火药残毒重,必须切开皮肉全面清创——这话说白了吧,“清创”就是用药纱条在一道肉沟里拉锯式的拉来扯去,就是用钳子夹上药棉团这里那里猛戳一通。
我哥来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找到了我——这里已人满为患,加床都差点加到厕所里去了。我哥对小驼背怒不可遏地喊:“你什么人?干什么的你?你会用枪吗?你也配拿枪?你的枪口再提高一点点,他就没命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实际上就是个未遂的杀人犯,杀人犯!谁在乎你那点水果罐头?医药费算个屁呵。他要是留下个什么,你这个家伙必须一辈子负责到底我告诉你……”
小驼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把手枪哗啦一声推上膛,狠狠地塞给对方,“那怎么办?大哥,你打我一枪。”
我哥愣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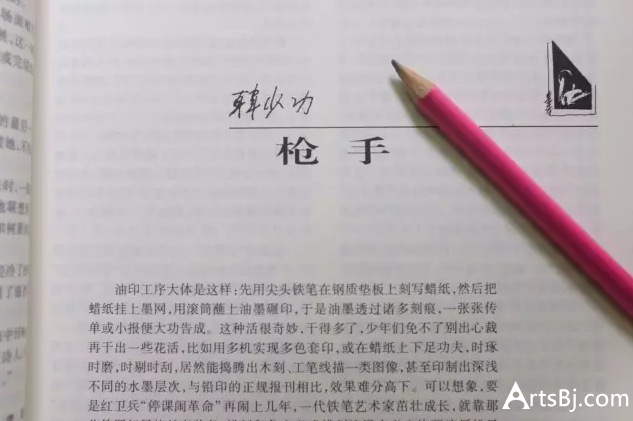
《枪手》结尾:
他最终被加刑重判,死刑。
食堂照例是下半夜提早做饭,黑暗中传来嘀嘀哒哒的切菜声。为了尽可能避免扰邻生乱,武装警察总是谨慎行事,确保在天亮前悄悄提人,还得安排死囚“上路”前的一顿稍微吃得好点。这样,下半夜的监狱食堂总是让人不安,一有动静就让很多囚犯竖起双耳。一群鼹鼠捕捉风声时就是这样子。
我前面说过,我不太愿意想象这一个情境,不愿意说到这一个早晨。尽管两个故事之间有几分暗合,我说的夏如海却不应该也不至于这样倒霉。恰恰相反,几十年过去,他可能眼下还活得好好的,比如在某个工厂退了休,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老花镜,背着手的小驼背在街上闲逛,看老街坊下棋或打牌,跟在那些广场舞大妈们后面,耸肩撅臀地比划两下子。他身边应该有一条狗,有一个总是泡上浓茶的保温壶,还有夕阳里江面上一片灿烂的光波,南方深广无际的秋天。
很可能的是,他仍住在那条小巷,那个电线杆旁边的红墙小屋。大概是把一个地址住久了,习惯了,就不想离开了。儿子去年给他一沓票子,说什么年月了,把房子翻修一下吧,他也支支吾吾一直没动手。
夏小梅,事情是这样吗?夏小梅,如果你看到我这一篇文章,请理解我没有采用你和你家人的实名,但相信你不难从中读出熟悉的往事,不难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肯定没有忘记那一切。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障碍,你可以通过杂志编辑部联系我,告诉我你失联后的故事,告诉我你哥眼下或许就是我说的这样。
你是否还会继续保持沉默?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