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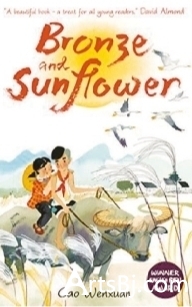


想一箭双雕地得罪两个人,莫过于此时提起郑渊洁。
在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与郑渊洁如两个路标,一个指向精英,一个指向草根。
论市场地位,郑渊洁是当然的胜者,虽然曹文轩也是“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甚至进过前十名,但与几乎每年位列前三的郑渊洁比,还是差了不少。而论文坛地位,曹文轩则遥遥领先,他的作品意境更幽远,思考更深邃,气质亦更华丽,相比之下,郑渊洁下笔却怎么也抹不去一股“山大王”的味道,倒也契合了“童话大王”的诨名。
不敢评价曹文轩与郑渊洁创作的优劣,只是觉得二者的割裂颇有趣味——本土读者更接纳郑渊洁,但“为国争光”时,还得靠曹文轩。这,恰好体现出当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向往天空,却又无法脱离脚下的土地。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参照西方文学标准建立起来的,几代作家所敬仰、所模仿的,都是西方经典文本,一提到文学的天空,总会不自觉地想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不言而喻,只有在他们之间,才能找到永恒。
甚至在鲁迅先生的心中,都存有这种焦虑,他的《故事新编》本是他最有才华的小说,可他自己却并不看重,因为从没有西方大师这么写,所以就是“油滑”,鲁迅不觉得趣味有多重要,也没发现以史笔来写小说是一种创造,而沿着这条路线,鲁迅本可写出更多的经典。
在相当时期,中国文学界为缺乏大作家、大作品而苦恼,可什么才叫“大”?无非是外国人承认、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罢了。早在民国时,赛珍珠便批评道:中国作家过分模仿西方,少有创造力。
并不是中国作家甘心做二手文章,而是现代小说源自西方,它的丰富、成熟与多样,远非传统中国小说所能匹敌,正因彼此审美品质差距过远,我们不能不以对方为参照系,而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传统,又显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功业。
于是,那片天空与本土的需求之间,出现了断裂。
现代中国遭遇种种危机,促使时代对文学提出更多、更现实的需要,一个作家在亡国灭种的风险面前,很难回归内心、深入反省,可失去了这个基本功,则其创作注定粗糙,只是掌声之下,又有多少人能拒绝绑架?
赢得大地,就失去天空,赢得天空,就失去大地。换言之,对生活真诚,就要损失对艺术的真诚,而对艺术真诚,就要损失对生活的真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谓杰出作品,多是二者妥协的产物。
可以具体对比郑渊洁和曹文轩的创作,他们都擅长写成长话题。
在郑渊洁笔下,成长充满了闹剧般的快感,以《驯兔记》为例,皮皮鲁上学了,班主任徐老师希望孩子们遵守纪律,成为好学生,可皮皮鲁却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好学生会变成一只兔子,在各方压力下,皮皮鲁只好订购“兔子模拟衣”混过难关。这显然是卡夫卡《变形记》的某种翻版。
郑渊洁对成人世界的残酷、虚伪充满警惕,自觉地充当着童年的守护者,对无处申诉的孩子们来说,显然更需要郑渊洁,因为郑渊洁能替他们发泄不满,能给他们以娱乐。
在曹文轩笔下,成长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曹文轩笔下的主角大多会遭遇天灾、屈辱、贫穷、歧视等,但这些负面因素竟会神奇地转化为正面因素——原来它们都是为了帮助主人公实现完善人格才存在的。曹文轩告诉读者:通过苦难,才能学会爱、勇敢与温情。在《草房子》中,桑桑甚至被放到一个更极端的背景中——大夫们预言他即将死去。
在曹文轩作品中,总有一个“姐姐”,她们出场,完全是为了帮助少年们获得成熟,且规避了将亲密关系复杂化的风险(显然,“妹妹”就肯定不行),在成功引起主角情感波澜后,她们立刻全身而退,善尽炮灰职责。
也许,面对生活,郑渊洁更真诚,他能写出孩子们的痛,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家长观念、学校教育尚不健全的当下,郑渊洁更能赢得掌声。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郑渊洁的文本便显得过于粗糙、幼稚,正如学者批评的那样:“非童话环节似乎成了漫骂的场所。”“他每逮着一点话柄,便出动脑中所有尖酸刻薄的词语骂个痛快,初看者尚觉俏皮讽刺,然而每一期都绞尽脑汁,倾尽墨汁地骂!骂!骂!骂!”
中国尚在发展中,我们所遭遇的困境未必普适,对常态社会的读者来说,很难理解郑渊洁的戾气,如果人家已经原创出《变形记》,又何必再来看你《驯兔记》式的“低仿”呢?
相比之下,曹文轩的文本形式更雕琢,堪称诗化写作,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翻出“鸽羽划过空气时发出的好听的声响”(《草房子》)、“害羞是一种让人激动又让人无法承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的心理状态。它忽然而来,如雷电的袭击,让你顿时低垂下脑袋,然后直觉得血液呼啦呼啦往脑袋上涌……”这样精彩的句子。
曹文轩的写作带有强烈的复古意味,其中隐含了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何其芳、汪曾祺等几代巨匠不断探索而形成的诗化小说传统,既是京派文学的延续,又得朦胧诗的风骨。这些作品可以被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读懂,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
通过诗意,曹文轩将挫折与成功、丑恶与美丽、凶残与善良统一了起来,这种对比鲜明的叙事策略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当然,这也容易让长年生活在灰色中的城市人,对乡村文明产生出不切实际的渴望。
在中国文学以世界文学为模本进行自我歪曲的同时,世界文学也在误读着中国文学,世界渴望看到另类的文本,曹文轩打造出一个纯美的文字世界,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诱人、更契合于他们的误会了。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但它反映的,注定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从郑渊洁的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图景,从曹文轩的镜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幅图景,毋宁说,两者都有其真实性,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个侧面。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