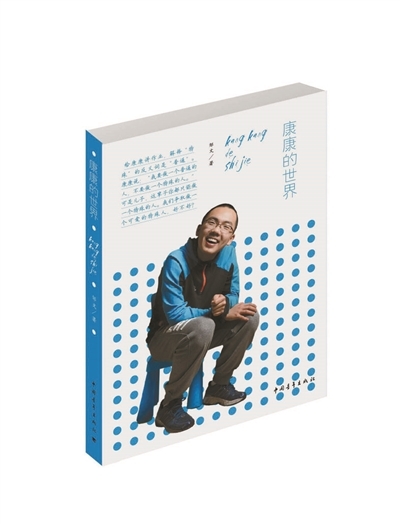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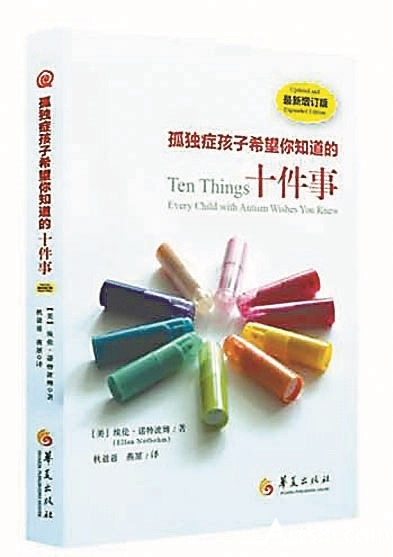
当主题日过时,新闻热点散去,在漫长的平凡岁月里,面对特殊人群的日常需求,我们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先跟随《云图》作者大卫·米切尔的文字想象一个场景:
“你现在无法和别人描述你饿了、累了或是痛了,也不能跟任何朋友诉苦;你毛衣上的衣物柔顺剂的味道,现在闻起来就像是对准鼻孔喷洒空气清新剂那样刺鼻;原先穿着很舒服的牛仔裤现在好像钢丝球一样扎人;而你的平衡感和本体感好像也失常了,地板就像巨浪中的小船一样,不断地东倒西歪……你甚至无法感知时间,对你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其实没有任何差别,你就像被埋葬在埃米莉·狄更生关于永恒的诗作之中,或被困在时间扭曲的科幻电影之中,无法逃离。不过诗歌或电影终有结束,而你却永远被困在现实中,自闭症将会伴随你终生。”
今天我们要谈谈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这是一个近年来被大众逐渐熟知的群体,从好莱坞名片《雨人》到几年前由文章和李连杰主演的《海洋天堂》,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让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家庭走入公众视线,并引发舆论热潮。但话题多了,难免会陷入空谈——因为天性驱使,我们只会关注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话题,很多时候仅在一些纪念日里为相关人群贡献一点发言而已。
2016年4月2日,第九个世界自闭症日。两本和自闭症相关的图书出版,又把这个话题拉入我们的视线。本期青阅读从这两本新书的现场出发,想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普通人应该如何与这些“星星的孩子”相处?而除了自闭症之外,还有哪些特殊精神残疾群体需要关注?在这个领域出版现状又如何?
这也许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但如果把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开一点,多去关注、了解他人的生活,也许“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距离与误解就会少一些,理解和交流就会多一些。当有一天我们在面对特殊群体,不会以“正常人”自称,而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时,平等这个议题将不会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了。
特殊的反义词不是正常,而是普通
4月的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里的一间小咖啡厅里,飘来曲奇饼干的香气。邹文和丈夫肖大林领着18岁的康康来到现场,参加《康康的世界》新书发布会。母亲邹文多半时间牵着康康的手,如果遇到好朋友,她会松开手,让康康和朋友们自如地聊天。
这是一个自闭症家庭在日常生活里温暖的一幕。如今,18岁的康康能和关心他的人交流,也是一家人与自闭症搏斗15年来的“战果”。这本书,正是记录了15年来父母帮助康康治疗、康复的点点滴滴。
全书由100组记录康康十几年来成长的“温暖的小事”作为主干,并配以20篇母亲邹文的“铭心记忆”等文章。“康康从小自闭症的状况比较严重,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从原来重度的情况到现在可以半自理,从不会说话到说话,其实过程是很漫长的,如果没有邹文这些细节的记录,这个过程就会不知不觉。”康康爸爸肖大林说。活动上,邹文拉着康康的手听大家念出这些文字,不时落泪。“出版这本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4月3日他18岁的生日,这么多年来我们家里一直在和自闭症战斗,虽然没有打败它,但是看到康康一点一点的进步,还有社会的关注,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康康妈妈说。她拿出一盒曲奇饼干递给记者,这是她所就职的康纳洲雨人烘焙坊制作的饼干,饼干的制作者正是自闭症人士,小小的饼干,是他们的劳动与尊严。
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的“正日子”。侨福芳草地的中信书店里,一本由日本自闭症人士东田直树所写的《我想飞进天空》新书首发式在此举行,这是一部由自闭症少年自己完成的书籍,作者东田直树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男孩,在5岁时被确诊患有重度自闭症。幸运的是,他学会通过键盘来交流。在《我想飞进天空》中,东田直树也以朴实的语言解释了自闭症孩子的所思所想,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虽然作者没有亲临现场,但主办方邀请到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电影《海洋天堂》原型人物田惠萍和她的儿子弢弢来到现场。
活动是以记录田惠萍生活的微电影《4月2日,我是田惠萍》开始的,此前拍摄组进入田惠萍的家,拍摄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一天的生活。她喜欢做饭,纪录片里,她给摄制组的人做了香喷喷的重庆小面。故事里当然还有弢弢——他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状态里,少言寡语,没有配合导演做什么。视频里的田惠萍讲了属于她自己的故事:比如她童年和知青父亲短暂的相聚,比如她喜欢旅行,收集世界各地的酒杯。电影在播放,观众席里田惠萍看得入神,弢弢趴在她腿上。有时候看到母亲在电影里笑得开怀,他会坐直,也笑一笑。
视频结束,新书发布正式开始,中信出版社经管社社长朱虹和大家分享了《我想飞进天空》这本书戳中她内心的东西:“很多人问他,东田直树你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吗?东田直树说,‘经过这么久,其实我已经不是很在意正常人的生活,因为究竟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难道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正常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当时戳中了我的内心。”朱虹感叹说,“这个少年能把生活想得那么透,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要努力追寻自己的幸福,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
轮到田惠萍发言,她和弢弢站起来,蓝色风衣盖住她的裙子,在藏蓝色高跟鞋的衬托下,纤瘦的小腿显得格外白皙。弢弢则穿了一件红色的T恤,上面写着数字“1/88”——那是美国一家协会送给他的礼物,“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自闭症的发病率,前年是八十八分之一,去年是六十八分之一。”田惠萍说。
她说自己格外喜欢这个影片——特别是题目《我是田惠萍》,“当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带着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弢弢在北京一间地下室里给留学时的好友写信,我说你们认识的田惠萍已经死了,从此我只有一个角色是弢弢的妈。”此后她创立“星星雨”,成了在自闭症未被广泛关注时家长们的互助组织,1996年前后,她的故事被广泛报道。
此后媒体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母亲:“媒体采访我,我把全部的人生讲给他们听,但是电视节目里只剪辑出我掉眼泪的镜头,最后把田惠萍渲染成悲壮的母亲在不幸中挣扎。可是生活不是这样的啊!生活有多种多样的调料,就像打一碗小面,不是只有痛苦。”她觉得媒体把她对生活的态度裁剪掉,其实是把她的社会责任扭曲了,“很多自闭症孩子的家长看到这些报道,会觉得原来那么漂亮的留学生因为这个孩子,生活彻底完了。在媒体人眼里,我只是弢弢的妈妈,但23年过去了,今天,我是田惠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有很多欲望,我对生活有很多向往。”
说话间,弢弢站在他旁边,低头专注看着地板,双手攥紧裤线。田惠萍停下来,问弢弢是不是累了,想不想坐一会儿,他看向身后空着的嘉宾座椅,坐下来,很舒服地松了一口气。
“他这样比较舒服,刚才那个椅子他觉得难受。”田惠萍说,“孩子是母亲生命里最重要的元素,他出了问题,这个挑战是无可比拟的。但我到现在都觉得弢弢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是我的全部,我还是田惠萍。”
直到最后,她才想起自己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为《我想飞进天空》作推荐,她很自然地望向主办方的方向,说了一声感谢,“这本书是自闭症人士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大家,自闭症是怎么回事。但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打字,而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带着支援的心态,和这些孩子在世界上共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找到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
之前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致辞,现场鲜有人发现话中有任何不妥,然而其中的“正常”二字显然戳痛了田惠萍。在诚挚的致谢之后,她将这个概念郑重地纠正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所有的人都有过正常化生活的权利,跟他本人是否正常无关。国际专业领域描述有障碍者群体,不管是聋人、残疾人、智障、自闭症……他们是有特殊需求的群体。他们有他们的特点,带来他们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为他们的需求做点事,而不是要求他们过正常的标准化的生活。”
如果身边有自闭症人士,我们应该如何做?
《康康的世界》新书首发结束后,康康一家人回到了家,妈妈邹文告诉记者,这几天累坏了。晚上9点了,她刚从康纳洲雨人烘焙坊回家,这是她工作的地方,也是为众多自闭症人士提供工作支持的地方,这几天她一直忙着给亲友寄书,接受采访,“今天一个记者来找我,她采访完离开,我还要把烘焙坊的工作做完。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还要带康康,他正在青春期,睡眠有些不好,我要尽快回复到生活原来的秩序中,康康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问题——公众除了在4月2日给予自闭症群体泄洪般的关注之外,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身边出现自闭症人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是用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可能确实和我们在行为上有一些差异,但不要把他们当成另类去怜悯,就把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就好了,正常地打招呼问好。如果他们没有提出需要帮助,就不必多做什么。如果他的监护人提出需求,再来帮助我们吧。”康康妈妈告诉记者。
而当记者在现场请田惠萍给大众一些如何和自闭症人士相处的建议时,本以为这是个不难的话题,结果没想到田惠萍的开场白是“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自闭症是社会交往的障碍,很多人在没有接触这个概念之前,都没有想过社交和视觉听觉一样可以失去。所以对于自闭症来说,没有简单的事。”田惠萍说:“你如果遇到身边有个人跟你不一样,不要去盯着他。很多家长的难处就在于别人用异样的目光围观,这是这个民族的惯性。我认为大众不需要知道什么是自闭症,但应该学习一种接纳性的心态,接纳不普通,接受和你不一样的人。”
记者也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蔡春猪——大多数读者在《爸爸爱喜禾》这本书里认识了他:蔡春猪用幽默的语言为他自闭症儿子的沉默写了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悲剧的漩涡。然而现实生活中,切实的困难会比书中的幽默来得实在得多。他说:“如果在公众场合,小孩的行为奇怪或者情况比较棘手,我提倡公众保持一种‘冷漠’——就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希望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没人管的地方,让我们独自处理好这件事。今天,社会上更多强调热情、帮忙和爱心,其实对于我们家人来讲,这种热情往往带有压迫。我的邻居做得很好,他其实知道我孩子的情况,但从来都不会问我什么。”蔡春猪补充说,“如果需要帮忙,我们会提出来的。”他最后义正词严地告诉记者:“我特别烦人家来问我,‘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千万别问我将来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办,你敢问我就跟你急。”
采访前一天,记者见到了刘娲,她的本职工作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稍后再谈。从小想当老师的她,从大学开始学习特殊教育专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很多自闭症儿童和家庭,她坚持做志愿者已经快20年,是真正能和许多自闭症家庭一起度过生活难关的伙伴。她的建议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想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到自闭症人士,一定要尊重他们的要求,这和与其他残障人士接触一样。举个例子,你看见一位盲人过马路,一定要先问,‘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而不是上来就把他拉走。”
第二点,是“己之所欲,勿施于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尽量不要去给他东西;当你不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个人的情况时,很礼貌地跟他打个招呼就好。”刘娲说。“我觉得大部分自闭症家长可能还是需要支持的,如果他们需要倾诉,我们能做的是倾听他们表达情绪。还有一点,如果你的邻居有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制造一些噪音,尽量去理解包容,体谅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痛苦。”
刘娲也提到了蔡春猪所说的“冷漠”,其实就是以对待普通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不是我要帮你做些什么,甚至是你在公众场合看到一个行为怪异举止怪异的孩子,不去关注他可能对他就是一种支持。”
除了自闭症,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
来给刘娲一个特写吧:华夏出版社特殊教育编辑部里,刘娲藏在堆成山的书里办公,书名里有一些离普通读者很远的专业名词: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她桌上一本字典有更多包括了临床诊断的名词解释,名叫《精神残障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些统称为精神残障,专业领域对其的定义是: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影响日常生活和活动参与的状况。
这里是国内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针对精神残疾领域有专业出版经验的部门,刘娲是这里的编辑,“所谓精神残障,离我们比较近的,最常见的就是抑郁症,还有一个潜藏在普通人群中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就是焦虑症。在小朋友当中比较常见的症状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就是ADHD。还有老年人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自闭症。”
“首先要说,我不太赞成用‘残疾’这个词,我更倾向于‘有特殊需要的’但中文的定语太长了,不像英文中表述的那样在字面上可以减少标签的作用。但官方文件里用的也都是‘残疾’,所以大家只能这么用。专业人士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残疾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刘娲说。
说到出版的传统,刘娲说,“华夏出版社隶属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从成立之初就在做康复医学和特殊教育,第一任社长邓朴方也希望我们能多为残疾人服务。”刘娲介绍说,出版集中在官方认定的几种类别里,“比如肢残、听力残疾、视力残疾,还有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
“我们做的书偏向于专业出版,我必须承认,国内这方面面向大众介绍这些病症的科普书非常少,但专业的就更少了。”刘娲介绍说。记者了解到,除了华夏社,湛庐文化“心视界”系列也出版面向大众的精神残疾科普书籍。
因为自己和自闭症打交道20多年,她所在的这个部门还是以出版自闭症相关专业书籍为主,已经出版的有《孤独症孩子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地板时光:如何帮助孤独症及相关障碍儿童沟通与思考》、《孤独的大脑》等几十种书籍,刘娲介绍说这其中包含几种类别,如:行为干预、研究方法、大师之作、教师指南、家长随笔、儿童读物等。她们希望有朝一日,不同病症的产品线都可以实现这些类目的细分。“专业领域的书,主要是给特殊人群看,在专业上我们一定会把关,就拿自闭症为例,不靠谱的干预方法我们一定不会做,等于害人。如有未经实证研究证明有效的,我们会很谨慎,不会出版。”
刘娲说,囿于国内起步较晚,目前的出版还是以引进图书为主,“90%以上的书都是引进的。国内本身专业研究人员就少,加上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翻译的作品不计入学术指标,所以找到合适的翻译也很困难。”不过,尽管很难,她还是引进了不少经典之作:“国际上比较好的作者是天宝(Temple Grandin),她是世界上很著名的自闭症人士,成年后情况有很大好转,现为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我们引进了她的系列图书,向家长和专业人士展示自闭症人士是如何思考和感知这个世界的。”
“相较于我们国家庞大的残疾人群来说,咱们为残疾人出版的书非常少,咱们国家官方的统计有8500万残疾人,这8500万残疾人背后就是8500万个家庭,而我们的康复医学、特殊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出版——这些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起步也非常晚,和发达国家有差距。”刘娲直面现实:“不说别的,美国亚马逊上的书目分类,有针对各种病症的图书细分,每个类别里都有很多书在打榜。所以,需要我们做的真的还有很多。”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