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天明
采访者:金涛
被访者:陆天明
为了参加新书《幸存者》的新闻发布会,陆天明特意理了发,效果却不尽理想,“太丑了,对不住大家”。之所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太看重《幸存者》,看重第一批读者对于《幸存者》的评价。“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新书扉页上,陆天明这样写道。他说:“如果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放在他棺材里的枕头书,那么我当时要写《幸存者》,不写完这一笔,我就闭不上眼睛。”两年零九个月的创作,陆天明说很累很累,头发比两年前又白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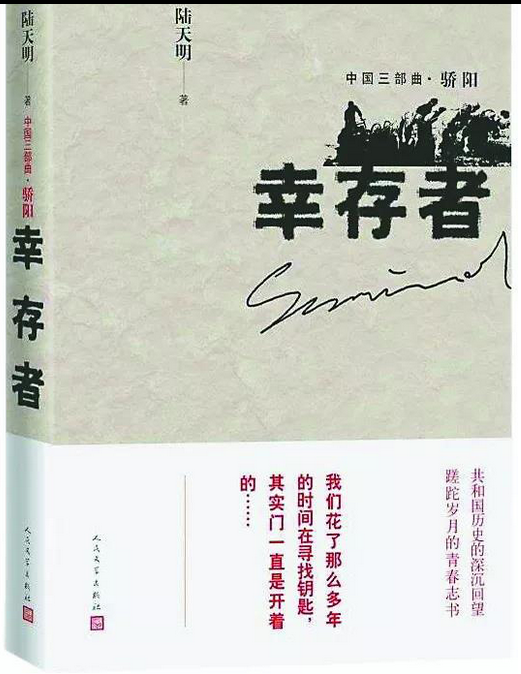
《幸存者》 陆天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作为《幸存者》的第一批读者,评论家贺绍俊看完后心潮澎湃。“为什么心潮澎湃?因为它唤醒了我很多少年的记忆。陆老师写的主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六十年代我正在上中学,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一部叫做《军垦赞歌》的纪录片,拍的就是上海青年到新疆支边。我们那些少年看了这部片子热血澎湃。我记得电影里有好多旋律非常优美的歌,至今都回荡在我的心中,顺口就能唱出来。看了电影,我们几个同班好友商量,我们应该爬火车去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还没钱买票,去和电影里面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一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在贺绍俊看来,《幸存者》记录下陆天明这代人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但是陆天明不仅仅停留在记录,而是在思考,“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丰沛的思想容量,巨大的思想冲击”。
为描绘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陆天明计划以“中国三部曲·骄阳”三部长篇的形式,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地的岁月里所经历的重大转折。因为主题鲜明、题材恢弘,该“三部曲”被列为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艺类图书。第一部《幸存者》近日出版,讲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内陆,来自大城市的支边知青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人接受时代感召,投身于新中国的边疆建设,不料却由于一场爆炸事件,命运发生突然转变……近日,就《幸存者》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专访了陆天明。

陆天明
三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最后浓缩到一本36万字的小说中
记者:为写这部小说,您积累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最后浓缩到一本36万字的小说中。这个创作过程和人们一般的想象很不同,作家往往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尤其是现在网络作家,一遍过的不在少数。
陆天明:我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创作习惯。其实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我没有创作提纲,但在创作之前会酝酿很长时间,大致的走向、意图、时代和历史的背景确定以后我就开始写了,这时有些人物的基调都还没定。为什么要这么做?改革开放后,作家写作要求尊重自我,尊重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受,而不是事前拟定一个主题。这样,一边写,一边形成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包括细节,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到什么程度呢?情节、细节自己往外蹦。比如小说最后钟绍灵自杀的情节,我写了两年多,一直到最后一个星期,这个细节才蹦出来,这个人物一定要死,而且是自杀。
记者:这些蹦出来的情节与细节,也不是您记忆中自己或朋友的经历,而纯粹是小说逻辑走到这一步?
陆天明:对。是自己产生的,不是我事先规定的,也不是生硬地按政治要求、社会要求虚构的。经验告诉我,产生这样的情节和细节,往往是创作中最华彩的部分,最鲜活的。这个时候也是我作为作者进入了一种最愉快、最舒服的创作境界。
第二个原因,因为这部书要写我们这一代人,要写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这是非常宏大的命题。怎么去表现?我想既要有我个人的感觉,同时又希望做到客观、科学、准确。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大论文,而且要通过文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论文母题”。虽然我已经写过那么多年,但要做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仍然非常艰难,需要不断攀爬,不断找路,不断摔倒再爬起来,反复琢磨,为了最后形成的这36万字,前前后后就写了三百多万字。
第三个原因,我写的是当代,要写的这些人物原型还活着,许多事情都还没结束。俗话说,画鬼容易画活人难。当代的人当代的事,要让当代的读者认可,要感动当代人,引起思索,这三点都很难做到。每一个当代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你的人物、情节做出接受与否的判断,要让所有看小说的人觉得你不是在胡扯。真实才会引起思考,这也是我写《幸存者》一个重要使命,不光是看故事、好玩、消遣一下就完了。
所以,预计半年写完的作品,我写了两年零九个月。当初预计这部小说,应该能比较顺畅地写出。因为此前我已经写了九部小说,也写过电影、电视剧、话剧剧本,写作上还比较老练,又是写我这代人的事情,怎么会拖那么长时间?顺便说一下,这部书里80%以上的细节和情节都是真实的,只是放在不同的人身上。还有一点,我一定要把小说写得好看。当然要深刻,要对得起历史,但无论如何要写得好看,我坚定不移地要为读者、为大众、为老百姓写小说。就是这些原因,让我翻来覆去“折腾”,陆续提炼出最后的三十多万字的完成稿。这三百万字都在前三分之一用到了,然后,路顺了,渠道挖成了,后面三分之二的文字自己就碰撞出来了。

年轻时的陆天明
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
记者:小说取名《幸存者》出于怎样的考虑?
陆天明:写这部作品我一直抱着写成一点算一点的想法,毕竟年龄摆在那儿。“幸存者”有多种解释,也有朋友质疑、担心。但后来我坚定用“幸存者”为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前,站在黄花岗72烈士墓园前,站在所有为强国梦而献身的那些先驱先烈们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呈现一代“幸存者”的命运和经历,无可非议。理所当然。在探讨这个重大主题时,我觉得要赶紧说、赶紧写,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前无古人,我想后也不可能有来者的经历。
记者:在您的第一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也有一个叫谢平的主人公,您说这是之前唯一一部有您影子的作品。后面几部长篇,尤其是《苍天在上》等影响非常大的几部反腐作品,里面并没有多少您的影子。两种类型的创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陆天明:非常不一样。我前面几部作品,尤其是反腐四部曲,社会影响还比较大,我在创作中也很真诚,但更多考虑的是社会认同,更清醒地知道我是在摹写社会,表现时代、他人。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我在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些年来,一些作家朋友不认可现在“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写作”的创作理念,觉得只要服务自己、表现自我就行了。但这是我重要的文学理念之一。文学要为社会服务,要介入社会。但《桑那高地的太阳》和《幸存者》等作品,我很明白是写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幸存者》。我这次给自己的写作要求是: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遵照一个标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大众。我要把我们这一代人表现好。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个“最后一代”的概念有争论。理想主义者还会有,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会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是空前的以追求无私为自己生存目标的一代人,这个过程中经历坎坷,做了奉献、牺牲,也有反省,给历史留下了一段很值得思考的宝贵的东西,我感觉这些就像焰火一样闪了一下夺目璀璨的光,迅速消逝了。这其中有多少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有多少哲学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摒弃的?值得后人考虑。几许艰辛踯躅,只能概括在“幸存者”这三个字里。前些年我在为自己一个文集写的序言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会有血流出来”,这依然是我对《幸存者》的期许。
记者:《幸存者》中也涉及到腐败问题,这似乎是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的主题?
陆天明:我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到北京的,我为什么要开始写反腐小说?了解我的人都说,天明,你其实没有变。我们这批城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放弃高考,注销上海户口,从大上海去到新疆,走工农结合的道路,当年这么做,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想到工农中间去,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到了农村和农场,看到一些蜕化变质,发现了毛泽东所担心的,包括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担心的一些干部的变化,脱离群众,腐败滋生,完全忘记初衷。我们看了后深有痛感。我调回到北京,写反腐,还是这个初衷。我的第一部反腐作品《苍天在上》,就是想呼唤苍天,中国你不能腐败。写这部戏,最初没有情节,没有人物,什么都没有,但题目有了,就是《苍天在上》。当时就想喊这么一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人民的春天来了,但腐败也来了。老百姓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这种情感一脉相承,也就是现在说的不忘初心,要把中国搞好,中国共产党不能丢掉初心。
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时代都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但都是人群中的少数?
陆天明: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1963年、1964年,上海第一批到新疆去的支边青年,报名三万,批准一万。许多青年都写了血书,坚定扎根边疆。有的家长把女孩关在楼上,不让出去。我们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那样,从楼上把被单系好,溜下来到街道报名去新疆。这不是个别的,很多都是这样热血沸腾过去的。这一批人,是典型的,但不能说代表全部。我通过这部小说,很想告诉大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也想让大家知道年轻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认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实现中国梦,不可能让所有年轻人都走这条路,但这里面的精神因子还是需要的。被认为有很多问题的“80后”,现在已经是各个岗位上的重要人物,什么道理?当历史和社会把担子压到每一代人身上后,他们一定会成长,会承担起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因为历史是往前走的。对年轻一代,我们永远抱有希望。
记者:小说中谢平和父亲的关系很打动读者。谢平和父亲关系的紧张,是否也是他去新疆的重要原因?在后面两部的写作中,谢平和下一代的关系,是否会是您考虑的一个重点?
陆天明:写父子关系是从塑造人物出发。每个人物有特定的生存环境。谢平去新疆主要是理想信仰,当然也和家庭有关系,想给家里减轻负担。我也是家里的老大,从小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我去新疆是为了革命,也想为家庭减轻负担。至于说到父子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父子关系往往最能够凸显时代的意义。父子矛盾冲突,不仅是生理上、心理上的,而且是时代的、文化的。这种矛盾,在两代人之间永远会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停滞了。三部曲后面还会写到谢平和他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他变成父亲后如何对待父子关系?如何看待父子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悬案,要重点写。通过父子关系写时代变迁,有文学意义,也有社会意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