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敬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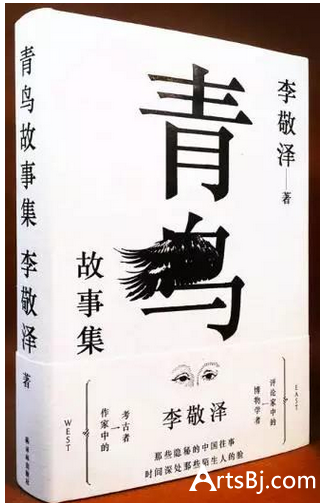
《青鸟故事集》,李敬泽着,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113.00元
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李敬泽
他曾经将自己想象为“一千零一夜”的见证者,注视着那些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倾听他们的讲述,写就《见证一千零一夜》;他曾经试图“为文学申辩”,他说,我并不是那个理想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我想探讨的是:我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于是在《致理想读者》中梳理了诸多关于文学的思考和表达。
现在,他寄情于李商隐和梅特林克的“青鸟”,在《青鸟故事集》里写下了对异质经验的感悟和奇异的历史镜像。貌似出手无招,却是以艺进道;貌似东拉西扯,却是渊博奥妙。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着名文学评论家。坊间流传多年的一个说法,文学青年进京三件事: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他在作家中影响之大窥斑见豹。
然而光环之外,他还是一个经常处于被逼稿状态中的纠结的写作者,一个既然要做就一定做好的摩羯男,一个把什么都搞“杂”了的文人。
在被定位为“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辩,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的《青鸟故事集》腰封上,李敬泽还是“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作家中的考古者”。
总觉得应该羽扇纶巾,或朱子深衣,才和他骨子里的追求相符;又觉得似乎他从来也没被俗世尘嚣打扰过,不然,何来那些风雅闲散、怡然自得的文章?何来时而与嘉靖年间人“话不投机”,时而又与大明王朝的外国囚犯盖略特“一见如故”?
他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谈笑自若,在时光隧道中穿梭自如,在古今中外辽阔无边的精神视野沉吟梦想。
更难得的是,他也让读者跟着他阅读侦探小说般追随到底,跟着他的奇想飞驰。
这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几乎称得上奢侈。
《青鸟故事集》写的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山海经》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飞到唐代成为信史,比如我们熟知的“蓬山此去多无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比如南唐李璟的《浣溪沙》中“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飞到现代,成了戴望舒《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记者:《青鸟故事集》被定位为“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辩,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
李敬泽:我不在意定位问题。要说是散文、随笔也可以,说它是非虚构,我也不敢保证里面没有虚构的成分。新文学以后,我们建构了一个文类传统,规定了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诗歌是什么样子,散文是什么样子——但中国传统中,最根本的是“文”。现在拿出《庄子》让你给他一个现代归类,你一定会抓狂:这是虚构吗?非虚构吗?是小说散文论文吗?都是都不是。这些事情,庄子不会想,他所写的只是“文”而已。
我不是拿自己和庄子相比,而是说,在新的互联网时代,或许将迎来古典的“文”的精神复兴。
2016年我在《十月》开专栏“会饮记”,包括几年前出版《小春秋》,经常有人较真,问我写的是什么体裁?用必须给个说法的目光盯着我。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散文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一百年来照着西方的文学体制定的,不是天经地义。为什么非要把一棵草药使劲塞进中药店柜子的抽屉里呢?
记者:阅读《青鸟故事集》,能感觉到您写作的快乐。
李敬泽:是这样的。文学文本除了意义还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不如直接写论文。首先是有意思,把意思写足了,意义自在其中。
记者:“十六年后,重读当日写下的那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仍写得出的。”看得出您很有自信。
李敬泽:这里面有一部分文字写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是不甚自觉的写作者,写下的这些文字中呈现的历史的、人性的面向,今天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突出、重要,更具现实的针对性。我确实觉得,这十几年来眼光、趣味以及文字的方向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比那时候写作的自觉性强一些。年轻的时候,有一点信马由缰的任性,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写得痛快。到一定岁数之后,对写法的思考,自觉性、方向感会强一些。
记者:十六年前的内容,现在看有何意义和价值?
李敬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认识伟大传统的丰富性。我们现在谈起中国文明容易把它简单化,实际上我们的伟大传统是一条浩瀚的大河,不知道容纳了多少涓涓细流,包括汉唐以来对异质经验的接受吸纳融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误解,同时也是好奇、是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在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文明、文化乃至不同的国家地域交往固然越发密切,但交往中的想象、偏见、错谬,不是减少了,而是更高概率地发生着。恰恰是“全球化”的时代,会形成很多习焉不察的误解和偏见,而且相当牢固。从汉唐到明清,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仍然经历着。这种误解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文学经验、文学题材。面对误解,表现误解,是达成理解的必要途径。
“我最好是做个无所事事的读者。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写。”李敬泽说,他从来没想过要写什么,也从来没有立志当小说家,或要精研小说搞评论、要成为学者。写作起步时,他已近而立之年。
记者:腰封上所概括的“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作家中的考古者”,准确吗?
李敬泽:从书本身来讲确有一种考古的趣味。什么叫考古?从学理上讲,福柯是运用了考古学方法;从实际上讲,考古是专门的特殊的学科,是通过古代有限的物质遗存推论和恢复古代的生活。这遗存和当时活生生的整体相比可能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不到,这是考古的根本境遇。对我来说这也是文学的思想方法和想象方法,是从有限的、也许是有把握的东西,去推论整体。像考古学者,也像侦探。比如福尔摩斯,他的侦探方法和考古方法一样,从有限的东西,比如从一个鞋印推断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经历和身份。
记者:您的评论是否也采用这样的方法?
李敬泽:自出道以来,我的评论文章被夸或被贬,都是说“李敬泽的文章不像评论”,或者说“李敬泽的评论文体独特”——我没有自觉地这么想过。可能在天性和趣味中包含着某种特点,在写作中表露出来而已。我愿意称之为庄子式的知识兴趣和写作态度。博杂的、滑翔的、想象的、思辨的,一方面是回到“文”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伟大传统不是死的传统,是在新媒体时代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传统。在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这个传统正重新获得生命力。
记者:您说博杂,这种博杂来处是哪里?是大学吗?
李敬泽:从一开始搞“杂”了。大家都说上世纪70年代是封闭的时代,从我个人来讲,反倒是比较幸福的。十岁以前我还在保定,每天除了疯玩,就只有一件事:看书。我母亲在出版单位工作,院里有一个封存的仓库,那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什么书都有。我就乱七八糟地没有目的地看,没有学业的压力,没有父母要求的压力。托尔斯泰、三岛由纪夫、范文澜、吕振羽等等,当然什么也看不懂,大部分是白看。我从一开始看书就养成了不太有路数的趣味。
后来考上大学,四年下来,课上得三心二意,书却看了不少。毕业后又一直做编辑,接触的一直很杂。总而言之,把学问搞“杂”了。
记者:在大学里就开始写作?写作是受谁的影响?
李敬泽:上世纪80年代,大学里都是指点江山的人物,很多人都是文学青年,我不是。诗也没写过。看到周围的同学在写诗,摇头晃脑的样子很奇怪。大学毕业我才二十岁,去《小说选刊》当编辑,根本没想写什么东西。
当然人的一生肯定不断在受一些影响。我很幸运,在工作中碰到的上级、同事都是杰出的人。很难讲得特别具体,实际上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正式写作起步很晚,1993年才开始硬着头皮写点东西。有人问在那之前,你干什么?我说,人生除了写作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吗?
我也不觉得早或晚有什么意义。早写或晚写,对写作者来说,一切都是不浪费的。有人说你在1993年才开始写,之前不是浪费了吗?我从来不认为是浪费。我对自己没有很强的写作规划。较大规模的写作行为,比如开专栏写整本书,都是被逼着写的。如果不被逼着恐怕不会写,看人写总比自己写幸福得多。但是如果被逼着,做就一定要做好。是典型的摩羯座性格吧。
记者:“被逼”着写作,是一种什么状态?
李敬泽:我的写作生涯伴随着被逼稿被催稿,对于和我合作的编辑来说几乎都是噩梦。去年在《当代》《十月》开专栏,马上付印了,写完发给编辑,还要一改再改。刊物出来要在微信推出了,仍然要改——总能发现表达不准确的地方,总认为可以更有力,更简练。幸亏我是摩羯座,虽然没有强大的动力,确定一件事之后还是蛮勤奋的。要做的事会尽我的全力。
任何上手的事,我都受不了凑合。特别是在文字上。这和我曾经从事的编辑工作有关。看到文字不审慎,逻辑混乱、表达不准确,我就受不了。一个写作者,对文字负责任,对自己的表达、对表达的意思负责任,是写作的基本伦理。提笔就该负责任。不是要求你的语言多么摇曳生姿,至少表达要清楚明白。孔子讲“辞达而已矣”,这个要求高吗?不高。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作家批评家中也有不少是辞不能达。
李敬泽说,自己有一个“好处”,就是成长得慢,什么事都慢半拍。真正开始写作是三十岁左右的事情,就连找到写作的自觉性,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作为评论家,他的批评精准生动,不但得到作家们的深切认同,在评论界也有良好的口碑。
记者:您的批评,往往能切中要害,也最被作家们认可。这其中有何妙诀?
李敬泽:不是我有什么高明,是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旨趣和学术志向。有些批评家对一部作品的批评,最终目标不是对作品的充分理解,而是从作品出发建构自己的理论,学术性和理论性更强。我不是这样的批评家,但我对他们满怀敬意。我自己更偏于感受,更有文人气。当然,也许批评家最好的境界是这两者兼而有之。
记者:看得出来,您的文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鲜活感性而且有一种文人的风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今天继承得似乎远远不够。您怎么看“传统”在批评中的影响和作用?
李敬泽:谈中国的文章之道,无论批评史还是文学史,大家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都是回到先秦,回到孔孟,回到老庄、《左传》《战国策》,再往下就是回到司马迁。为什么?因为他们确实有着巨大的原创性。同时,他们的力量在于混沌未开,像一片汪洋,后来的文章只能从里面取一勺。
我最近还看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先秦文章相比也差得很远。先秦那种汪洋恣肆、无所不包、看不出界限的气概,那种未经规训、未经分门别类的磅礴之势,那种充沛自然的生命状态,只能令今人望洋兴叹。这大概也是一千年来那么多的聪明人反复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的缘故。
2017年是新文学一百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体裁和门类,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建构。我们应该、也有可能重新从原初的“文”的精神那里获得新的力量和新的可能性。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