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一名党卫军医生,你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度过的:筛选运到的囚犯,送一部分人去毒气室;下令往毒气室投入精确的毒气量;通过孔眼观察人们的死状;签署死亡证明;从尸体上拔牙。“这个屠杀过程——从一开始到结束,均由医生领导。”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样回忆。
原本以拯救生命为天职的医生,是怎样发动大屠杀机器的?他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怎样败给了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一本叫《纳粹医生》的书回答了这个问题。2016年10月,它在中国出版,并登上了许多好书榜。它的出版30周年英文特别版也将在近日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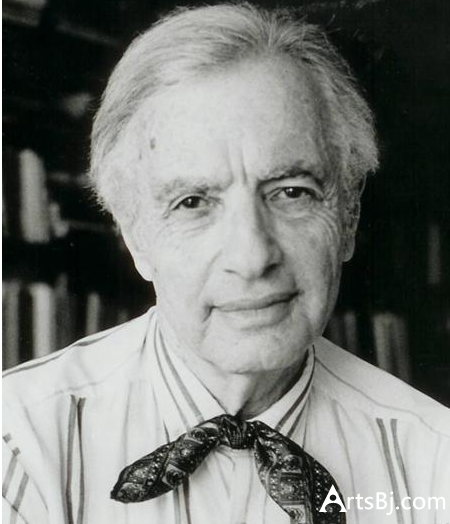
罗伯特·利夫顿
采访者:崔莹
被访者:罗伯特·利夫顿
《纳粹医生》的作者是现年90岁的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作为美国重要的心理史学实践者,他也研究过广岛核爆幸存者和越战老兵。在《纳粹医生》中,他对40个纳粹(其中包括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进行了访谈,并结合档案资料,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医生是如何心安理得地从治疗者变成凶手的。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纳粹种族歧视观念的起源与蔓延,特别是在医学领域的扩散。第二部分分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囚犯医生(多为犹太人)在筛选、毒气室屠杀全程监督、人体医学实验中的角色和彼此关系。第三部分探讨了种族灭绝的心理学。
围绕此书,12月14日,记者对人在纽约的罗伯特?利夫顿进行了电话采访。电话中的他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对书中内容记忆犹新。他还表示,自己仍在研究和写作,最近刚完成了一部新书,讲的是核武器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
以下为采访内容。
纳粹医生是关于专业人士从事屠杀的最极端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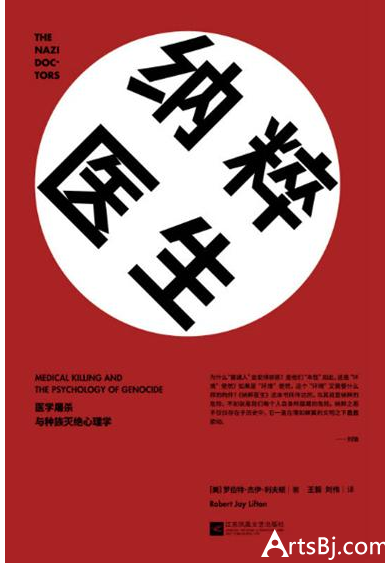
《纳粹医生》中文版
记者:在写《纳粹医生》前,你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是什么让你从研究他们转向研究纳粹医生?
罗伯特·利夫顿:大屠杀是我一直想研究的主题,但我感到大多数大屠杀研究研究的是幸存者,极少研究行凶者,尤其是行凶者的心理。但如果我们要避免未来发生类似事件,了解行凶者的心理就尤为重要。
当时关于大屠杀行凶者的研究文献很少,更没人采访他们。而我的研究方法,就是采访这些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医生。
记者:你提到,促使你写《纳粹医生》的直接原因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和奥斯维辛医学试验的材料。这些材料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罗伯特·利夫顿:这些材料来自我的编辑,当时他在编辑我关于广岛幸存者的书。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去,告诉我他有一些关于纳粹医生的庭审材料,特别是关于约瑟夫·门格勒的。这些材料让我非常吃惊,它们清晰证明:纳粹的一系列屠杀行为都是以生物医学愿景为基础的,医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后,我把“用屠杀来进行治疗”作为整本书的线索。
记者:为什么选择它为线索?
罗伯特·利夫顿:作为医生,我被同行将职责逆转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本应救治病人,却变成了屠夫。这种转变令人感到不安。自此,我对研究医生这个特殊群体的行为产生了兴趣。
我研究过越南战争中的精神病医师,但纳粹医生是关于专业人士从事屠杀的最极端例子。
记者:你是犹太人,这样的背景会影响你做有关纳粹医生的研究吗?
罗伯特·利夫顿:正因为是犹太人,我对大屠杀的感受深入骨髓。犹太背景促使我进一步做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尽力做到准确,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只有这样,我们对这类问题的了解才会更深刻。
采访时,只有一个纳粹医生嚎啕大哭

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记者:在对纳粹医生进行采访时,你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罗伯特·利夫顿:为挖掘出更多细节,在采访前,我做了大量准备。首先,我和支持我研究工作的德国同事紧密合作。正是这位德国同事,写信说服了大多数纳粹医生接受我的采访。其次,我尽可能多地了解要采访的纳粹医生,或者和他处境相似的纳粹医生的情况,比如他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他们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所以我对他们的回答也都有了思想准备。
他们说的话要比我想象中的多得多,但他们都竭力把自己和“行凶者”拉开距离。这种情况在采访时经常出现。纳粹医生向我回忆和讲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我把这种现象称作“精神分裂”。
记者: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鼓励他们多说?
罗伯特·利夫顿:当然。有各种情况。有些人很爱说,有些人说得少一些。他们在我面前展示的自己都身陷困境,没有其他选择,都已经尽力了。我才不会听他们这一套!
在大多数情况下,采访气氛比较紧张,他们能感觉到我的咄咄逼人。从我反反复复的追问中,他们明白我不并接受他们讲述的这个版本。然后我根据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继续问一些很细节的问题,追问他们当时到底做了什么。这样一来,我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采访资料。
记者:你问的都是什么样的细节问题?
罗伯特·利夫顿:比如说,很多纳粹医生把屠杀称为“安乐死”工程。实际上,他们屠杀的是患不治之症(通常是精神病人)的人或异见分子。对屠杀的整个过程,他们大都避而不谈。然后我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是谁打开了毒气阀门?”
我并没有直接指责他们,没有说“你们罪大恶极!”我只是追根究底,尖锐地提问。
记者:面对你的这些问题,纳粹医生的反应如何?
罗伯特·利夫顿: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不怎么讲话,有些轻描淡写过去。
只有一次,一个纳粹医生嚎啕大哭——在我的逼问下,他意识到他一直在拒绝面对这样的事实:自己曾经是刽子手。我就让他哭,他哭完了,我再继续采访。
记者:你对所有纳粹医生提相同的问题吗?
罗伯特·利夫顿: 我尽量问相同的主题,比如他们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后来是什么职位,被分配做什么工作,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对此有什么感受……
他们的回答为我的书稿提供了其他研究中少有的珍贵资料。
记者:怎么甄别他们是否说谎?
罗伯特·利夫顿:这也是为什么采访前的准备非常重要的原因。采访之前,我对他们可能说的内容已经有了大概了解。这些内容可以在不同的庭审档案中找到,我让我的助手对此仔细搜集和研究。所以,在采访之前我就知道他们都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即使不完全了解当时的细节,我也多少了解当时的情况,可以据此追问。在评估他们的话方面,我有主动权。
普通人是如何成为刽子手的?

纳粹疟疾实验受害者

约瑟夫·门格勒在进行人体医学实验
记者:在书中,你归纳了纳粹医生出现的诸多因素。在采访了这么多纳粹医生之后,你认为催生他们的一个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罗伯特·利夫顿: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我提出了“恶性的常态”(malignantnormality)的观点。希特勒和纳粹集团的核心人物建立了种族灭绝的机构,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原本是普通大众,后来加入了纳粹组织。他们不过是适应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常秩序,做了这个集中营需要他们做的事。
因此,催生纳粹医生的最重要因素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创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常态,医生被派到这里工作,最终适应了这里。他们可能最初会排斥,但是逐渐地,他们被社会化,成为杀人恶魔。
类似事件的发生通常要具备两个条件:极端思想、有破坏性的组织。
记者:你对纳粹医生的深层心理结构有着许多重要发现。在你自己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什么?
罗伯特·利夫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大多数纳粹医生并非法西斯主义者(约瑟夫·门格勒例外,他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不过是被社会化,成了屠杀流程的一分子。也就是说,普通人被卷入邪恶的制造机制后,也会变得邪恶。在我的研究中,这个研究成果令人感到极为不安。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医生在集中营每周工作5天,然后在周末回家,成为普通的父亲和丈夫,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转换。有时,我们不得不身处的环境和我们通常所处的正常环境可能是对立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坏事,有可能伤害他人,即使这违背我们一贯的原则和信念。
记者:书中详细描述了恩斯特·B、约瑟夫·门格勒和爱德华·维尔特这三类纳粹医生。在他们中,你认为哪一类的破坏性最大?
罗伯特·利夫顿:三类医生各具特点。门格勒最狂热,他是最直接的凶手。他研究双胞胎,为了获得病理报告,他直接让人处死他们。我认为破坏性最大的是门格勒这类医生。
爱德华·维尔特在成为暴躁的纳粹医生之前,曾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医师。他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被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这里的主管医生。他对纳粹绝对忠诚,领导创建了整部奥斯维辛医学杀人机器。因为不喜欢混乱,在他的领导下,屠杀更具系统化。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恩斯特·B是有争议的。他实际上救了很多人,并对他人充满善意。但同时,他是门格勒的好友,也从未抛弃纳粹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过和其他两类医生相比,他的破坏性较小。
记者:你说过,约瑟夫·门格勒是奥斯维辛的灵魂。如果他还活着、你有机会与他面对面,你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罗伯特·利夫顿:我不觉得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建设性的对话,但我想问和他的观点相关的问题。这些观点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也算是杰出的科学家。
另外,我想问他如何看待“你的研究令无数无辜者丧生”这个问题。我也会问他他的狂热意识形态和他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关系——我想了解狂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催生大屠杀的。
记者:如果把你作为囚犯医生置于奥斯维辛的环境中,你会表现得与他们不同吗?
罗伯特·利夫顿:没人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会如何。我觉得我会竭力阻止被社会化成恶魔,但我不能保证能做到。
当人变得邪恶时,他就不再是平庸的

1945年1月,奥斯维辛被解放时的幸存者
记者:《纳粹医生》出版后,外界有什么反应?
罗伯特·利夫顿: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得了好几个奖。我想,人们肯定了它对纳粹医生进行心理研究的角度和深度。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我和纳粹医生对话,觉得他们应该被谴责和隔离,不应该从他们那里汲取什么教训。
但我认为这是错的,因为知道了“普通人能通过社会化变得邪恶”,多少可以防止人们再犯类似的错误。
记者:你采访过的纳粹医生对它有什么反应?
罗伯特·利夫顿:我没有收到我采访过的纳粹医生对这本书的反馈。
记者:这本书是在整整30年前出版的。对于书中的研究结果,今天的你有哪些想补充的?
罗伯特·利夫顿:《纳粹医生》最近再版,我给它写了新的序言。在序言中,我强调了我刚才提到的“恶性的常态”的观点。我还回顾了世界不同地方存在的不同形式的严刑拷打事件,以及医生在严刑拷打中的角色。我对纳粹医生的研究也有助于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记者:你如何看待鲍曼发表于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罗伯特·利夫顿:大屠杀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但我不觉得它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表现。在现代社会,大屠杀是狂热的一种表现方式。
记者:书中也提及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理论。在你看来,这一理论存在什么缺点吗?
罗伯特·利夫顿:“平庸的恶”理论有一定的道理:简单而言,普通人也可以作恶。这也是一种社会化的邪恶,也可能会很官僚。
在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之上,我要补充的是,第一,人们要认识到,这个人可能很平庸,但他转变成的恶魔可能就不再是平庸的,而是很极端的;第二,当人变得邪恶时,他就不再是平庸的——他们具有了邪恶的特性。
记者:普通人可以通过社会化而变得邪恶。要防止自己走向这条道路,作为个体,需要怎么去做?
罗伯特·利夫顿:首先要知道这个现象的存在,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理解这一点后,人们就可以有抵制恶魔的依据。
当某种意识形态要攻击或声称有必要攻击其他人群时,要对此特别提防。几乎所有的大屠杀事件,都是以声称这样是必要的、光荣的为开端的。必须知道这是错的。因此,要防止社会化的邪恶,就要发现有建设性的、能改善生活的意识形态,将它们和有害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记者:在你看来,奥斯维辛还有可能重现吗?
罗伯特·利夫顿:我不能确定。希望我们能竭力防止类似的事件。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