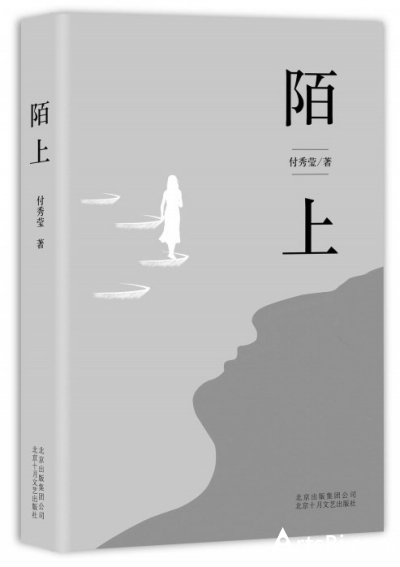
《陌上》,付秀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39.80元
采访者:舒晋瑜
被访者:付秀莹
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
在给付秀莹新作《陌上》所作序言中,曹文轩评价付秀莹是“一路风景”。的确,写作过程中不间断的风景描写,让阅读变得轻松愉快且富有情趣。
风景是付秀莹笔下芳村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芳村,风景几乎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她说,这世界从来不缺乏风景,是缺乏发现和欣赏风景的眼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景几乎消失了。实际上,风景描写不仅仅是调节阅读节奏,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文字质地的湿润、情趣的丰饶,意味的一言难尽。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付秀莹笔下的那些风景,跟那些人物一样,有呼吸有气息有情感有命运。他们都至关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在《陌上》里,付秀莹试图写出在大时代洪流中一个村庄的心事,一个村庄的命运。她幻想着,写出一个芳村,就写出了中国千万个村庄,就写出了乡土中国,写出了乡土中国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伏。“我不敢说《陌上》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初衷,但至少,在《陌上》里,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芳村的表情就是时代的表情;芳村的泪水,是时代脸庞上流下的泪水;芳村的微笑,也是时代嘴角的微笑。
记者:《陌上》叙事节奏缓慢细腻,是否有意要和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对抗?
付秀莹:贺绍俊老师曾写过一篇评论,叫做《短叙述,慢思维》,可能指的是我的叙事节奏,缓慢,不慌不忙。我倒不是有意要和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对抗。这样的叙事特点,还是因为我的审美理想。我想在“慢”里面,发现生活细部的肌理和暗藏的缝隙,发现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部分。好像是刘庆邦老师讲过一句话,意思是,好的小说,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我深以为然。我的理解是,自信的小说家,不是努力用故事去吸引读者,紧紧抓住读者不放,而是敢于把读者放开,给读者松绑,对他们听之任之,听任他们在小说中随时停下来,流连不去,反复品味。在审美的“格”上,这一种放人的小说,可能更高一些。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一本书很好,很吸引人,你急切地想看完,想一探究竟。还有一种情况,一本书很好,你舍不得一下子看完。你要省着看。后一种体验是我的小说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记者:总能在语言中寻到《红楼梦》的味道,在你的写作经验里,追求怎样的语言风格,是否确有这些经典的影响?
付秀莹:新浪好书榜推荐理由说,《陌上》是“乡村版大观园”,我把这个看做是很高的褒奖。《红楼梦》这样一部书放在那里,如果谁说不曾受到它的影响,一定是假话。但我觉得,《陌上》受《红楼梦》影响最深的,是日常经验的书写。《陌上》写的几乎都是日常,在日常经验之外,《陌上》试图拥有某种超越性,某种飞翔感,拥有超越世俗之上的某种审美视角,更宽阔,更辽远,更苍茫,有升腾而起的诗性。《红楼梦》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不仅有大观园,还有太虚幻境。那些人物不仅有今生,还有前世。在《陌上》里,我试图写出世道和人心,写出时间和空间的幽深和空茫。好的小说语言,彼此之间相互揖让,顾盼而有情。语言是有意味的形式。我深信这一点。
记者:看到乡村故事,非常亲切,有很多我熟悉的场景和语言,能把我迅速带入到乡村社会。但是,也有更多我不熟悉的东西——我想了解的是,作为写作者,你离开乡村也二十年左右了吧?你觉得对乡村的了解还那么深入吗?又如何准确把握这些现代乡村人的心理?
付秀莹:没错,我离开乡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对于乡村,我几乎毫无陌生感。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我依然认为,我的家在芳村,在华北平原那个小村庄。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我的根脉在芳村,芳村是我的精神故园。至今芳村生活着我的众多亲人,步入暮年的父亲,长眠在芳村泥土中的母亲,我同芳村的关系是血与肉的关系,永远无法割断。我太熟悉他们的疼痛,他们内心的波澜,他们琐碎的苦恼,他们卑微的梦想了。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的邻居,我的乡亲,甚至,他们就是我自己。
记者:感觉芳村女人们怀着万般委屈,好多处描写女人嘤嘤的哭泣,有些是有来由的,有些却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对笔下的这些女人,怀着怎样的感情?不知你如何看待女性写作?
付秀莹:芳村的女人们,每一个我都爱。素台,翠台,小鸾,春米,瓶子媳妇,望日莲……她们就是我的姐妹,她们甚至就是我自己。我说过,一个乡村妇人,她们内心经历的,一点都不比一个都市白领少。她们文化不高,但她们却深深领教了现代文明的厉害,她们也上网,玩微信,新媒体资讯铺天盖地,她们在劫难逃。她们见识的越多,痛苦和烦恼越多。因为,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深渊令人沮丧和绝望。与上一代相比,她们更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她们更难以在传统的秩序中安分守己。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如果真正走入她们内心,那些哭泣和眼泪,其实都是有来处的。如果真正品尝出了她们泪水的滋味,也就真正理解了中国乡村。
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其实是在对抗男性话语的背景中出现的。写作就是写作,其实也不必要强调女性写作,因为强调本身,可能就是另一种姿态。我的理解是,女性作家写女性,因为性别的原因,可能更有同情之心,更细腻,更体贴,更能够感同身受,更容易走入人物内心深处,走得更远,更能触摸到人物内心独特的幽微的暧昧不明的那一部分。女性作家观照世界的角度,也自有其敏感纤细处,往往能曲径通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者:能谈谈你的中篇创作吗?此前你的《爱情到处流传》被转载很多,《你认识何卿卿吗》《幸福的闪电》《旧院》等作品也颇具影响。你如何看待中短篇创作?
付秀莹:我写中短篇比较多,尤其是短篇。写短篇有很大的挑战性,它不容许你不犯错,也绝不给你改错的机会。对瞬时的专注度要求很高。激情,速度,力量,燃烧,一挥而就的快感,有着十分迷人的魅力。好的短篇小说中往往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区域,因为这种沉默,可能蕴藏着更大的喧哗。如果说短篇考验的是小说家的才情,长篇往往更多的是对小说家意志力的考验。很多作家,都是先从中短篇小说入手,慢慢磨砺自己,然后才开始长篇创作。
记者:从中篇到长篇,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是一种自然的厚积薄发,还是觉得是时候向文坛证明你的实力了?
付秀莹:也算是水到渠成吧。更重要的是,芳村这个小村庄,让我牵肠挂肚,日夜不得安宁。这是真正的情感牵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实生活如此复杂丰富,变动不居,我清楚其中的难度。但我想,写《陌上》不仅仅是出于膨胀的责任感,还因为,我想安顿躁动的自己,我想通过写《陌上》,尝试着重新理解我的芳村,理解我的亲人们。我想走入芳村的内心,我想找到回家的路。
事实上,很多很棒的小说家一生都没有写过长篇。比如鲁迅。但毕竟,长篇的气度,长篇的容量,长篇对人类生活经验的吐纳能力,是巨大的。当你发觉中短篇小说无法满足你要表达的欲望和野心的时候,写长篇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记者:在70后作家中的创作背景中,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价值?
付秀莹:70后这一批作家,大都受外国文学影响很深。谈到对自己有影响的人,几乎清一色是外国作家。在这样一种普遍的国际化焦虑中,我可能是比较沉得住气的那一类。我想,在众人都争先恐后国际化的时候,在大家都蜂拥奔向大世界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且慢,回头,向内转,转向我们的内心,转向我们自身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写中国故事,就是要在传统文化的浩瀚海洋中汲取养分,用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方式,写出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细节,写出大时代里中国人的隐秘的心事,写出真正的中国故事。在宽阔视野中获得自信力,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到价值,我以为可能是,这种对传统的热爱和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中国传统美学不懈的新的探索。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