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文学评论家王雪瑛在今年对作家韩少功的一个长篇访谈,因篇幅原因,澎湃新闻刊登其中的部分章节。在访谈中,作家韩少功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的写作,从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创作,回顾了自己的知青生涯到现在“山南水北”的乡村生活,也对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和当下思潮、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评价。
在访谈中,韩少功认为,“80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90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在他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韩少功
采访者:王雪瑛
被访者:韩少功
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盲区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你不仅以小说的形式拓展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空间,同时以散文的形式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前沿。这是你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慎重的选择?
韩:这样说吧,小说是一种“近观”方式,散文则相当于“远望”。这种“远望”比较方便处理一些散点化、大广角的材料,即不方便动用显微镜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看黄山就不一定合适吧?在另一方面,在文学与理论之间,有一个叫做文化随笔和思想随笔的结合部,方便一个人直接表达思考。我曾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心智成熟经常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肌肉扩张,有一种大娃娃现象。很多问题来得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等不起长效药,就得用速效药。思想随笔有时就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工具,好不好先用上再说。
王:你的散文写作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小说与散文不光是两种体裁,而且常常承载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说的虚构是一条,是否直接表达思想也是一条。此外可能还有其它,比如慎于判断和勇于判断的态度差异。一般来说,小说模拟生活原态,尊重生活的多义性,作者的价值判断经常是悬置的,至少是隐蔽的。比如安娜·卡列琳娜怎么样,林黛玉或薛宝钗怎么样,由读者去见仁见智好了,作者最好站远一点,给读者留下自由判断的空间。但散文不一样,特别是思想随笔需要明晰,有逻辑和知识的强大力量。伏尔泰、鲁迅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模糊。在这里,模糊和明晰,自疑和自信,是人类认识前进所需要的两条腿。但两种态度有时候脑子里打架,怎么办?我的体会是要善于“换频道”,把相互的干扰最小化。一旦进入这个频道,就要把那个频道统统忘掉,决不留恋。
王:在《进步的回退》中,你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了你的一部重要的充满感性的散文长卷《山南水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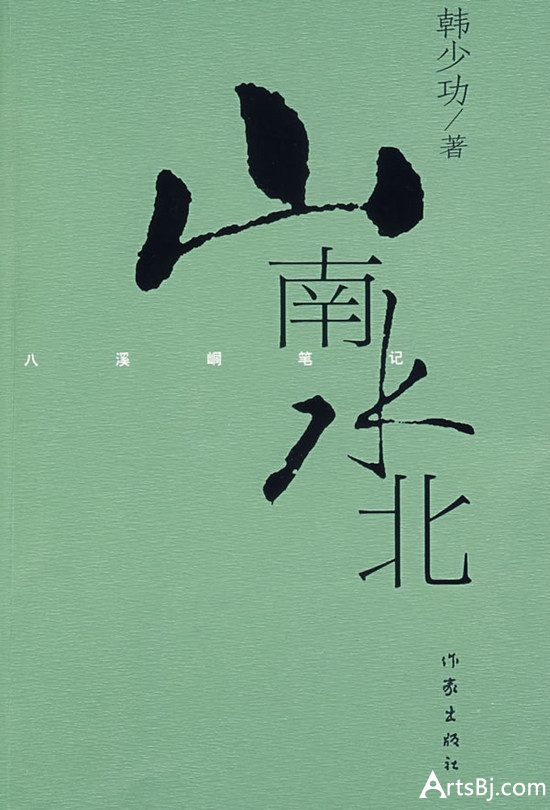
《山南水北》 韩少功 著
韩:以前恋爱靠唱山歌,现在恋爱可能传视频。以前杀人用石头,现在杀人可能用无人机……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变化,但变中有不变,我们不必被“现代”“后现代”一类说法弄得手忙脚乱,好像哪趟车没赶上就完蛋了。事实上,经济和技术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就道德和智慧而言,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牛皮可吹。这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常有的盲区,恰好也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在《山南水北》中,你以生动质朴的语言记叙了你的乡村生活。你怎么看待自己现在的乡村生活经验?
韩:我在那时已住过十六个半年。最初只是想躲开都市里的一些应酬、会议、垃圾信息,后来意外发现也有亲近自然、了解底层的好处。说实话,眼下文坛氛围不是很健康的,特别是一个利益化、封闭化的文坛江湖更是这样。总是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泡,你说的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
相反,圈子外的农民、生意人、基层干部倒可以让你知道更多新鲜事。这里的个人原因是,我从来就有点“宅”,不太喜欢热闹,经常想起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每当我从人多的地方回来,就觉得自己大不如以前了。
王:面对那些“回避现实”的疑问,你写了99篇文章,23万字,让大家感受到了你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山里人的日子。你当时开始动笔的时候有整体构想吗?
韩:没有。很多章节不过是日记,后来稍加剪裁,有了这一本。当然,我从不认为这里就是现实的全部,但这种现场感受至少是现实的一部分,比某些名流显贵那里的“现实”更重要,比某些流行媒体东抄西抄嚼来嚼去的二手“现实”可能更可靠。中国一大半国土是乡村,至少一半人口是村民,这些明明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被排除在“现实”之外?
王:《山南水北》是你对思想和理念的一种感性的实践和体悟,是你个人对现代化的一种自由选择,一种个性化的文学表达。从此书出版至今9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山南水北》对你的意义?
韩:怀疑和批判永远都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必须成天活得怒气冲冲,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思想文化而言,18世纪以来不论左派右派都是造反成癖,反倒最后是易破难立,有破无立,遍地废墟,人们生活中的自杀、毒品、犯罪、精神病却频频高发,价值虚无主义困扰全世界。文学需要杀伤力,也得有建设性,而且批判的动力来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是对美好的信仰,对美好一砖一瓦的建设。缺了这一条,缺了这一种温暖的思想底色,事情就不过是以暴易暴。用廉价的骂倒一切来给自己减压,好像别人都坏透了顶,那么自己学坏也就有了理由。这是一种明骂暗赞的隐秘心理。《日夜书》里有一句话:“最大的战胜是不像对方,是与对方不一样。”就是针对这一点说的。
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呈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韩:就文化演进而言,趋同化和趋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全球化不过是这两个轮子的古老故事,从村庄级上升为全球级,单元边界扩大而已。人都要吃饭,这是普适性。但什么饭好吃,人们的不同的口味受制于各种条件和相关历史,就有了多样性,其中包括民族性。我曾经以为舞蹈是最不需要翻译的,最普适性的,后来才知道肢体语言也有深刻的族群差异,我的语汇你可能无感,你的语法我可能不懂。舞蹈尚且如此,运用民族文字的文学怎么可能完全“一体化”?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如果有的话,肯定是趋同化与趋异化在更高层面上重新交织,决不是拉平扯齐、越长越相像。否则,那个同质化世界一定乏味透顶,失去成长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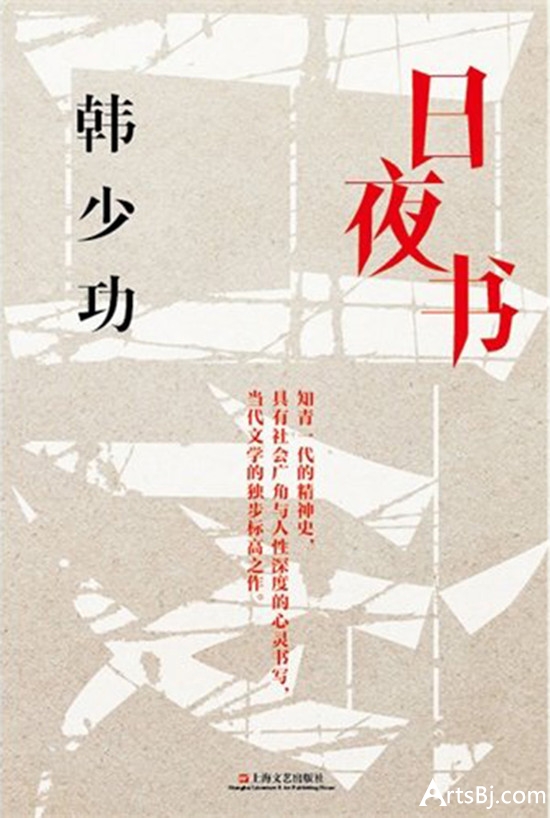
《日夜书》 韩少功 著
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东西
王:《日夜书》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这是你的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描摹知青这一代,来审视和思索自己的人生。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
韩:有些书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志在卓越。有些书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意在解脱和释放。《日夜书》大概属于后一种。这本书写作耗时一年多,触动了一些亲历性感受,算是自己写得最有痛感的一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淡出历史。我对他们——或者说我们——充满同情,但不想牵就某种自恋倾向,夸张地去秀苦情,或者秀豪情。我把他们放在后续历史中来检验,这样他们的长和短才展现得更清晰。由这一代人承重的时代,为何一面是生龙活虎而另一面是危机频现,才有了一个可靠的解释线索。“中国故事”难讲,最难讲的一层在于人和人性。没有这一层,上面的故事就是空中楼阁。“苦情”和“豪情”宣示虽不无现实依据,但容易把事情简单化,比如把板子统统打向别人,遮挡了自我审视。我的意思是,每一代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恋,但我希望这一代人比自恋做得更多。
王:我觉得《日夜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摆脱了自恋,也摆脱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套路,而是真正地以小说的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回望和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回避卑微,不回避平淡,不回避内心的纠结。
韩:郭又军是个仁义大哥,但他曾经把“大锅饭”吃得很香,结果误了自己。贺亦民在技术上是个超强大脑,但他对社会不无智障,江湖化的风格一再惹下麻烦。马涛有忧国忧民的精英大志,但从自恋通向自闭,最后只能靠受迫害幻想症来维持自信……他们该不该把这一切的责任推给社会?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人性弱点,他们的奋争是否才会更真实、更艰难、也更让人感叹?相关的历史描述是否才更值得信任?
王:你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中,你似乎收敛了思想的锋芒,而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带出往日的一段段经历,那些物质贫乏,精神亢奋的日子,同样通过人物来连接往日与今日之间那巨大的沟壑,在往日和今日,现实与记忆中塑造出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勾勒出人物在时代的风云起伏变幻中形成的命运,而不是想做什么定义和结论。
韩:写人物,当然是小说的硬道理。我们可能已经记不清楚《水浒传》或《红楼梦》里的很多具体情节,但那些鲜活人物忘不了,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一点东西。《日夜书》是留给自己的一个备忘录。写谁和不写谁,重点写什么,肯定受制于作者的思想剪裁,但我尽量写出欧洲批评家们说的“圆整人物”,即多面体的人物,避免标签化。有人说,这会不会造成一种价值判断的模糊?问题是,如果只有面对一堆标签才有判断能力,才不会模糊,那也太弱智了。
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正是要关切自我
王: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冲破十年极左思想的禁锢后,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许多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你的文学创作了贯穿了当代文学发展的30年,你对文学思潮,小说的创作手法有过怎样的思考?
韩:作家多种多样,该各就其位,各走各路。所以人家多做的我会尽量少做;人家少做的我却不妨一试。我很愿意尝试形式感,包括对报表、词典、家谱、应用文乃至印刷空白动动脑筋,包括对新闻或神话打打主意,但我也相信任何文体、风格、技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一旦写作人热衷于拼产能、拼规模,生活感受资源跟不上,眼下超现实也好,新古典也好,装神弄鬼的水货其实都太多。好的形式感,应该是从特定生活感受中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有根据、有道理、有特定意蕴的。你说很多作家“回归”,可能是大家对搞怪比赛开始厌倦,去掉一些高难动作,回到了日常形态。当然,这不意味着形式实验到此止步。不会,将来还会有奇思妙想,真正的先锋说来就会来。
王:当代中国文学中,先锋文学首先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形式探索,也是一种文学的精神和理念的探索,你是不是认为先锋的理念和精神也贯穿在作家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吴亮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先锋的艺术只能由先锋的哲学精神来识破和鉴别。你对此怎么看?
韩:吴亮的说法没错。好的形式感一定是有哲学能量的,是人类精神突变的美学表现。广义的超现实主义曾经就是这样,当人类的微观和宏观手段都大大拓展,肉眼所及的日常“现实”就必然被怀疑、被改写、被重构。这不是文学技巧的问题,是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重新确定,认知伦理的破旧立新。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幕后通常都有科学、宗教、哲学、社会的大事件在发生和推动。
王:目前应该是你写作的黄金时期,你在写作中有什么困惑吗?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你来说,目前写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随着感受、经验、技能等各方面的消耗,自我挑战和超越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写作是一个缘聚则生的过程,有时候一、二、三、四的条件都有了,就缺一个五,作品也成不了。缺半个四,你也成不了。作家也可以敷衍成篇,维持生产规模,但那是骗自己。
王: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社会历史是“传统”文学,个人内心、无意识、意识流、现代主义才是“现代”小说,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韩: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焦点,病不一样,药方就不会一样。这没什么奇怪。但“传统”和“现代”的两分法太简单了,“自我”和“社会”也不是什么对撕的两方。自我当然很重要,但抽象化、极端化的自我就是新的神话。眼下好多流行作品,狗血得大同小异,矫情得大同小异,“自我”们狂欢的结果却是千篇一律。其实,没有土壤,就没有树苗的“自我”。没有锤子,钉子的“自我”也是个笑话。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其实正是要关切自我,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高深。
王: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用这样一组关键词来分别描述八十和九十年代:激情、浪漫、理想主义、人文、迟到的青春属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则步入现实、喧嚣、利益、大众、个人……你的创作贯穿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你对80年代与90年代有着怎样的看法?
韩:大体来说吧,80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90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问题在于,差异双方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怀念单纯,包括能比对出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世故了。人们滑向世故,恰恰是因为以前过于单纯了,或者说以前那种“单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抗压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以前的清教禁欲,就不会有后来猛烈的利益化和物质化;没有以前的极左,就不会有后来的极右……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骗子是受骗者的产物。这里的道理是:要看到你中之我。
1990年代至少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二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王雪瑛系《文学报》副主编、文学评论家。)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