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米塔夫·高希
被访者:阿米塔夫·高希
采访者: 冯婧
“如果有茶,那我肯定是喝茶呀。”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熟练地给自己斟上一杯。
每天早晨沏一壶绿茶,边喝边听粤语磁带,这是高希创作“朱鹭号”三部曲时的惯常状态。除了爱喝茶,从小就常吃中国炒面,年轻时还曾迷恋《卧虎藏龙》……我们有些讶异于中国流行文化在印度的如此普及,但更多宏大而隐秘的关联却被中印两国共同遗忘了——千年前,曾就佛法对答、往来辩难的两个文明古国,却在1962年时面对边境问题面面相觑,中印政府都发现自己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一无所知。
高希于是想到了鸦片战争。19世纪,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开始大面积地种植罂粟,以鸦片为引的硝烟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却不知道在虎门升腾起的黑色烟云里,有90%都来自印度。
他搭建了一条十九世纪早期往来于中印之间的黑桅货船,来从事鸦片贸易的行当:朱鹭号上混居着印度人、孟加拉人、英国人、美国人各色人等,满载着梦想、痛苦和希望,就此奔赴着相互关联的未知命运。这是真正的同舟共济,印度文化中有着天然的多元主义,“印度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度之一,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去加入伊斯兰国。我想,这是因为在印度,来自不同社群、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都生活在一起,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以自由贸易为名义,以坚船利炮为保障,叩开广州十三行的两大利器,后来又在阿拉伯半岛故技重施。而鸦片战争对中国和印度最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才袒露出狰狞的原貌。
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和印度都被猝然抛入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经历了贫穷、战争和屈辱,我们都太想和西方看齐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观看方式完全被西方同化。高希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鸦片战争才在中国和印度真正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前,我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抵制伴随资本主义入侵而来的“自由贸易”,而现在,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渴望成为下一个美国。
无论是北京面目模糊的高楼大厦,还是印度随处可见的低头玩手机的少年,都证实了西方通过战争所播种的消费主义观念本身就代表着绝对的不平等,“我们的地球不可能允许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享受同样的生活方式”。但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或者来自圣雄甘地的警告都被抛诸脑后,我们早已丧失了从古老传统中汲取定力的能力,随波逐流、身不由己,“我们的世界不会好了”。

高希
谈及这些,酷爱纸质书写的老派写作者高希显然有些情绪低落。他掏出手机看时间,发现又错过了妻子的电话,一脸茫然地问,“你知道这个苹果手机怎么解除静音吗?”
即使我们可以轻易操纵消费主义的神圣图腾——iphone噤声或鸣响,却无法阻止全世界对它的执迷,“中印两国的年轻人完全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奴仆,他们效忠物欲,总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更多。我对欧美的年轻人更有信心,他们面临着经济的崩溃和生态的崩溃,比我们更能直接地感受到问题的本质。”
而就在今夜,双十一狂欢节即将开启,势必又将造就“大把大把的吃土青年”……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城市的个性在流失,看上去和西方差不多
记者:这次来中国,感觉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高希:是的,过去几年我曾经多次来到中国,中国之行的确是很有趣又很激动人心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探索发现新世界的过程。
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那一次真的是很让人兴奋——我去了广州,阅读这座城市和广东四周的一些区域,广州真的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地方。几年过去了,广州当然也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也不光是广州,还有黄埔,这些地方都和过去大相径庭。
但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有些地方从来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比如你去杭州,在西子湖畔漫步,你会发现时光是静止的,无垠的——那一刻你才懂得什么叫做永恒。广州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老寺院,你也能体会到这种无边无际的永恒之感。广东城内有两三处古老的寺院,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些寺院周围有一些小小的店铺,还有一些做斋饭的小馆子,一些茶馆,这真的是广州格外有魅力的一部分。在广州城内四处走走看看、打发时光的确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
记者:那么,您提到的广州城内发生了变化巨大,指的是哪一部分呢?
高希:其实我认为,我真真正正走访过的那一部分广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些真正的广州老城区,十几年来几乎保持原样。
真正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地方是成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都就看上去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而我第一次去成都也不过是2010年而已。今年我再去看成都,已经物是人非,当然了,也有可能我去的那些地方正好是改变最大的地方吧。
记者:看到成都的这种变化,会不会感觉个性的消失,和其他城市的同质化之类。
高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参观过很多中国城市,它们看上去真的和西方城市差不多。尤其是当你去市中心走一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的确很像西方的大都市。很多时候,你真的不能分辨自己到底是身处上海还是成都、广州亦或北京,这些城市的外貌愈来愈趋同。对于北京来说,城市的特征之一恐怕是马路更宽阔——没错,气势磅礴的高架桥,规模宏大的机动车道之类。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些城市的个性特征的确正在流失,成都对我的打击就很大。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生机勃勃,个性十足的城市,可是现在完全变了。
不过这些观察都是很表面的,很宏观的。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大城市中现在还有一些被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区域。前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吃晚饭,她住在北京市中心很老很老的城中村里(恐怕高希不太懂得城中村和胡同的区别)。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城市的个性和风骨。那些青砖碧瓦,那些细小的胡同,住在那里的主要是移民,而几步之外就是高大巍峨的现代建筑,可是在“城中村”的内部,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记者:您说的“城中村”,指的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类似贫民窟的聚集区吧?不过说起来,印度的贫民窟文化也很典型,还是想听您聊一下无论是在印度还是中国,人群或者阶级的分化。
高希:我觉得,在中国,阶级之间的差异还不如省份之间的差异明显。当然,你会注意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因为那些民工都是来自北京之外的其他省份。所以我前天去拜访我的朋友,我朋友的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四合院,在那附近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民工,住在四周非常袖珍的小房子里。那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我不觉得那是一个“贫民窟”,它看上去也不像一个贫民窟,只是很有烟火气。
甚至在印度,贫民窟也是一个经常被污名化的地方。人们对所谓的“贫民窟”的理解是有错误的。在孟买就有一些被称为贫民窟的地方,没错,那些地方的确很拥挤,可是它们也很有生产力,那里有很多的小型工厂,事实上,孟买非常大一部分的工业产出是在这些小小的贫民窟中实现的,而居住在这些所谓的“贫民窟”中的人们往往非常富裕。孟买的情况和北京非常相似,因为那些贫民窟中住的人大部分都是民工,也就是说来自印度其他州的人。
中印在流行文化上非常熟悉,深层互不关心是因为都想向西方看齐
记者: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之间会有一种“互不了解”、“互不关心”的情绪在呢?
高希:没错,这的确是一个让我很困扰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问题,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中国人和印度人,我们对彼此也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点真的让人很费解.我们中印两国之间有着长长的边境线,有着那么多彼此往来的历史,还有那么多深远的相互影响,比如佛教,还有很多文化方面的、观念方面的往来。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几乎不可能理解的状态——我们两国之间,怎么就会产生一道如此巨大的鸿沟天堑?
但是,从好的一面说,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中国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专注于研究或者书写印度,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年轻人正在研究中国。每一次我踏上前往中国的飞机,都能看到很多来自印度去中国求学的年轻留学生。我也真的很希望,这些年轻人将带来真正的改变。当然了,虽然我们现在在说中印两国之间彼此如何不感兴趣,还是有一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方面——比如现在在印度,最受欢迎的食物居然是中餐,虽然是印度式的中餐吧,但也是中餐啊。
记者:中餐在印度很流行?
高希:太多啦。在印度,不管你去哪条街角,你总能看见有些馆子在做中式的面条。炒面简直成了印度人的首选食物——我小的时候,“下馆子”往往就意味着去中餐馆。
电影也一样,印度电影有段时间在中国很受欢迎,而中国的电影,尤其是功夫类、历史类的,比如《卧虎藏龙》在印度真的是家喻户晓。这种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彼此影响,还是广泛存在的,这一点也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其实在我还小的时候,十几二十岁吧,去看一场功夫电影真的是非常了不得的梦想呢。
记者:您是说70年代吗?
高希:七八十年代吧。所以,在流行文化的层面上,我认为中印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
记者:但是在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上,中印交流或者说彼此的“好奇心”就少了很多。
高希:是的,很可悲,在中印两国历史的层面上,我们对彼此基本没有什么好奇心,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学了大量的英国历史、欧洲历史、美国历史,可是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没有人教给我们,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从殖民时代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印度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我们的视线都是向西方看齐的。而当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看的也是西方,而并不是亚洲。因为中国当时的目标也是要赶超英美。
记者:鸦片战争是他们第一次发生以西方为中介的联结吗?
高希:不不不,完全不是。我们翻开历史,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我认为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得到学者和大众的关注和研究,那就是乾隆时期对尼泊尔的军事输出。
在179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派遣了一支军队,由一位钦差将军领导,前往尼泊尔驻扎(即廓尔喀之役,尼泊尔发动的一场入侵中国西藏的战争)。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这的确是打开了一系列的窗户,让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在那之后,1795年,英国人进攻了尼泊尔。不过他们一直都没有能够得逞,因为那个时候尼泊尔正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吗?不过你知道吗,乾隆皇帝还真的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才华横溢,很与众不同。他当时和印度很多国王都有书信往来,而且还真的有一些印度的国王试图和他建立联盟关系。我们必须要谈到喜马拉雅山脉了,没错,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屏障,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中间地带,通过喜马拉雅,中国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联系。正是乾隆皇帝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中亚。很遗憾的是,之前中印双方的历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但是现在,随着中印之间的研究和联系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有趣的知识点。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同样也基本没有人知道,那就是在英国侵略尼泊尔之后,中国的将军带了一些尼泊尔人回到了北京,而这些生活在北京的尼泊尔人就成了中国连接南亚地区的纽带。所以,通过这些尼泊尔人,中国人了解了很多南亚方面的信息。更有趣的是,鸦片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这些尼泊尔人其实已经警告过清朝了,说英国人就要来打你们了。这些尼泊尔人声称,唯一能够避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的方法,就是中国资助尼泊尔,然后尼泊尔出面和英国交火。如果当时清朝真的这么做了的话,可能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吧!然而,历史没有假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是从孟买出发,从海上打过来的。但是其实孟买和尼泊尔距离很近,它们是接壤的。所以那些尼泊尔人会建议从尼泊尔进攻孟买,这相当于从后方突袭英军老巢。但是可惜的是,清朝的皇帝拒绝了这个建议。现在回头看看,这的确是能够阻止鸦片战争爆发的唯一方法。
记者:拒绝是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感?
高希:其实,长久以来,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他们是绝对不会和另外的国家结盟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大吧。或者也可以说,是因为一叶障目、敝帚自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太浅薄了。
记者:可是鸦片战争还是发生了,而且它给亚洲格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希: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设。如果清朝当年真的资助了尼泊尔攻打英属印度,那么整个亚洲的历史可能都要重写了。因为尼泊尔人都是很骁勇善战的,如果他们得到了支持和资助,一定会击败在孟买的英国人。他们也许还会在印度的北部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尼泊尔的国土会扩张得非常非常快。
鸦片战争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彻底取得了对中印的胜利
记者: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再看,这场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高希: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了,而且就像书里白纸黑字写得那样爆发了。它驱使中国和印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西方社会——也就是英国——建立起来的。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依然在为此支付着沉重的代价。
比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后遗症。在19时期初期的时候,英国人从中亚开始向各个方向发起侵略,一部分是针对俄罗斯的侵略,还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侵略。这就是英国人所谓的“大博弈”。但是印度方面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英国人在中亚地区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告诉印度人,因为这是高度机密。英国人之前和清政府的谈判、和早期共和党人的谈判,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但是印度人从来没有参与到这些对话中来。所以当印度最终独立的时候,印度领导人发现自己有好多的问题要和周边的国家协商解决,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所以1962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都发现自己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一无所知,边界问题的确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可是当时两个政府都不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所以你会看到,在这种政府治理的连续性被打破的情况下,你不得不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政府,而这个新政府和之前的政府的确没有什么交集和传承,我所谓的“代价”,就是指这种连续性被打破之后的一系列后果。而在这种断裂带来的,则是一整个惶惶无知的真空地带。
记者:可以认为我们现在还处于后殖民的时代吗?
高希: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得承认我根本不知道“后殖民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最关键的一点是,其实西方是很想要打这样一场鸦片战争的,以贸易的名义发动一场战争。
事实上,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我们都在用各种方式抵制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所以我认为鸦片战争其实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取得了胜利,现在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渴望成为下一个美国。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让整个世界都“美国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地球有它自己的物理极限,它不可能允许地球上的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享受同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对于殖民主义,或者整个这场鸦片战争来说,这一点恰恰被遗忘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本身就代表着绝对的不平等,因为只有在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才能成功运转。所以如果你想构建一个平等的环境,每个人都过上西方式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地球会崩溃的。
记者:甘地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高希:是的,不过也不光是甘地的看法,还有一些中国学者也是这样想的。
记者: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高希:对。而且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印度传统文化,不管是道家,儒家,甚至印度教,我们的前辈们看待人类生活和自然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亚洲文明的一份子,都不应该是贪婪的,我们不应该贪得无厌,予取予求,我们不应该那么自私。
传统价值不复,到处都是吃土青年,我们的世界不会好了
记者:那么,我们怎样能让这些传统的智慧与现代化的社会现实发生联结呢?
高希:我们没有办法,这些传统已经被丢掉了,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你知道吗,在短短10~15年的时间内,我眼睁睁的看见印度变了。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教育我们不要浪费,也不要欠债。但是现在你看看印度和中国,大把大把的吃土青年。这些年轻人们都使用信用卡,而且都负债累累。看看此刻窗外街上的那些车吧,他们靠什么买来的这些车?是贷款啊。
记者:您之前提到说欧美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做这种反思了。
高希:是的,事实上,我对欧美的年轻人很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能直接地感受到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本质。年轻的美国人,年轻的欧洲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崩溃,一方面是生态的崩溃。
而且我觉得目前在欧美,应该已经有新的抵抗运动正在兴起,比如说有一个叫作“退行增长”(Degrowth)的运动。所以当下,有很多有意思的运动正在发生。不幸的是,在印度,在中国,我认为年轻人还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奴仆,他们效忠物欲,希望等到更多更多更多。
记者:是因为我们还在发展中的缘故吗,因此很多的消费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
高希:或许吧,我想应该是这样。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发现不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当你看向车窗外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低头摆弄自己的手机。
记者:印度人也一样?
高希:都这样,我刚去过不丹,他们也是这样。年轻的不丹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低头族。真的让人感到很悲伤。这真的太可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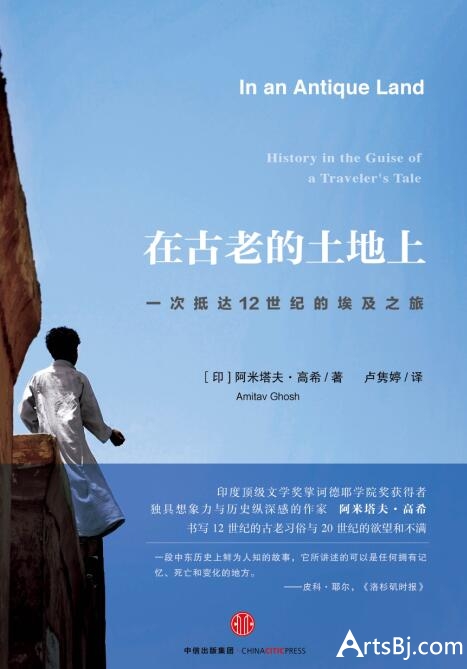
《在古老的土地上》
当下的“宗教问题”是战争的创伤,与宗教无关
记者:所以我们的未来终将被消费主义裹挟吗?
高希:我认为我们正处在历史长河中一个相当黑暗的时刻。这个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我们的的确确是生活在地球村之中,好比之前我还在印度,而此刻我又在中国,这两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算稳定。而如果你去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看一看,你会看到满目疮痍的文化,分崩离析的国度,要知道我对中东也算是有一点了解,我曾经在埃及度过了很长时间。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作《在古老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您在里面讲了自己是如何去埃及寻找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的,所以您对现代性的批评是以对其未来的悲观为前提的吗?
高希:我当然觉得古印度洋一带的世界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世界并不完美,但是很有意思,同时我也认为,这个世界已经遗失在时光之中了。悲观主义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只是指出人人都能看清的现实。而且也不光是我,整个德国哲学界从1910s~1920s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学科传统,我们得回到尼采,回到海德格尔去看这个问题。
记者:您怎样看待那片土地上肆意横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呢?
高希:我怎么看?自然是一脸惊恐的看啊!不然还能怎么看,那是绝对的恐怖。
看看现在世界各地的情况,宗教冲突已经越来越有杀伤力了。事实上,当我还在埃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在《在古老的土地》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关于年轻人越来越激进化,诸如此类。但是今天,宗教冲突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极端的状态,我认为伊斯兰国现象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宗教冲突,这样极端的残酷和暴力真的是让人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记得,伊斯兰国的崛起,是伴随着伊拉克战争开始的,还有随后我们看到的利比亚战争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也就是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这种声势浩荡的运动。我想,当一个社会经历了某些可怕的冲击之后,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那样的、超乎寻常的反馈。很显然,现在中东正在经历的,正是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后果之一。
记者:所以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信仰冲突,或者习俗冲突。
高希: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而往往,当一个社会经历了这种巨大创伤之后,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信仰”出现。要知道,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中国死了两千万人。在真正的战争过程中,可能死亡的人数并不多,几千人左右,但是战争带来的后续往往非常糟糕。
而且似乎在西方的干预下,同样的故事一再上演。比如英国人在1885年的时候侵略了缅甸,在那场战争中其实没有多少伤亡,但是战争带来的叛乱过程中,有几十万人因此丧生。而现在,你们看在埃及,在也门,在叙利亚,在土耳其,又正在发生些什么。
启蒙运动说一套做一套,自由贸易完全反人类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追溯过去,近几百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分配激荡里,起初是战争和自由贸易,再之前是启蒙运动,但启蒙运动的核心之一不就是平等吗,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那个时候其实也在讲私有制啊财富啊带来的不平等,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平等的扩大化。
高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不平等。
我提到了启蒙的问题,之前也提到了种姓制度。其实在印度,平等的观念和对于种姓制度的批判并不来自于启蒙,佛陀认为,众生平等,他是批判种姓制度的,而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有类似的关于平等的概念。
可有趣的是,当你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我们迈入现代化社会已经有二百来年了,或者说这二百来年以来我们过的都是后启蒙时代的生活,然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平等的现象比现在更普及,更严重。其实对于收入分配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当今的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刻。
想想看,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其实很荒谬,一方面,我们有了所有这些关于平等啊,自由啊之类的话语,而另一方面奴隶制度也达到了顶峰,种族主义被完全制度化了。所以这就是关于启蒙的有趣之处,它说一套、做一套,反差如此强烈。
所以,启蒙主义批判了不平等,可是它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记者:所以您想说的是这种启蒙价值的虚伪性?打着自由和平等的旗号,行的是贩卖奴隶之实等等。
高希:“自由贸易”这真的是一个完全反人类的想法。在所谓“自由贸易”的年代,首先应运而生的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破坏力的想法,也就是说,市场规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本身。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依然奉这种想法为圭皋。
人人都知道,市场必须有一定的道德边界。这个边界到底是什么、在哪里,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个边界一定是存在的,也必须存在。比如说,我不能拿走你的肝脏,哪怕我非常想要你的肝脏,可是我不应该被允许拿走你的肝脏。你看,在这个意义上,在鸦片战争中,来自清朝方面的批评,尤其是林则徐对鸦片自由贸易的批判,就是这样的。我们先不要管鸦片是不是毒品,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的道德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样的道德边界到底存在不存在?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以前,自由贸易就已经存在了,你觉得中国商人们那时候做了些什么呢?印度商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做买卖,他们在彼此合作,他们在做投资,所有这些商业活动他们都有从事,而且往往比西方人做得更好。可是他们做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有限的道德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其实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这些商人的活动总是被严格监视的,因为中国人相信“商人重利轻别离”。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看法。
所以说,所谓的“自由贸易”也不过是一个概念层面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商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声称的自由贸易完全是不知所谓——因为他们贩卖的鸦片都是英国的寡头大公司批量生产的!因此,他们一方面大言不惭的谈论着自由贸易,一方面却贩卖着垄断机制下的产品。此为其一。
其二,他们高谈阔论关于自由贸易和市场规则,然而面对发动战争的契机却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如果自由贸易真的有他们声称的那么强大,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他们一手抓“自由贸易”,一手抓“军队战争”,这个模式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比如伊拉克战争和鸦片战争又是何其相似!他们一边谈论着“自由贸易”,一边派了一支军队来“支持自由贸易”。这简直是自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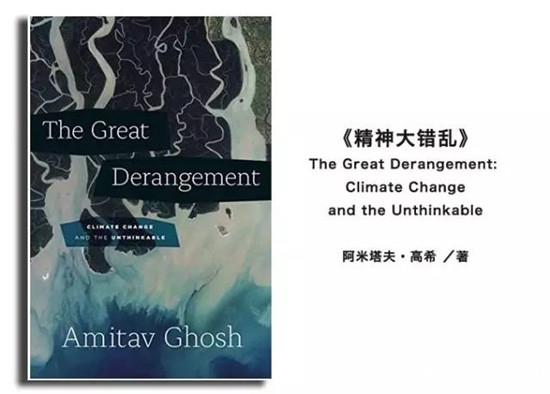
《精神大错乱》
印度奉行历史多元化,穆斯林几乎没人加入伊斯兰国
记者:然而,当今世界的军事政治秩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霸权格局,您也认为我们很难退回到过去的状态,那么未来呢?我们会面对怎样的未来?
高希:我想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无法恢复从前的旧价值秩序了。那些旧价值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关于未来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我想任何的危急时刻的好处之一,就是强迫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种不同的、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我的新书《精神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所提到的论点。我们不得去寻找那些新的方式来思考生命,思考这个世界,因为原来的那些模式很显然已经崩溃了。
记者:您认为这种新的方式是什么?
高希:我想我不能,因为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去思考我们是如何与世界相连的、以及我们是如何彼此相连的。所以我觉得,社群将会变得非常重要。而我也认为,社群正是我们正在丢失的东西。看看北京那样的城市,再看看孟买那样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深深的割裂了。
记者:那么在未来,社群建立的基础又会是什么呢?
高希:嗯,之前我也谈到了伊斯兰国的招募工作,有一个很惊人的事实不知你是否知道,那就是印度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度之一,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去加入伊斯兰国,所以人们说起伊斯兰国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起印度。我想,这是因为在印度,来自不同社群、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都生活在一起,而且几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光是从外表看上去,你就知道印度人民是非常宽容的。比如这儿有个人戴面具,那儿有个妇女穿着布卡(Burka,穆斯林妇女传统的罩袍)。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让你感到困扰,因为你知道人人都是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也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奉行的,是宪政多元化。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对于宪政多元来说,时常有龃龉发生,就以布卡为例子来说吧,法国政府对于布卡的问题非常头疼,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它。除了布卡,还有面纱,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印度,我们奉行的是历史多元化,历史多元化比宪政多元化要更有力一些,但我绝对不是说,历史多元化就一定是我们的未来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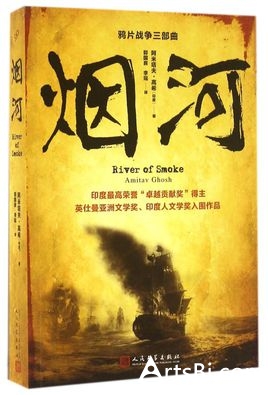
《烟河》
记者:其实您在《烟河》中提到的广州十三行的那个情境也有点类似这种历史多元化,虽然它是一个各方干预下的微妙平衡。
高希:你知道吗,在《烟河》一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广州。尤其是广州对外的内飞地(即“广州十三行”,起始于明朝,为政府设立的对外贸易特区)。这块内飞地构成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彼此交汇的、立体的多向性殖民空间,在当时,这里真的是除了租界之外,能够让亚洲人,非洲人,西方人能够充分交流互动的场所。某种意义上来说,内飞地也是一种殖民空间,但却不是被西方势力掌控的,而是亚洲本土的势力(译注:尤其是在清政府的控制下)。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广州内飞地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飞地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有意思的关系,印度人,中国人,西方人,马来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对我来说,这是《烟河》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些复杂的交易是怎么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或者说,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内飞地被完全地摧毁了,广州等通商口岸也完完全全地沦落为殖民地了,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完全被西方势力控制了。我想十三行的存在是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路。历史多元化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是反现代性的,它是在现代性的对立面生存的。
鸣谢:西天中土计划陈韵女士,肃慎猫和姜昊骞同学,三辉图书。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