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元勇
采访者:范俏佳
受访者:曹元勇
曹元勇,知名出版人,文学翻译家,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编辑出版过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系列(十六卷),作家张承志的文集(十二卷)等百余种图书。责任编辑的原创文学作品《蛙》和《江南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奖。工作之余,他还翻译出版有《海浪》、《马尔特手记》、《已知的世界》、《黑色唱片》、《老无所依》等外国文学作品,著有文学评论与随笔集《聚焦与印象》;近期将出版的译作有《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7月24日,曹元勇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主讲了一场题为“无关牧歌的乡村真相——才女萧红和她的《生死场》”的讲座,从萧红的生平经历,鲁迅、胡风等名家对其的评价等诸方面解读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和她的文学观念。借此机会,记者就近两年国内出版界的人事变动以及萧红作品中女性关怀等问题专访了曹元勇。
范俏佳:您如何看待从去年到今年出版界的资深编辑跳槽,如施宏俊从世纪文景跳槽到中信出版社,王笑红从上海三联出版社跳槽到译林出版社?
曹元勇: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行业的正常现象,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下,行业内没有人员跳槽、寻找新平台的现象出现的话,应该说是不正常的。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出版业其实也到了一个重新调整的阶段,就是说从出版资源到人才资源,再到出版行业的资本投入,都到了一个重组阶段,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些出版界的人才有新的流动,我觉得这很正常。
范俏佳:那您为何离开上海文艺出版社?
曹元勇:因为我原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应该说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个人来说,从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我没想到的高峰,比如有莫言的诺贝尔奖,我坚持了十几年他终于得奖了,然后茅盾文学奖也有两部作品得奖,一些重要的、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作家的作品我也出过了,比如说莫言、格非、张承志的作品,海外的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我也做过了,那么如果要突破自己,我想可能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才有可能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在原来的平台上可能我个人感觉好像很难再突破我自己,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现在上海的本地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决的,那么对一些想做事情的人,如果有机会在一个新的平台去做事情,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对个人来说你可能是等不起的,对一个大的集团来说是可以等得起的,它等几年都无所谓,但对个人来说你的五年可能就是很宝贵的五年,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
范俏佳:近年来许多出版企业纷纷采取跨区域经营模式,作为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社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曹元勇:原来出版社格局是个死格局,出版社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很难到另一地盘上开辟桥头堡。应该说出版业到了21世纪又经过了将近15年,也到了一个很多旧格局需要被打破的时候了。出版资源的第一资源是作者资源,就是说因为它是内容产业,以内容为主,而中国的人才首先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因此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在北京、上海陆续出现一些异地出版社的分支机构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在北京、上海,离人才就近一些,很多信息就会便利很多。外地出版机构进驻上海要比进驻北京要晚,北京过去就已经有很多了,近五六年才出现大规模进入上海的现象,所以说浙江文艺在上海开分社也不算一个新现象。
范俏佳:您认为全国出版业转型升级、跨界融合的发展新形势会为出版物的质量带来怎样的影响?
曹元勇:对出版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出版机构自身,还有包括社会的因素。比如作者是内容的第一生产者,是第一梯队,他的质量决定后面环节的质量,假如作者能提供高质量的内容,那么后面环节的质量就不会很低。那么作为出版这一方,受几个方面的限制,一个是作者资源的限制,一个是读者市场的限制,那么出版物质量的高低,和市场的需求也是有关的,当然作为出版方来说,质量的概念也很宽泛,含金量比较高或者受读者欢迎的,或者说尽量没什么低俗内容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出版这个环节,有这么多出版社在竞争,实际上也逼迫这些出版者更主动地在质量上要求自己,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因为读者的要求也在提高,出版机构的增多不是一件坏事,在竞争当中也能促进质量提升。
范俏佳:出版业新业态下的编辑工作是否会面临新的挑战?您愿意为新环境下的编辑工作提出一些您的建议吗?
曹元勇:作为一个出版人面临的挑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人也有挑战,你的出版物需要符合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一个编辑,你的出版物是不是能受市场的欢迎,同时也不违背国家的政策,这其实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如果你的出版物不受市场欢迎,经济上就会出问题,如果出版社经济上就维持不下去,关门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对年轻一代编辑来说,压力比以前大了。但是同时新一代编辑所具备的综合素质要比以前的编辑高,包括识别稿子的能力,比如一部书稿到底有没有市场价值、文化价值,要有一个判断,还要具备一定的市场运营能力,所以现在对编辑的综合能力要求比以前高得多。
当然这是一门职业,如果说要有什么建议的话,首先做编辑,经过一两年要认清自己,是不是一定喜欢这个行业,或者即便谈不上特别喜欢,也还能认可这个行业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做一名编辑可能会很郁闷。有了认同感才能适应这个行业,通过各方面努力再去提高,因为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只要你喜欢,就会主动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认同这个行业的价值。现在有纸质出版有电子出版,外界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比方有人说数字出版是出版业的明天,纸质出版马上就不行了,那么你能够认清自己工作的价值吗?只有认清这一点你才能坚持,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做到的。
范俏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将《生死场》列入纪念抗战胜利丛书来出版,您认为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与抗日战争相关联?
曹元勇:一部作品其实出版之后,别人要把你归到哪一类是别人的权利,也许萧红写作《生死场》的时候,她并不是想写一部抗战小说,但是里面又写到了北方乡村农民自发地起来救国救亡,有这个因素在,所以我觉得人民文学这么做也肯定有它的道理,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角度来看待《生死场》,我觉得这个是读者有读者的权利。也许有些读者或者出版人也没有仔细去读这本书,只不过前人有把它当成抗战小说就跟着做了,这种情况多种多样,但小说毕竟包含了抗战因素,所以人民文学这么做我觉得也没什么错,毕竟它通过这个方式也让这么多中国读者也读到了一本非一般的抗战小说。
范俏佳:您如何看待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关怀?
曹元勇:当女性主义批评家出来的时候,自然首先会关注到萧红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倾向,但这个所谓的女性主义是别人贴给她的标签。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因素肯定是具备的,但是萧红写作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这也未必,作家有作家的写作动力,至于要说她是女性主义作家,那么首先你是一个女性主义批评家,才会更重视这个层面,自然地就会选择一个角度去批驳把它当成抗战小说的观点,想要证明它不是一部抗战小说,就会强调女性主义这个侧面。对萧红来说,抗战也罢,女性主义也罢,都不能涵盖萧红作品本身,萧红作品本身的内容比这些主义或倾向要丰富得多。
范俏佳:您认为萧红成名作《生死场》对其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曹元勇:对她个人的状态来说,这部书的成功肯定对萧红想成为一名作家的自信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周围都是左联的作家,里面比如萧军,就是风云人物,周围的朋友只认萧军不认萧红,但是她的书又卖得这么好,也有人私下跟她讲,你的《生死场》大热说明你在文学上的前途肯定比萧军高,所以对她来说就很矛盾,有的人很捧她,有人觉得《生死场》里面有很多毛病。从左翼文学的角度来说,《生死场》不是一个完全的抗战文学,受到故事情节不强,人物又不鲜明等等一系列的批评,但作品很受欢迎,她会想为什么会受欢迎,她认为是因为她的写作最贴近底层人,她没有站在比底层人高的立场上,比如“我不是一个启蒙者,我是和农村的这些大姐大哥一样的”,她在这个层面上写作,所以她慢慢地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对文学的认识,所以《生死场》的成功对她形成这样一套非主流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中间她也试图写过一本书叫《马伯乐》,我觉得她当时有这种潜在的野心去证明说她也能写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丰富饱满的小说。《马伯乐》应该是她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但没写完,计划写三部,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只写了两部多一点,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剩下日子不多,所以赶快停下来去写《呼兰河传》。对她来说可能虽然有能力去证明自己也能写出所谓现实主义的那套小说,但是当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她肯定先选择写自己最认可的,符合自己艺术观的那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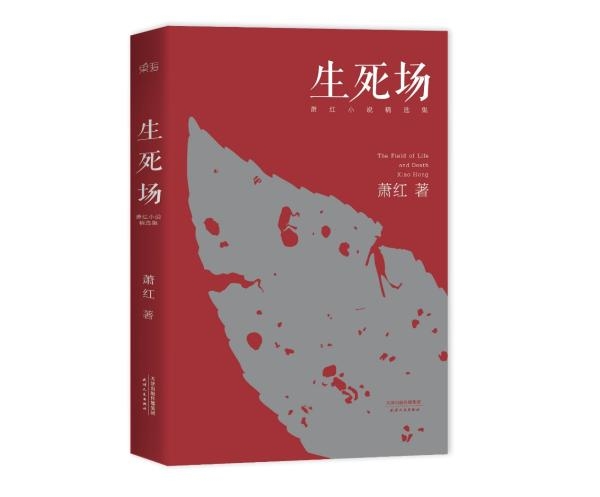
《生死场》,萧红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以下为曹元勇当天讲座内容节选。
萧红是民国时期的四大才女之一,是当中最短命的,活了31岁。这么多年过去,很多同时代名气很大的作家和作品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萧红的作品反而越来越有光芒,为读者所喜爱。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更多是谈她的《呼兰河传》。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只谈《呼兰河传》是不够的,必须要谈到《生死场》和《马伯乐》。
萧红出生在辛亥革命那年的端午节,按东北当时的风俗来讲,端午节出生的小孩不吉利,萧红家对外是隐瞒她真正出生日期的,一个人的出生日期都常被说是不吉利的,对一个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祖父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人,性格非常温和,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很爱护,这对萧红的影响也非常大。萧红8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很快又续娶了妻子,在北方乡村的风俗当中,继母一般都对前任妻子的孩子不好,萧红的继母就对萧红比较冷淡,她的父亲也对她不太亲近,但该尽的责任还是做到了,比方说在东北那个时候让一个小女孩去读书是比较罕见的,她的父亲却把她送到了哈尔滨的女子中学去读书,她的父亲从思想上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只不过在家里可能会对前妻的女孩表现得冷漠一些。
萧红16岁的时候上中学,学校里面有几位老师对她影响很大,萧红后来的写作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其实和这几位老师是有关系的。她的美术老师高仰山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思想受到那里左派艺术家的影响,注重表现普罗大众的生活,这也影响到他的学生,包括萧红。有一个细节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萧红在一次美术作业中,并没有选择老师提供的静物作为绘画对象,而是跑到他们学校的更夫那借了一个烟袋,又搬了一个石头,就这么画了起来,她选择了能代表底层人物形象的物品,这幅画被老师命名为“劳动者的恩物”,她关注底层,不直接控诉,而是选择了一个物品来代表它,后来我们也能看到她写《生死场》和当时萧军写《八月的乡村》是完全不一样的,萧红写的是底层的人民,可以说这是从中学的时候就种下的种子,她潜在的异于常人的艺术感在那个时候就被激发出来了。当时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萧红从语文老师那借过一本书,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描写的是底层工人的悲惨生活,这本书对萧红的影响很大,让她意识到用画笔画东西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文字的艺术表现空间大得多,所以她转而爱好文学,起了个笔名叫“悄吟”,并开始写诗。
萧红长大后曾经私奔过,后因此被家里人关禁闭,在关禁闭的期间,萧红与她的一位小姑妈来往密切,她的小姑妈因不答应家里安排的婚姻而被关了起来,萧红从自己和小姑妈身上看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家族、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束缚,后来萧红写《生死场》、《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当中都有对受社会风俗压抑的女性悲惨命运的描写。她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的经历非常不幸,也对其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写出的作品也不一样。
《生死场》到底写了什么,我觉得读者不应该听评论家说写了什么,因为评论家都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片面的,所以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要想知道一本书是写什么的,就要去捧起书来看。
萧红的写作非常细腻,她的细腻并不是说用很多语言去进行描写,而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抓住最最关键的东西。很多名家对《生死场》都有过评价,这些评价的影响很大,对当年萧红坚持作家之路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胡风,他是一个大文学批评家,他对生死场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准确。他发现这本书里写的农民,像蚊子似地为死而生,后来又巨人似地为生而死。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是要写一部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大家都一心要批判社会,写中国人怎样觉醒反抗。所以胡风从自己文学观的角度来看生死场,看到了三个缺点,但反过来讲,这三个缺点可能恰恰是生死场的优点,因为这正是萧红的写法,就像我们前面说她画更夫的烟袋,而不是给什么画什么。
胡风第一点说的是萧红对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散漫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我们想想,当时的农村社会,一个村里面其实是找不到一个中心人物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每天过的都是没有灵魂、精神的生活,都像其他的动物一样过着物质的生活。萧红对此看得很透,乡村社会本来就是这样散漫,萧红便按着这样写了。所以胡风在批评的时候,是期望她写出主流的样子,而萧红心里想的是,我知道有主流的样子,但是我要尊重我看到的真实,所以这是两个文学观念的冲突。
胡风第二个讲的是人物描写方面的不足,其实鲁迅也认为《生死场》的人物形象不饱满。但实际上因为它有象征主义小说的意味,是散文化的小说,就不会刻意地去刻画人物,而是主要写这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的生活才是主角。这样的小说在今天来看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在三十年代那个现实主义小说占主流的大背景下,萧红的文学观会显得比较另类,她遵从了她内心的真实,很多时候寥寥几笔就刻画了一个人物。
第三个批评是说她的语句太特别了,欠锤炼。从现在搞出版的角度来看,《生死场》的语句肯定会被改掉很多,但那样就不是萧红的作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过一版《生死场》,对它做了很多句式修改,很多意境就没有了。比如对成业和金枝谈恋爱的细节,也都改掉了,其实萧红已经写得非常克制,那个版本认为这是性描写,就删掉了。归根到底句法特点不是错,主要是萧红的写法是象征主义的、诗意的写法,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这样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语言有特殊的追求,至少想要达到一个陌生化的效果,而从胡风他们当时现实主义文学观来讲,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这三点我们完全可以翻过来去看,也很有意思。
萧红笔下的乡村与很多作家的不一样,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恬静,而在萧红的笔下,农村是多么残酷。沈从文笔下的农村是我们很多人想象当中的乡村,风景优美,民风淳朴;莫言笔下的乡村——《天堂蒜薹之歌》,写改革开放年代的乡村,农民在国家机器面前极其渺小;阎连科写过一本叫《炸裂志》,写一个村的男人靠偷抢,女人靠卖身发家致富,后来这个市变成直辖市,完全靠着打劫过路的拉煤车。所以说作家笔下的农村是各式各样的,有理想化的牧歌式的,也有非常残酷的。
萧红的散文像小说,她的小说像散文,文体之间的鸿沟被打破。当时人总批评萧红的句子、人物描写不够好,她也有点反感,其实她不是不会写情节、人物饱满的小说。她也写过有情节的长篇《马伯乐》,对人物的塑造也是栩栩如生。后来写《呼兰河传》的时候萧红已经经历了很多,相比写《生死场》的时候心态有很大的变化。写《生死场》时她是要把自己内心的作为女人的愤怒都要爆发出来,根本不管别人看法,而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她的心态已经平稳了,如同河水一般去追忆、控诉。以准备闯文坛的心态写《生死场》,和到后来生命即将走到终结的时候写《呼兰河传》,是不一样的。
萧红的小说观念与当时主流的很不一样,她的小说写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现代派小说的自觉实验作品。她认为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觉得鲁迅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可以启蒙别人,而她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高度,只能站在和笔下人物平等的立场上来写,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异类的文学观,只有这样的文学观才写出与当时主流不一样的作品。我们当代一度有改革文学,工厂文学,有写农村的包产到户的文学等等,但这些作品到今天来看,文学价值比较低,配合国家政策来写作的文学是缺失主体性的。后来只有有自我觉醒意识的这些作家,像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这些人,才经过时间的筛选,成为当代文学当中最重要的作家。萧红也一样,她的作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类是底层人物的生活,一类是带有自传性的。所以萧红的作品为什么能变得越来越让人喜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应该说和她写作内心真实,而不是从宣传和当时社会主流要求的角度来写作有很大的关系。萧红经过七十多年,也逐渐成为像张爱玲、鲁迅、沈从文这些作家一样的,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