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润生

殷实

新时期军旅文学 代表作品
采访者:记者
受访者:殷实
今天是建军节。在中国文学生态中,有一支文学力量始终存在,但较少被拿来讨论,那就是军旅文学。今日的军旅文学创作,除了一贯以来写军营、写军人的题材外,各类战争题材的类型文学十分扎眼,它们在畅销书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该如何看待当今的军旅文学?军旅文学创作现状如何?问题何在?出路又在哪里?带着种种问题,昨日,记者采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殷实。
军旅文学与当下军营现实存在疏离
记者:谈起军旅文学,这四个字对于很多读者估计是有点陌生的,他们估计更愿意听到战争小说。在我的印象中,军旅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是很熟悉的一个词,那时的作品家喻户晓的很多,最出名的估计要数80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那个时候听到“军旅作家”这个称号,觉得非常神秘。但近一二十年来,军旅文学尤其是军旅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可读性不高,总觉得他们的题材太雷同了,无非就是营队那点事,写得太实了,看不到有多少想象力……
殷实:曾几何时,军旅小说与“军营现实题材小说”之间,其实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其他的小说传统。一般来说,中国作家擅长写实,喜欢记录,多半情况下,仅只是仰仗生活本身的丰厚赐予,他们就可以展开自己的工作了,而且往往卓有成效——在接受方面没有任何异议。军队作家们的写作也是如此。这种天然的、也就是不自觉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中国式的观照世界的生命态度有关。简单地说,我们“载道”、“致用”的精神制度本身,就在规定着文学的世俗化性质,同时也制约了想象、虚构和寓言层面的“离经叛道”。
记者: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阅读体会,今日的军旅文学写军营生活,但总觉得写得不深入,反映的仅仅军营生活,没有写到人心深处去。
殷实:今天的军旅文学写作,与当下军营现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论很简单:存在着某种严重的疏离。从创作主体也就是作家方面来看,甚至存在着有意无意的回避。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奇怪:世俗化特征鲜明的文学写作,却要与现实保持距离,长于摹写生活、照搬“现实”的军队作家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简单地梳理一下,我们会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生活”、“干预生活”,到90年代的“军营新写实”,军旅文学基本上都是应和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在同步前行。“表现生活”、“干预生活”,自然多少会带有主题先行的遗风,致使艺术创造的主体精神多有贬损。“军营新写实”又太过于照相式的逼近,造成了就事论事和机械反映。[Next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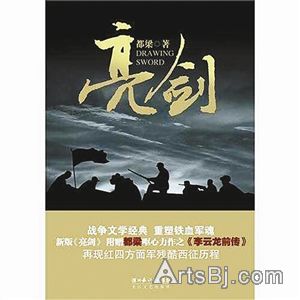


新时期军旅文学 代表作品
战争题材类型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记者:新世纪之后的军旅文学呢?
殷实:按理,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收获教训,有所超越。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这个新的现实很快引起了作家们的浓厚兴趣——不是基于市场观念在本质上对人、对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积极或异化作用感兴趣,而是对如何才能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感兴趣。许多作家一夜之间变成了畅销书商、影视剧生产商的雇佣劳动者。我们看到了大量以战争题材为主的畅销小说,以及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这意味着,原本具有思想主动性的精神活动——写作,进一步世俗化,降格为一种向订制人提供商品的“量体裁衣”行为了。就市场条件下的劳动交换而言,这也许无可指责。然而,若从精神事务的层面看,就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价值的否弃。此种变化所引发的悖谬和矛盾,看上去格外地难以调和:作家们服从或者迎合读者、观众的趣味,而自然人性所要求的诸如猎奇心理、对刺激的满足,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化享受,最终塑造出的大众“美学”需求,往往平庸而低俗,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非理性的和反智的。尽管他们的故事很好看,情节很离奇,但终究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记者:如此说来,军旅文学要有所作为,必须走出既实用主义地寄身现实却又谨慎地回避现实表达这一怪圈。走出之后,又该怎么办?
殷实:很多人谈到军旅文学的怪圈,会想到发表和出版机制、意识形态管控之类的制约,其实未必,还是创造力、想象力的问题,是作家思想境界和生命情怀的问题。在此可以举两个当代以色列人的例子:小说家奥兹,写了多部以巴以关系为主题的小说,既受到以色列读者喜爱,也受到巴勒斯坦人的青睐,因为他的小说中对巴以和平的渴望,对人类之爱这些主题的深刻理解,完全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政治的藩篱;同样,在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笔下,刀剑、担架、爆炸声和母亲的哭泣,都是最常见的意象,他并没有简单地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谴责那个民族,而是通过对军事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一再告诉人们和平是多么珍贵。历史上,美国诗人惠特曼写军人与战争的一些诗歌,中国诗人穆旦写于抗战时期的许多作品,都堪称经典,至今少有人能超越。反观我们当代的军旅诗歌创作,显得过分随意,没有什么形式感,也没有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深度介入,写岗哨、士兵、枪,都是在刻意营造,很难深入人心。
通过比较,军旅文学要走出怪圈,作家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各种精神文化困境,要有勇气面对和突破,还要有历史眼光,并从现状这个大的格局中去思考,并且超越现实,必须要有这种崇高的情怀。
新人新作看到可喜变化
记者:最后,谈谈就你观察到的一些好的、给人惊喜的作品。举个具体的例子。
殷实:这两三年来,我在一些新人新作中也看到了一些迹象。我认为这些迹象预示着可贵的变化。作家王凯的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中篇小说《终将远去》、《任务》这些作品,大都涉及了军人的道德困境,以及他们内心的挣扎、自我修复、自我救赎冲动等等,这在之前的军旅文学中是稀有的元素。
《全金属青春》中,一名军校同学肖明因被大家孤立而痛苦难抑,在极端心理状态下与哨兵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被退学处理。在肖明离校当晚,同宿舍每一个自觉不自觉讨厌过这位室友的人都辗转难眠,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之中。原因很简单,这是个一入学就以“积极追求上进”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角色,他的种种表现,在成熟得略有些冷漠世故的各位室友看来似乎有点平庸,但当这位只不过按照一般社会逻辑寻求自我塑造之路的孤独个体遭遇惨败时,本该幸灾乐祸的同窗室友们却无法不承受自责,当惩罚真的出现时,还是让他们觉得惊骇,严厉得有点不能接受,还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看透”,却被证明是另一种更可怕的平庸。这样的小说就很好,写出了人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还准确捕捉到了一种天然纯洁的善。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