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语冰(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沈语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世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系统翻译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独立或合作翻译了十余部经典著作。
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沈语冰的新著《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

沈语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出版,401页,98.00元。
采访者:丁雄飞
受访者:沈语冰
您在《图像与意义》中介绍了六位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他们涵盖了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艺术社会史、精神分析、视觉考古学等主要理论流派。这些方法更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方法的更迭是否体现了时代的变化?
沈语冰:这个问题需要追溯艺术史这个学科十九世纪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以后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化到二十世纪的规律。艺术史在德奥建立的时候有两大基础。一是为博物馆的收藏培养鉴定家。欧洲的博物馆是在十九世纪大规模兴起的,其时就面临了收藏的问题:作品有真伪,鉴定是基本功,需要大学建立学科来培养鉴定家。这是艺术史这个学科的初衷。在培养鉴定家的同时,它发展出了对作品的风格形式进行分析的方法。当时的维也纳学派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形式分析潮流了,代表人物有里格尔、沃尔夫林。另外,瓦尔堡认为分析作品光靠形式不够,还要涉及图像的主题和意义问题,这就发展出了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形式分析和图像学便成了艺术史最初的两大传统。国内如范景中先生等人是做贡布里希研究,陈平先生做维也纳学派研究,可谓抓住了艺术史学科的根本。
到了二十世纪初,英美开始有艺术史学科。罗杰·弗莱在担任牛津、剑桥的艺术史教授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艺术史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问题,他觉得德国已经做得很好了,英国也应该做这个工作。二十世纪后,在之前的两大传统之外又发展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艺术史的学科范围也拓展了。我这本书把源头放在弗莱,同时又收入了对施坦伯格的研究论文。这就囊括了形式主义和图像学这两大传统。弗莱的形式主义是对过去形式主义的发展。而我在施坦伯格的图像学研究前面加了“现代”两个字。是因为早在中世纪就有图像学了,到了近代,瓦尔堡、潘诺夫斯基使之成为比较完善的方法,但主要用于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图像学的功能主要是考察图像的主题。但施坦伯格把图像学用到了现代作品的研究,他研究罗丹、毕加索、罗丹,一直到美国画家约翰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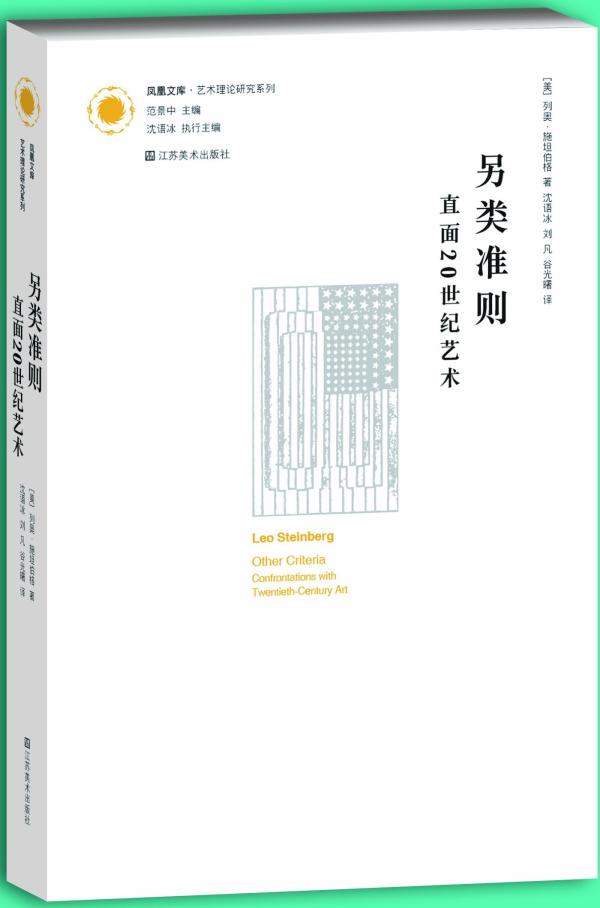
列奥·施坦伯格 :《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光曙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上面这两个学术传统大致属于传统美术史的范畴,但二十世纪还有很多新的发展。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非常强势。到二十中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皮罗的方法是多元的,不仅仅是我在章节标题上所讲的“精神分析”,他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和艺术社会史。夏皮罗晚年感兴趣的是视觉语言的符号学。我在这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他的精神分析个案,尤其是他对塞尚的苹果和梵高的鞋子的研究。
二战以后,艺术史的中心有向英美转移的趋势。因为战时许多德奥的犹太学者都移民英美。贡布里希从维也纳去了伦敦,潘诺夫斯基则从汉堡去了普林斯顿。与此同时,美国大学的艺术史学科也越来越强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博物馆和民间收藏逐渐崛起。这与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渐成世界强国有关。大都会博物馆刚开始时不能和罗浮宫、大英博物馆比肩,但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了。这些原因导致了对艺术史学科的需求的增加。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建立了艺术史系,博士生也越来越多。很多新的方法和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其中比较大的转型是艺术社会史。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东欧国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如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研究影响很大。但他有局限性,研究方法比较粗犷。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与具体的作品、艺术现象的对应有时候比较勉强。T. J. 克拉克将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大大精细化了。虽然他自己的目标仍然是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但他不会像传统的艺术社会史那样粗线条。克拉克在七十年代初出茅庐,到八十年代成为一代大家。有人把以他为代表的方法命名为“新艺术史”,表明他们拓展了艺术史的边界。
到了九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研究又有大的变化。英美受到了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巴特的影响。在美国出现了《十月》杂志,以及所谓《十月》学派,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当然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学院层面,一般画廊会觉得他们太深奥了。《十月》主要关注的是二十世纪的艺术。我准备在下一本书里好好研究他们。《十月》的主要兴趣是二十世纪艺术,但我在目前出版的这本书中主要关心史学研究,所以我写了克拉里。克拉里是《十月》杂志的作者,但他不是标准的《十月》派,与他们有点距离。克拉里的研究对象是十九世纪艺术。他所用的方法是视觉考古学,主要来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比如1900年前后塞尚画了一张画,很独特,克拉里不再把这张画放在纵向的脉络里,说塞尚受到谁的影响,有何种人文主义的渊源,而是研究塞尚的这幅画与1900年欧洲其他知识体系,比如伯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谢林顿的神经生理学、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的关系。他做的是同时代的横截面的考察。克拉里做了十九世纪七十、八十、九十这三个十年的横截面的视觉考古:七十年代选了一张马奈的画,八十年代选了一张修拉的画,九十年代选了一张塞尚的画。分别考查这三张画和当时别的知识体系的联系——可能是画家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换言之,当时的艺术生产也是整个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而这些生产是受到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有生产的场域、惯例和边际条件。
这样我就大致勾勒出了二十世纪英美艺术史学的基本面貌,既有早期相对传统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也有中期的精神分析和艺术社会史,更有晚期的视觉考古学。但我的研究不是事无巨细的,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方法。
您是否能通过对一幅现代绘画作品的不同阐释,来呈现书中不同方法的不同侧重?

马奈:《在花园温室里》
沈语冰:我在之前的讲座里,通过马奈《在花园温室里》把我研究的六种方法串联了起来。这幅画是克拉里重点研究的。那么,《在花园温室里》和形式分析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不知道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奈把一男一女放在不同的光线下,色彩的处理也不同,比如那个女的特别明亮光鲜,男的则在灰暗中。单纯作形式分析我们也可以趋近这幅画。形式分析是一个基本方法,就像我们读文学作品,一开始不会注意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意图,但我们对语言、文体会有直觉上的感受。
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对看这幅画有没有帮助呢?也有。因为这张画很平面,是在一个很封闭的花园的温室里,画的正中间放了一把椅子,女的坐在椅子上,男的在扶手背后,男女的背后是密密麻麻的绿色植物和花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提倡的纵深空间就压扁了,压成平面了。这幅画主导的视觉引导是那把椅子的水平线,还有栏杆的垂直线,就变成了很平面的一张画,纵向线和水平线的分割。格林伯格强调平面性,认为从马奈开始绘画进入了现代主义,因为马奈有意识地追求平面性。
现代图像学和这幅画也有关系。图像学考察主题。我们从画的标题里无法确切知道画的主题是什么。但我们把反复出现的主题称为母题。在欧洲绘画史上,从亚当和夏娃以来,一直是这个主题:在一个密密麻麻的森林或花园里有一男一女。马奈的前辈画家弗拉戈纳尔,画了一系列男女贵族青年在花园里幽会的场面,和马奈这幅画就很有关联性。同样的主题,男女在花园、丛林中相会,反复出现。
再说精神分析。马奈有意识地把那位女士的脸蛋、嘴唇、耳朵的色彩画得和旁边的鲜花的色彩一摸一样,粉色和玫瑰红,调子也一样,马奈可能用了一次调色,等于把女士画成了鲜花。她的衣服紧紧包裹着身体,除了脸,只有一只手露在外面,还有一只手戴着手套。鲜花是一个精神分析的隐喻,花是植物的性器官,通过色彩和香味吸引昆虫传播花粉。画的场景又在温室——一个男女偷情的地方。所以这幅画的精神分析色彩很浓郁。
艺术社会史会讨论这幅画的定制者是谁,赞助人是谁,画上的两个模特是谁,这些是在画以外和社会相关的问题,把艺术品理解为艺术生产的一部分。就生产而言就有生产者、生产工具、消费者。这么看就会发现,这幅画是马奈专门为官方沙龙展出画的,不是送给朋友的,也不是卖给一般的画商、客人的。画面上的两个人,我们考察发现,真的是一对夫妇,是马奈的朋友。马奈让他们做模特的时候,他们还维持着婚姻状态。但是他可能敏锐地发现他们两人有问题,捕捉到了他们貌合神离的一个瞬间。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交集,目光也没有看对方,身体也没有接触,很疏离的感觉,特别是那位女士的眼神很恍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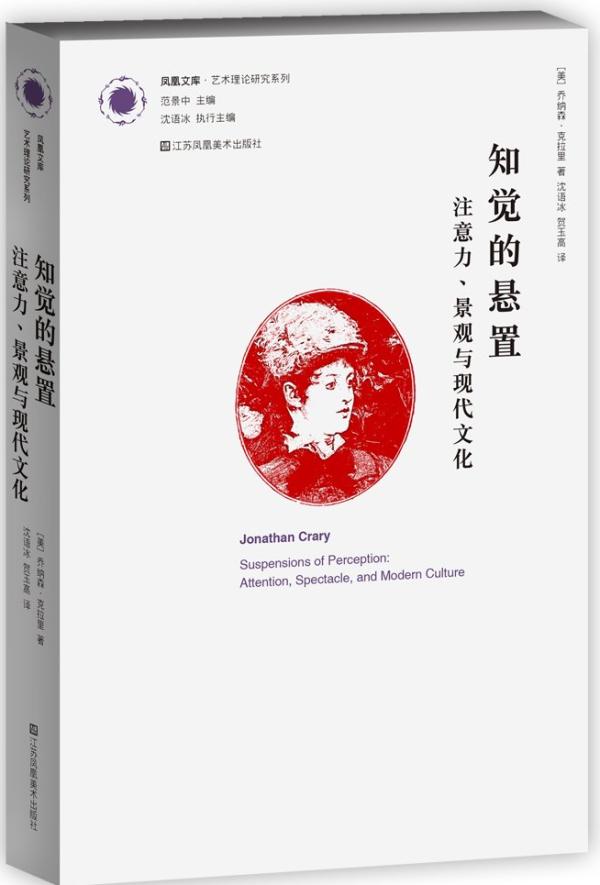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沈语冰、贺玉高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克拉里重点研究过这幅画。他把它放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当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注意力,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他画的男女都是对车水马龙的巴黎社会的逃避,躲到了花园的角落里,做白日梦,分神,逃避外部的喧嚣,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眼神就像梦游似的。这是他揭示出来的当时的时代特征。克拉里还把马奈看对象的方式,他所预期的观众的观看之道和七十年代的很多视觉发明——包括凯撒全景画、西洋镜、奔马的连续摄影联系起来。这些发明都改变了人们的视觉经验。过去我们看马跑,我们的眼睛没能看得那么快,不知道马确切是怎么跑的,连续摄影改变了当时人们的视觉经验。这和马奈的视觉经验是有关联的。马奈意识到,摄影对绘画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启迪。马奈的绘画作品有强烈的照片感。他的画时间性特别突出。他要画的往往是一个瞬间,这和摄影有关。他让这对夫妇做模特做了四十回,但他不像学院派画家一样,层层叠叠在上面修改,而是不满意就刮掉重新画。马奈要反抗学院派的绘画,要给观众即兴创作的感觉。所以这幅画既有高度的完成感,同时又有大量笔触暴露在外,最后呈现出来的还是瞬间感。
我尝试通过这么一张画把现在艺术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贯穿起来。要知道这些都是读图的基本方法。而许多人的读图能力或者说视觉素养是比较糟糕的。因为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系统不发达,艺术的普及教育的水平不高,又较难看到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的真迹。不像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从幼儿园年代起,就花大量时间泡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因此他们的读图能力和视觉素养就比我们高出许多。
为什么把罗杰·弗莱作为现代艺术史论的起点?所谓“现代”艺术史论是什么意义上的“现代”?布鲁姆斯伯里群里这种在学院之外的形式在英国文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今天仍然有启示吗?
沈语冰:弗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在中国,某种意义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少在我翻译弗莱的书之前的情形如此。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翻译了弗莱的一个学生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贝尔提出了一个口号: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口号在当时红遍大江南北。这和李泽厚先生的积淀学说有关——抽象的形式里怎么有具体的内容,是因为形式里积淀了内容。李先生重新阐释了贝尔的理论,因此好像与贝尔的思想不谋而合。就这样他把贝尔的书先引入国内。其实“有意义的形式”这个说法(我将significant form翻译成“有意义的形式”而不是令人误解的“有意味的形式”)最早来自弗莱。贝尔把这句话强化了,弗莱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讲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绝对。但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错觉:贝尔很重要,弗莱却被遗忘了。事实上,无论在学术史的重要性上,还是从辈分来讲,弗莱都要排在贝尔前面。
弗莱和伍尔夫一道,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核心成员。弗莱在欧洲的现代艺术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时候,就通过自由策展,举办了两届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展。“后印象派”一词就是他杜撰出来的,他命名了这个艺术运动。弗莱对于后印象派的推动,对于现代艺术在欧洲的接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举办这些展览的时候,媒体疯狂攻击他。因为当时的媒体和公众对塞尚以后的现代艺术大多看不懂,认为这些东西太草率了,作品是未完成的,和传统学院派的光洁、完整的作品一比,显得粗制滥造。弗莱要说服这些公众,这些东西是好的,好在哪里。他就举办了很多讲座,写了很多文章。他要把领会到的美好的东西教给观众,告诉他们如何欣赏新艺术。他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更精细的分析作品的方法。同时,因为他的哲学思辨能力特别强,因此能够将形式分析方法上升到形式主义美学的高度,成为20世纪整个现代艺术理论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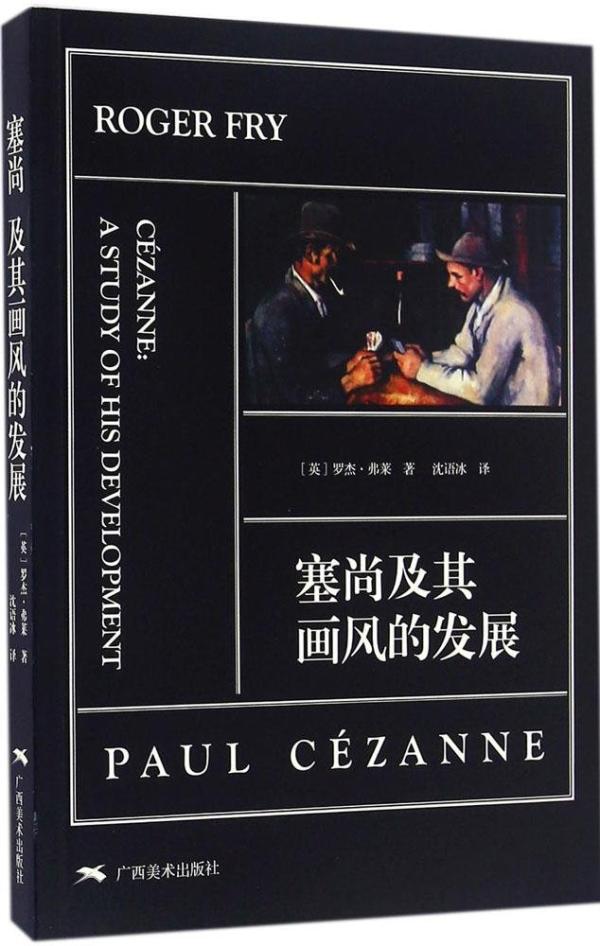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弗莱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秘密小组的成员。国王学院从每年的新生当中秘密地选中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怕造成没有被选中的人的心理负担。这个传统来自中世纪的某种神秘组织,发展成现代大学里的绝对精英。他们每周六聚会,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一个问题,培养出了极高的思维能力。这种训练使弗莱变成能力超强的一个人。
弗莱的地位是多元决定的。他在介入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已经是欧洲古典艺术收藏、鉴定圈子里的顶级人物之一。他早就被任命为大都会博物馆欧洲绘画部主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和美国的贝伦森、意大利莫雷利,被公认为鉴定古典绘画的权威。因此,弗莱的眼力很厉害。
我被他吸引也有一些个人原因。2001到2002年我在剑桥大学访问。经常去国王学院查阅弗莱的手稿。当时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读了他1927年版本的《塞尚及其风格的发展》,是他晚年的杰作,尽管是本小册子。我读得很兴奋,原来对塞尚作品的分析可以达到如此精妙的程度。过去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往往是直觉性的、印象式的,带有抒情色彩的,不可能真正切入一幅画的肌理,无法揭示塞尚的工作方式。弗莱在他的书里却作了极其出色的研究,不仅令读者仿佛可以走进塞尚的画里,而且让读者明白塞尚的工作方式。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您在讨论迈耶·夏皮罗与海德格尔、德里达关于梵·高《一双鞋子》的争论时,为什么不断强调艺术、艺术史相对于哲学的独立性?您如何理解艺术批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

梵·高:《一双鞋子》
沈语冰:关于夏皮罗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以及后来德里达对他们二位的再批评,国内外学者写了好多文章。他们之间的争论涉及到学科范式,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我的立场并不是要批评海德格尔或德里达,也不是要贬低哲学思维的有效性。海德格尔要批评欧洲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德里达更激进地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我觉得他们二者都在各自的关切里谈他们自己的看法。但国内不少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夏皮罗的关切是什么?人们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理解远远多于夏皮罗,哲学家的文本大量被翻译成中文,研究夏皮罗的人有几个?夏皮罗也是著作等身,目前已经译成中文的只有我和朋友翻译的两本。我觉得需要把夏皮罗的关切揭示出来。夏皮罗要捍卫艺术史的人文主义的传统,这是艺术史学科的基础。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都在反对人文主义,海德格尔要回到前苏格拉底,回到人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德里达更不用说了,要解构欧洲把人建构为主体的形而上学脉络。夏皮罗还是秉承了康德以来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追求人的尊严、价值、自由,承认人的局限性,讲究宽容。夏皮罗早年是比较激进的,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到五十年代以后,他的立场有所改变,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人文主义。这样的一个关切使他比较担心海德格尔的论述中取消了艺术家的地位,取消了人的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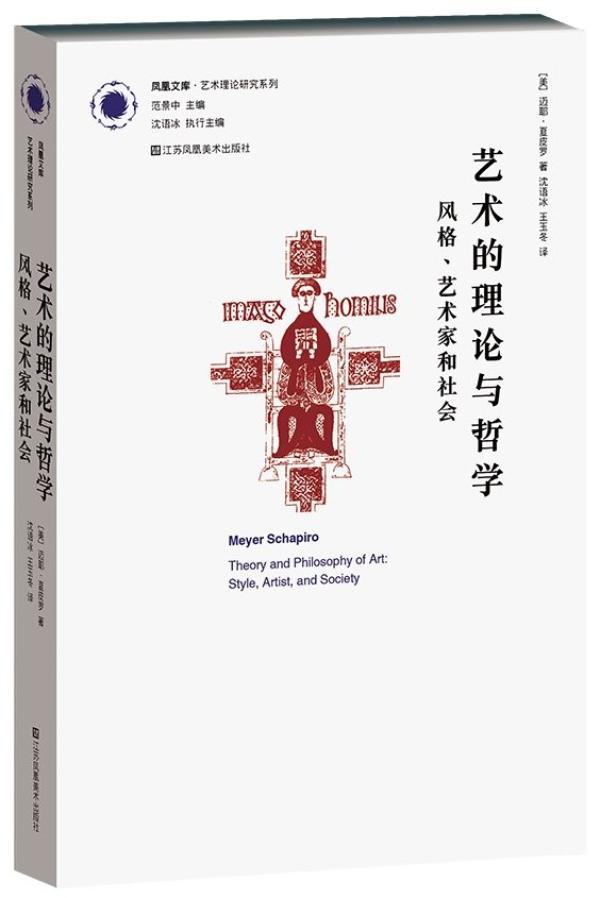
迈耶·夏皮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与社会》,沈语冰、王玉冬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海德格尔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只是真理呈现自身的通道,艺术家是无关紧要的,是被真理选中的,就像诗人被灵感选中一样。海德格尔认为梵高的《鞋子》是农妇的鞋子,让他联想到大地、分娩、死亡,真理得以敞开,世界得以保持。但这取消了艺术家本身的在场,和梵高基本没什么关系。夏皮罗的主要观点是,这是梵高自己的鞋子,根本不是农妇的鞋子。这双鞋子是梵高的自画像。向日葵、土豆、鞋子是梵高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题,他对它们有个人寄托。就像马奈是个富二代,经常画鲑鱼、牡蛎、芦笋;塞尚反复画苹果一样。鞋子是梵高长途跋涉的见证,梵高爱好走路,会从荷兰走到比利时。他有好多双走烂了的鞋子放在房间里。他气馁、沮丧的时候,觉得跋涉是徒劳的,但另一方面,他觉得跋涉有朝圣感,永远朝向下一个目标。夏皮罗的基本想法是,鞋子是梵高的个人精神写照,某种意义上的自画像。他无法容忍在海德格尔那里梵高可以不存在,重要的是鞋子本身,而从鞋子里看出农妇和大地的关系。他认为这不是对作品的真正的观看。
当然德里达说梵高可能拿错了鞋子,那可能是两只左鞋,这个可能性总是有的。德里达把海德格尔和夏皮罗都解构了:你们两个都认为这是一双鞋,一个说是农妇的鞋,一个说是梵高的鞋,但德里达认为那可能根本不是一双鞋,而是两只左鞋,或是两只右鞋。当然这种可能性永远存在。哲学家们喜欢拿可能性说事,他们甚至认为现实世界都只是可能世界的某个或好或坏的版本。但让我们考虑一下,梵高拿错鞋子的概率有多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不是一个数学问题或概率问题,而是一个同情理解的问题。因为梵高画过至少八双这样的鞋子。难道他八次都拿错了?都画了两只左鞋或右鞋?这是荒谬的!
我们该如何理解T. J. 克拉克的这句话:“承认‘政治’与‘美学’乃是永远无法结合起来的一体的两半,要比当下左翼学院派通行的那种两者只能选其一的论述高明得多”?这种说法对国内的艺术批评有什么借鉴意义?
沈语冰:这是克拉克在做了大半生研究后,在写《瞥见死神》这本关于艺术史的实验性写作里写下的。他反反复复看两张普桑的画,抛开一切他过去的理论框架,针对画面本身,把他看画的各种经验记录下来。他写的是日记体,比如某一天在这个博物馆看普桑的这张画。在不同的光线下,在博物馆大厅不同的人流量的状况下,他反复地看,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是对他过去的写作过重的理论色彩的反思。我认为他在这句话里带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他过去的写作和别的左派学者一样,都想把政治和美学结合起来。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很难。把政治和美学向任何一个方向还原,不论把政治还原为美学,还是把美学还原为政治,都会出问题。还不如保持双方的张力,保持二者一定的独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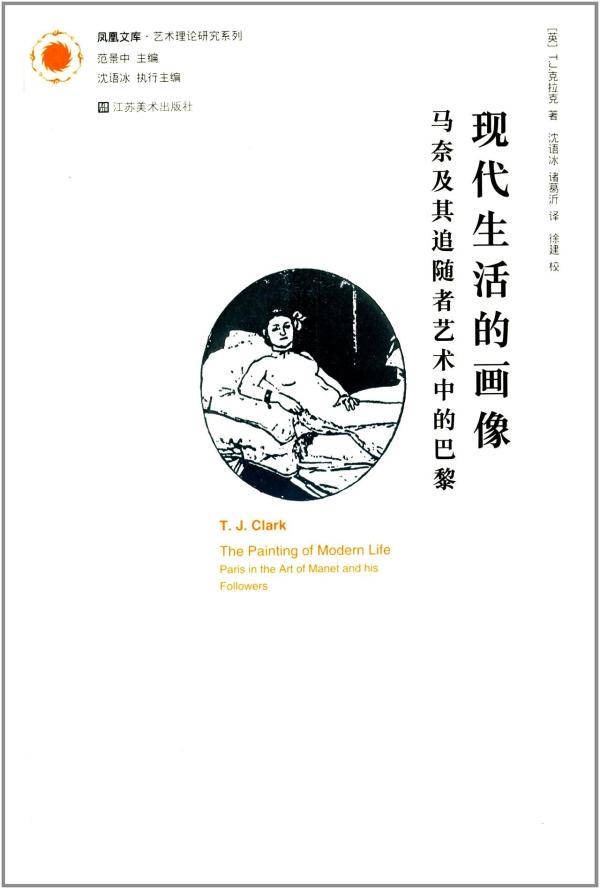
T. J. 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有的艺术家的某几件作品是把他的政治诉求和美学追求统一起来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无法统一的。艺术家经常是矛盾的、分裂的。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说库尔贝、杜米埃尔这些政治立场比较鲜明的艺术家,当然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政治立场不是那么鲜明,他们也有社会关切,也有隐含的政治立场。最典型的就是马奈。他没有参加巴黎公社,但他对镇压巴黎公社的大屠杀是十分愤慨的,他同情巴黎公社。但要把他的这种政治立场和他的创作美学直接结合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他偶尔有一两件作品暗示了他对巴黎公社镇压感到痛苦,以及他对屠杀者的抗议。虽然艺术,尤其是伟大的艺术脱离不开共同体,也就是说脱离不了政治,但也不能把伟大艺术和政治等同起来;艺术既不等于政治,也不在政治的对立面。克拉克这句话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反思,也提醒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不能简化、还原艺术。
您长期致力于系统翻译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独立或合作翻译了《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现代生活的画像》等十二部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您如何理解翻译和西方艺术史学科在中国之建立的关系?
沈语冰:翻译对学科建设非常重要。我一直在综合性大学工作,对学科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比较了解。比如外国文学、西方哲学比西方美术史发展得要好得多。外国文学无论是理论还是文本都有大量翻译,尤其文本,不少文学大师的作品甚至有好多译本。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有扎实的文献基础,就形成了讨论文献的共同体。如果没有译本,那连讨论翻译得好不好的对象也没有。每个人阅读原著有自己的阅读法、有自己的诠释,如果有一个译本,就方便围绕它讨论。当然,艺术史的文本有多种含义,我们也可以直接面对作品这个文本,但我们国内很少有系统收藏西方艺术品的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可能要更多借助文献。这个时候翻译就很重要。一个与西方相关的学科好不好,就看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如何。有的学生说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但他读了原文后,他的理解如何往往不得而知,这样就无法讨论,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我的翻译就是我的诠释,诠释的对不对、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我相信我的译本里肯定还是有好多问题的,但有了肯定比没有好。翻译是引起讨论的契机。

沈语冰、张晓剑主编:《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另外,翻译还是把外来文化融入我们本土文化的重要手段。历史上我们翻译佛经有近一千年,才创建了自己的禅宗,相比之下,我们近代以来对西学的翻译,虽然量上很多,但在质上,在消化吸收上,不见得比古代更好,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很好理解,更不用说融入我们血脉,变成我们创新的资源。
外国美术史过去翻译的比较多的是通史,都是蜻蜓点水的。今天必须要进入专题研究的层面。比如对塞尚的研究有好多年,从最早徐悲鸿和徐志摩的争论,一直到现在,快一百年了,但我在翻译弗莱的书的时候,查阅国内的塞尚研究文献,发现介绍和研究都少得可怜。我们对塞尚真的不甚了了。弗莱的那本书翻译成中文就六万字,但我做了十多万字的注释,都是关于塞尚研究的。国外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国内了解的还很少。如果我们文献不扎实,永远停留在常识性的水平上,我们这个学科永远无法繁荣发展。对此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很多画家朋友也有类似的感受。我觉得外国美术史要向外国文学、西方哲学学习,必须要有系统的翻译才行。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