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平时有点儿呆。在学校的时候,常被老师叫起来坐下去。中学没念完,我们就去云南农场了。傻子不太能干活儿,瘦筋干巴的,就起了个念:当卫生员。农场的卫生员,平时不用上山干活儿。谁头疼脑热,给点儿小药,谁磕了碰了,抹点儿红蓝药水,要是碰上大事故,就往分场送,再不行,往总场送,还不行,转昆明。真是个操不了大心的差事。我笑话傻子,说他想跟女的抢事儿。傻子说:“卫生员也不全是女的。二队的卫生员不就是男的吗?”傻子真就买了本儿《赤脚医生手册》,从头一页语录念起。我有个拐八道弯儿的亲戚,在医大念了八年,才当上医生。我妈那回在他那个医院住院,有点儿什么事儿,这位亲戚还得请老大夫。我把这话跟傻子说了,傻子不泄气,可麻烦也来了。我累狠了,请个病假在床上躺着。他像回事儿似地走到我面前,说:“把舌头伸出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一下就把手指头按在我舌头上,鼓着眼睛往嘴里看。我气得骂起来。舌头怎么能让人乱摸?恶心得我没吃中午饭。
傻子读了《赤脚医生手册》,神神叨叨,真烦人。什么你有钩虫啦,什么你大概是胃癌早期啦,什么你这腰疼是椎间盘突出啦。我整个儿成了残废,只配喘气儿等死。可山上他实在干不了的活儿,都是我帮他干完的。干完了,坐下来冒口烟儿,他就打开地上的干活衣服,拿出《赤脚医生手册》嘟嘟嚷嚷地看。
我七三年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等知人事了,就看见傻子在身边儿,问他:“我是什么病?”傻子想了想,就去翻书,说了一堆关于病因的词儿,可我到底没听出来我是什么病。我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都是傻子伺候的。拉、撒、吐,傻子一点儿不嫌乎。我对他说:“傻子,你当大夫行不行,我不敢说,你要当个护士,有富余。”
连队里要盖房。来了这么多年,都是茅草棚子,现在大家觉着可能要在这儿一辈子了,也都拥护着盖房。再说山外的老场,都是瓦房,干净、结实,瞧着是那么回事儿。
盖房要料。椽子、檩、梁,都要木头。木头这儿可不缺。可要一顺儿的料,不易。要进山里找,看哪儿成材的树比较集中,开进一彪人马,先修路,再伐树,用肩扛出来,劈劈锯开,得费不少劲,才能上房。
盖第三栋房的时候,进山找树的活儿派给我和傻子了。我们带上一天的吃食,捏着砍刀,顺山往北去了。为什么往北?不知道。往北就是往北。这儿东南西北都是野林子,往哪儿走都是树,往北有什么不行呢?自打来了这儿,鬼使神差的,北京知青有事就往北,上海知青有事就往东,没什么道理。
我们往北走了半天,都是些确立拐弯的树,按书上说,就是“婀娜多姿”,重看不中用,谁家的屋脊,也不愿意盖成蛇式的。于是又往前走,可就没路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加上在这儿不少年了,还怕这个?砍!砍出道儿来往里走。队上给这么个活儿,这是脸,不能丢。这原始森林,整个儿一个叫严实。树是高高矮矮,枝搭枝,叶碰叶,藤缠着,树树相连。地上一人高的荒草,乱成一团。想在林子里走痛快?没门儿!得用道,一刀一刀涮开,砍开个人能钻的道儿,才能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难!

我在前,傻子在后,我们就往北砍去。这样一直走到下午。我忽然觉得不对劲儿。换个样儿说,就是我觉得不是往北了。北是哪儿呢?不明白了。其实说是下午,也是因为腕子上带着表。这时天阴上来了,从哪儿看出林子去。没有太阳,怎么看出西来?我沉了沉气,没回头,说:“傻子,现在是往哪儿呢?”没听见音儿,回头一看,傻子正抬着下巴转来转去地看,看了一会儿,说:“那边吧?”我说:“那边呀?说准咯!”傻子说,“我反正跟着你,你不是往北吗?”我说:“我找死,你也跟着我找死?我考考你,哪儿是北?不能白干这么多年!”傻子说:“你别考我这个。你考我医药知识吧。”我说:“呸,到这时候了,医药管个屁用!说吧,哪儿是北?”傻子笑了,说:“我看哪,是你找不着北了,借着问我,转转向。接着走吧,我跟着你。”看着他那傻样儿,我开始慌了。
人一迷路,就像做梦。梦急了,还有个大喊一声醒过来的时候。可迷路,是真的,急也不行,越急越迷。这种时候,只有蹲下。我就蹲下了,先定定神儿。傻子以为歇了,也坐下了。他还带着那本手册呢!立刻就翻篇儿看起来。我一肚子火儿,就慢慢地说:“傻子,又学习哪?上头讲哪儿是北了吗?”傻子笑嘻嘻地抬起头来,正想说话,一看我的脸色儿,笑摸样儿就定在脸上了,赶紧把书收起来,凑过来,问:“你找不着路了?”我说:“废话!等死吧!”傻子说:“那照原路退回去吧?”这傻子傻,可这句话真是管用的实话,我怎么没想到呢?心里松了一口气,就伸腰躺下去了,点上烟。说:“退回去?料还没找着呢,有什么脸回去?”傻子说:“那就往前找吧?”我噗嗤一下乐了。这傻子是真傻,他一辈子也不会懂别人说的是什么。
我站起来,伸了脖子慢慢转着看,瞧有没有熟悉的山头。若能看到熟悉的山头,队上的方向就可以算出来。没有。我后来回城里把迷路的事跟人说了,别人立刻一套一套的什么树的年轮的疏密呀,什么枝叶的趋光生长方向呀,什么树皮色儿的深浅呀。我心里想:嘿!敢情明白人全在城里待着抽烟儿呢!那时候,怎么不飞在半空朝我说这些明白话呢?
反正我们是:迷路了。
傻子也明白了,有点儿慌,催着往回走。我也有点儿慌。天一黑,什么人也得慌。真是老天爷不待见我们,下起雨来了。先躲雨吧。我们俩站到一棵大树下,又不敢靠近树干。在学校老师讲的这点我还记得:一打闪,那电就会顺着湿树往地下走。这湿树干分明是个导体,碰不得。又抬头看看树高不高,高,就招电。树都缠在一起,也分不出高不高。
雨是越下越大。我们一人砍了一张大芭蕉叶,背在身上。不太管事,雨太大了。傻子一把一把地从脸上往下抹水,说:“完蛋了,我的书完蛋了。”我也没说什么。
天完全黑了,我们开始哆嗦。林子里一点儿热乎气儿也没有,全叫雨水给带到山下去了。我说:“傻子,吃口东西吧。”傻子的牙“哒哒”地响,说:“吃,吃,吃吧。”我一摸,书包里的饭全泡大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再说。黑暗中,你抓一把,我抓一把,一会儿就全吃了。我说:“傻子,咱们可全吃完了。好歹到天亮,赶紧往回走,谁也别充大个儿了。”傻子说:“咱们上树吧?”这野林子里,什么虫鸟都有,地下净是水,只有上树,免得碰上野物,叫它们会了我们的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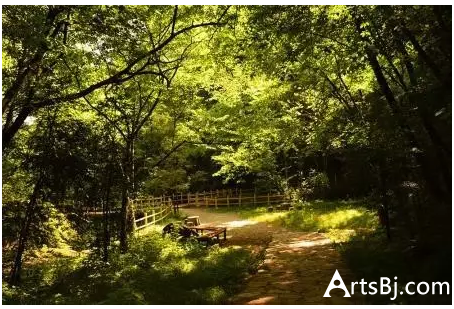
我们拉扯着,好歹上了树,在一个大杈子上蹲坐下了,背靠着背,还暖和一点。这一夜,风没停,雨没住,也不敢睡死,一个栽楞掉下去,不死也伤,迷迷瞪瞪,哆哆嗦嗦,唉,我都不好意思说,还不如在树杈上躲雨的家雀。
可天亮了,雨还没住。赶紧下了树,管他是泥是水,往地上一躺。腿蹲得直抽筋儿,可真舒服啊!
我是彻底绝望了,大雨一浇,砍倒的草又长好了,砍的痕迹极难找,慢慢儿找,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出去的。这之前,我们傻走了一天哪!傻子是真傻了。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呆着愣神儿,可谁也明白。傻子说:“你说吧,怎么着?我听你的!”态度很坚决。我要有依靠的,我得比你坚决。
我盘算了又盘算,跟傻子说:“这么着:咱们在这儿不能动。咱们才出来一天,离队里不会远道哪儿去。若是再走,谁知道是往近走还是往远走呢?现在要保持热量,不能拉屎,不能撒尿。咱们平常撒完尿,不都一激灵吗?那就是尿把热乎气儿带走了,身子骨儿哆嗦呢。这山上,常有老百姓打野物。咱们支着耳朵听着,有个响动,就招呼。见了这种人,咱们就算有救了。怎么样?”傻子说:“对,就这么着。可我这尿憋不住了。”傻子就憋着,不敢动弹。
雨慢慢停了,云在山上跑,像野马似的。一会儿,云渐渐高了,山上亮起来。忽然一下,太阳出来了,照得到处鲜灵灵,亮晶晶的。唉,这日子,多好!可我们是在这儿半等死。我说:“别在这阴处等死,找个地方晒太阳去,还能补充点热量。”我们站起身找了一个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坐在一块大根根上。地气蒸上来,各种小虫儿都活泛了,飞来飞去。我和傻子把衣裳脱下来,光着身子拧,拧干了,先把短裤套在手上挥,干了穿上。又把长衣裳平铺在草地上面,让太阳晒。傻子暖和过来,说:“我可撒尿了?”我说:“这事儿少问我。”他一撒,引得我也撒了一泡,身上真痛快!
我被晒得暖洋洋的,就砍了张芭蕉叶垫在身后躺下了。傻子呢,在旁边一页一页地剥那本手册,极小心极小心的,像揭伤口的疤。我说:“算了吧,一本破书,等出去再买一本。”傻子摇摇头,很伤心的样子,说:“这本儿扔不得,上头有我记的好些心得体会呢,还有偏方。唉,早知道,不用圆珠笔记,这一湿,都泅了。”傻子还是傻,什么时候了,还磨烦这个?昏昏沉沉,我就睡过去了。
忽然我觉得有什么往脸上打我。我一机灵,醒过来,太阳晃得什么也看不清。就听傻子说:“老沫儿!老沫儿!有响动!”我马上窜起来,叉着腿听。刚醒过来,什么也反应不灵,听不出什么响动,倒是有鸟儿在叫。我正纳闷儿,傻子一把揪住我,慌慌地说:“别是野兽!熊吧?”我也紧张了,难说!傻子说:“走,先上树。”傻子是没进化好,一有事儿就想上树。可这种情况,还是上树稳妥。我们抓了衣服,上了树,光着身子,碰破了不少地方。
确实是有声:刷拉—刷拉,挺重,挺急。我们缩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一会儿,远远的,大约有二十米吧,草动来动去。有个东西在走,不是往我们这儿走。正在这时候,那动着的草里,忽然闪过一个头!是人哪!妈,我的亲娘!我不顾一切地大叫:“嘿——!嘿——!”生怕佛祖派来的菩萨听不见凡人的声儿,就这么过去了。
草不动了。一个人头转到我们这个方向,远远的,眼睛里一道光闪过来。我和傻子慌慌张张下了树。可一下树,草高了,那个人又看不见了。我和傻子拼命大叫:“嘿——!这儿哪!”傻子又叫:“救命啊!”我按住他,说:“死不了啦,别这么惨。”我和傻子一边儿拿刀涮草,一边儿往有人的那个方向移动。
不一会儿,那个人也蹚过来了。这是个僾尼族,脸黑黑的,光着头,一身黑衣,裤子退又宽又短,上身敞着,结结实实一胸脯子肉,手里捏一把细长刀,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看着我们,眉微微皱着。我们两个汉人,只穿短裤,都比他高出一头,手里也捏着刀。大家一时竟谁也不说话。
我心里松快极了,就笑着说:“我们是农场的。”那个僾尼族汉字上上下下看了我们,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真要命!我们来这么多年,僾尼族话不会说不会听。
我们双手双手推出来,往四面八方做了一个寻找的姿势,又摇摇头,就看着僾尼族汉字。僾尼族汉字笑了,点了点头儿。嘿,他懂!他知道我们迷路了。可是他又摇摇头儿,说了很多话,脸上很是焦急。我以为他误会我做的姿势是想找个游水的地方,就又沉住气做了一遍,之后摇摇头,深深地叹息了一下,把手拽在一起,尽量用最可怜的眼神望着他。他也跟我演开哑剧了,用手在肚子上做了一个凸出的姿势,又摇摇头,哇哇地叫了几句,把刀甩起来,转身就走。我和傻子慌了,提着衣裳和刀,在草里跳着追过去。那僾尼族汉字站住了,回身愤恨地看着我们,傻子突然说话了,不是说话,是也舞动起来了。他用手在肚子上虚摸出一个凸形,又抬起一条脚,从屁股底下往外淘了几下,又挺难看地皱起脸装出哭的样子,再尖着嗓子挤出“哇、哇”的声儿,又把两条胳膊圈在胸前,身子晃来晃去,嘴里“嗯、嗯”地哼。不想那个僾尼族汉字非常高兴,哇哇叫着,连连点头儿,傻子笑着对我说:“他的意思是说,有人生孩子!”我松了一口气,急忙抓住傻子,指着傻子的手,又并起食指和中指,用大拇指慢慢地往一起靠,意思是这个人是个打针的,也就是医生。
那个僾尼族呆了呆,在想,又看看我们,突然走过来,一把抓住傻子,拉了就走。好,那就有门儿!赶紧跟着。我和傻子都还等于光着身,傻子一身的瘦筋在皮底下滚来滚去,踉踉跄跄地脚下绊着草。这原始森林里,其实有好多道儿。可这道儿,打个比方,有点像外省人看北京的胡同,不知道哪条走得,哪条走不得。山上打猎的人,常常有些小路,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只有走惯了的人,才能从乱七八糟的树棵子,草丛中走过去。我们就这么紧跟着,翻了一架山,下到了谷地。忽然,那个僾尼族汉字站住了,听了听,又快步往前走,只是不再抓着傻子。我们不敢怠慢,也跟了下去。

前面出现了一个窝棚。这种窝棚,是山上人打猎歇脚守猎物的栖处,极是简陋,可是很实用。眼前这个窝棚,草已经枯了,大概日子久了。一人多长,歪歪的有半人多高。那个僾尼族汉子转过身看着傻子,指了指里面。我想,是不是让先在这儿歇会儿,吃点东西?傻子探进去,一下就跳出来,两眼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是叫蛇咬了。我也探进去,一看,呵!差点儿没栽倒!
里面暗悠悠的,一双雪亮的眼睛瞧着我,一双手护在肚子两旁,那肚子凸起多高。是个女的!怀着孩子!
那个汉子笑着看我们,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样子。反正他也不懂汉语,我就说了:“傻子,这明摆着的事,你照量着办吧,我是没这个本事。你多少看过医书,比我强。我没说的,听你的!”傻子慢慢把嘴张开,脸开始白上来,半天,吧唧一下嘴,眼泪就淌出来:“你可把我坑了!你跟他说,我不会接生孩子。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转脸对那个汉子,想了想该做什么动作,忽然心里咯噔一下,就对傻子说:“唉,我说,你不是带着本儿书吗?我翻过,那上面有生孩子的事,还有图。也许她自个儿就生下来了,咱们在这儿照应着,生下来了,算咱们命大。这个僾尼族碰上这么个事,你我即是路人,也要舍命相帮着,更可况现在这个情况。干吧!咬牙!好歹有书,哥们儿在这给你帮着。是死是活,咱们拉出来看。”傻子呆呆地把书从衣裳里摸出来。瞧着这本皱皱巴巴的书,我差点跪下去了,这时候谁拿什么来换,我也不要!
傻子定定神儿,慢慢钻进去,跪下来,用指头捏着那个做妈的手腕子,号着脉。行,他开始像回事了。之后,傻子就把她的裤子往下慢慢移着,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我说:“别胡思乱想了,没什么了不起。”肚子凸出来,黄黄的一大块,傻子慢慢把耳朵贴上去,听了一会儿,笑了。我突然想起来,就在窝棚里用眼找着,只见一个长了苔的瓦罐,残了多半个口,就把它提出来,示意那汉子烧水。那汉子马上就懂,跑走了。一会儿,提来水用刀挖了一条小沟儿,把罐放在上面,下面摆了柴引着,烟就慢慢地升上去,我突然听到树上还有鸟儿叫呢。
傻子在窝棚里叫:“老沫儿,你来!”我急忙过去,看见那女的衣服已被傻子脱下来,又放在肚子上盖着。我低了眼,我还是个小伙子。傻子说:“老沫儿,这本儿书你拿着,翻到这一页。你就不停地念,什么时候我说念下一段,你就念下一段。这样,我就不用看书了。好哥们,可别念错了!”
我跪着,拿起书,捧在胸前,开始大声地念起来,念完一段,就又重复再念。开头几页,念得挺快,越到后来,重复的时间越长。不知念了多久,忽然,傻子啊了一声儿,我慌忙抬起眼,只见傻子满头是汗,喘着气说:“出来头了!混蛋!快念!你个小兔羔子!”傻子头一回这么威风,敢骂我了!好,等回去再说。也说他叫那个血呼呼的小头儿吓着了呢!我急忙又埋下头去,几乎是喊着念有小孩出来头的那幅图的几段文字。声音在野林子里荡来荡去,这时候谁要路过这儿远远听见了,肯定以为不是个笨蛋准备考试就是一个疯子在抽疯。我抽空看了一眼那个汉子,那个汉子双手扶膝跪在地上,看着我,脸上十二万分地严肃,像个听宣讲的教徒。他大概以为我在念咒呢。
我都快念昏过去了,声音开始发飘,舌头和嘴都木了,配合不上,开始南腔北调起来。手也麻了,开始哆嗦。汗从脸上流下来,迷了双眼。我就把书放在地下,擦了一眼睛,一手扶地,一手按书,接着喊。猛听见傻子在叫:“早叫你别念了,你就听不见,快过来帮我一把。”我浑身酸疼,眼也花了,爬过去,只见傻子手里托着一个粉红肉团儿,说:“你先拿着,小心!”
这就是孩子!谁刚生出来也是这样,瞧瞧你自己小时候吧。一张小脸儿皱得像核桃,眼睛挤着,嘴像没牙老太太,一撅一撅的,身上到处是褶子,小手儿小脚抽筋似地一动一动。头发真黑,一个小卷一个小卷的像非洲人。身上粘糊糊的,我也不嫌脏,这是个生命呀!我像捧着个小太阳,这小子会发光,会烫人呢!千万不能动,这肉多软呀,一动可能就会破。
那个汉子也爬过来,嘴一抽一抽的,只有眼睛笑着。我小心地扭过脖子,对他说:“是个儿子呢!”那个汉子把手擦了擦,伸过手来以为我是让他抱着呢。我急忙大喊一声:“别动!”吓得他一激灵,两只眼凄凄地望着我。我冲他笑笑。
傻子说:“这脐带怎么办啊?”咱们没有手术剪。我想起一个故事,就说:“拿牙咬,吐沫是消毒的。”傻子说:“谁下得去嘴?”我说:“那也不能叫我老这么托着啊!”傻子忽然看见烟了,就说:“对,把刀烧红了,那也是消毒。”我说:“你要给人上刑呀?”傻子一摇头,就站起来,拿过那汉子的刀,走到火沟那儿,把刀伸进去,用嘴吹炭火。一会儿,把刀抽出来,刀中间烧得青白青白的,微微带着烟。傻子把刀递给那汉子,向他示范,在脐带当中来上一刀。那汉子一直愣着,接过刀,看看傻子,又看看我。我大喝一声:“快!”那汉子又看看刀,又伸头看看黑暗的母亲,再看看我,又看看跪着的傻子,脸忽然绷紧了,呻吟了一下,把刀按下去。
一阵青烟儿。一股糊味儿。
孩子在我手上,还是那样,但他终于离开母亲了。人哪!真他妈不易。大了,什么都会干,可这时候儿,得有人帮他活下来。
傻子跪着把两头儿的脐带挽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立刻一脸血印子。他的肩塌下来,弯下腰,瘦瘦的胳膊支在地上,头向下垂着,背上的汗慢慢往下淌,一滴连一滴,慢慢结成了大汗珠,吧嗒吧嗒往地上掉。
我和那汉子都瞧着他,他一动不动,慢慢地说:“我可活过来了,洗洗吧。”我把孩子递给那个汉子,走过去,瓦罐儿里的水滚开着,已经蒸走一半了。我砍了一个芭蕉叶,正要去找水,猛听得大山沟里一个尖细的、亮亮的、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响起来,震得山谷嗡嗡的。我回过身,看见傻子只穿着一条短裤,叉着细细的两条白腿,把婴儿倒提着,用手在拍婴儿的背。那婴儿哭起来,傻子把婴儿抱在手上,哈哈大笑:“傻小子,看把你都憋紫了,我怎么就忘了你还没哭呢?别哭,别哭,是我的不是。别怨我,我和你一样,都是头一回呀!哈哈哈……”
我腿一软,坐在地上。
水找来了,倒进瓦罐,温温地给婴儿洗,又用衣裳包起来。这个小不点儿又哭了,那汉子抱着,跪进去,放在母亲身边。母亲慢慢地半撑起身子,看了一眼,又软下去,汉子就把婴儿和母亲并排放着。母亲慢慢把眼睛闭上。
傻子说:“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快叫这个僾尼族去叫人。”我示意了,那汉子就急急忙忙捏着刀走了。
我和傻子都躺下来,身上软得一点劲也没有,谁也不说话。呆了一会儿,傻子忽然噗嗤一乐,说:“老沫儿,真屈了你了。你应该去跳舞去。嘿,你学那个找不着路的样子真像洪常青带着小庞一出场,小庞到处探路,绝了!”我也乐了,说:“别小庞呀,我这块儿,可以跳常青指路。吴清华就是三百斤重,我也一手托她起来,投奔苏区!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们冤仇深。古有……”我转过头一看傻子,他已经昏睡过去了。
选自阿城文集《遍地风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