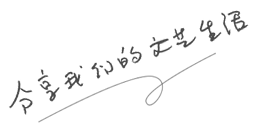她是“中国好诗人”吗?
进入微信时代以来,诗歌第一次引发了全民的关注,诗人余秀华迅速成为现象级的人物。
媒体时代,争议常常是引发关注的春药。余秀华的诗歌早在《诗刊》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广大的关注,因为还没有争议产生,尤其是没有名人介入争议,直到沈浩波、沈睿、臧棣陆续说话,才迅速形成了一个事件。
但凡媒体事件,都有一个结构。余秀华事件的结构就是:1她的诗好不好,2为什么男诗人说她的诗不好,或者不那么好,3何谓中国当代好诗歌,何谓好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她的诗真好,我也同意沈睿说的,她真的有天赋。
对于第二个问题,沈浩波说余的诗并不算好,没有艺术高度,遭到了沈睿的强烈批驳,并且引申为一种性别主义的批评。臧棣似乎比沈浩波积极,甚至反复强调她的诗比北岛的好,认为她的诗是当代诗歌的“一种进展”。但接着又说在中国比余秀华写诗写得好的女诗人至少有50个,而比她写得好的诗人有300个!
暂且不说臧棣这随便一估计,前300名中国好诗人中,男诗人已经占据了250席,这会不会让沈睿觉得,看似客观学院派的臧棣实际上和沈浩波一样都生活在男性自恋的幻象里?如果300名之外的余秀华都可以视为当代诗歌的一种进展,那她前面的人岂不是当代诗歌更大的进展?
这太不可思议了,就算在唐朝的任何一个时段,都很难说有300个诗人可以都称为当时诗歌艺术上的“进展”。所以臧棣的说法,要么就是在为当代诗歌吹牛,要么就是随便用“进展”敷衍一下余秀华而已。臧棣一直在用余秀华的诗超出了好与不好这样的话来腾挪闪躲,但却还是忍不住说她的诗引发巨大的关注,“不是因为她写的有多好”,而是因为她的诗歌为当代诗歌文化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云云,余秀华最后被定性为一个制造了问题的人,至于是否真正混得进臧棣所属的“诗歌文化”圈子,还不一定呢。最搞的是,臧棣后面还自相矛盾地说,“何况她有些诗确实写得不错”,看来沈睿的性别主义批评对沈浩波和臧棣其实都是同样适用的。
不过,暂且放下这两个比较直接的问题,我最想涉及的其实是最玄乎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好诗的标准,或更说中国当代好诗的标准。
纯的诗才美吗?
在沈睿评价余秀华诗歌的时候说,之所以是好诗,是因为她的诗符合好诗的最重要标准“打动人”或者“给人强烈的震动”。
按道理说,这种“震动”其实是要仔细分析的,因为每个诗人给我们造成的震动实质上是不同的,对于这种情感反应的分析,实际上恰恰可以揭示这个诗人的艺术特色。
但恰恰相反,沈睿没有继续分析这种感动,而是提出了几条“纯化”倾向的意见,一是批评《诗刊》用“脑瘫”来为余秀华冠名,似乎在用身体缺陷博同情;其次她拿余秀华和美国诗人艾丽斯狄金森类比,并且强调两个人都不是田园诗人。沈睿不同意强调余秀华作为农村诗人的身份;第三,沈睿也不主张强调余秀华的性别身份,似乎女权主义特别担心一个女人因为自己的性别获得“额外”的认可或否定。
奇妙的是,臧棣同样也反对给余秀华贴标签,认为脑瘫、农民、女人这三个标签都是“恶俗”。总之,沈睿和臧棣似乎要我们忘记余秀华是个女的、是个农民、是个脑瘫患者,然后“单纯”地欣赏她的诗歌,并仅仅以此来评价她的诗歌的高下。
我不知道,如果余秀华是个健康的、北上广的、男诗人,我们在读到《经过墓园》《打谷场的麦子》时,我们的“感动”会和现在的一样吗?一首诗放在那里,和写诗的人可以割裂开来吗?诗人的信息对于我们欣赏和理解一首诗歌的美,到底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甚至会不会是有害的?
美的表皮与深处
从余秀华诗歌的评价之争议,出人意料地进入到这个美学史上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到底存在于形式,还是内容。或借舒斯特曼的概念说,是存在于表皮(surface),还是在深处(depth)。
在东方儒家艺术评价传统中,美很少只停留在表面,从《论语》中的“绘事后素”到明清小说评点,美总是具有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表层是形式方面的形色、节奏、韵律,深层是道德方面的善恶雅俗正邪。
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美也同样具有道德维度。但从康德开始,形式主义后来居上,美变得越来越薄,最后变成了一层不透明的表皮,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有意味的形式”等等,在绘画的画面和诗歌的文本之外,再无作品多余的美存在了,真如钱钟书先生说的,吃鸡蛋的人没必要去认识下蛋的老母鸡,看了《蒙娜丽莎》的人也没必要去从达芬奇的生平或艺术史中寻找这幅画更多的审美价值了,美全部存在于作品本身,没有任何溢出。
这种形式主义,或纯美主义,在现代接连遭到重创,首先是海德格尔揭示了艺术品作为“此在”的深邃结构,他的学生伽达默尔更进一步将这种此在描述为效果历史;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布尔迪厄、本雅明等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艺术品和美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所以今天,纯美,纯形式,纯诗等等说法,已经不具有学术上的严肃性了,不过是见识尚浅的文艺爱好者们常用的词汇而已。
她是她的诗歌没有出声的部分
上面为了解除纯诗的幻觉,不得以班门弄斧剪辑了一下美学史。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说,要真正理解余秀华诗歌的美和价值,就不能屏蔽诗人本身的特征:她的性别、她的农民身份、她的疾病,诗和诗人是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生活、解释和经验这个世界的过程和方式,就如余秀华自己说的,她是她的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她是“以血供字”的人,而沈睿和臧棣要把这滋养文字的“血”清洗掉,认为这是恶俗的标签。
比方说她的诗歌里最为动人的意象之一“雪”:“我按住心中的雪,怕它太接近春天”,请注意,这雪不是岩井俊二镜头里唯美清纯的女主角睫毛上的雪,而是湖北乡村冬季里油菜苔上的雪,你不赤着手捋取你不会知道它的冷和尖锐,但南方的暖又让这冷而尖锐的雪也很脆弱,阳光一晃,很快就消逝了。试问,不了解江汉平原的冬天,没见过冬日菜田里的雪,你真的会完全领略她诗歌中的情感和触动吗?
还有她那首著名的《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如果出自一个衣食无忧、曾经做过外企高管,现在只想寻找一次刻骨艳遇的玛丽苏之手,这诗带给你的感动和余秀华的一样吗?
其实与余秀华带来的震动,并不是没有前例,“打工诗人”已经是一股力量,郭金牛的《纸上还乡》最近还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之所以不能不强调他们的身份和疾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要克服身份和疾病需要多大的毅力,这种能量是构成我们感动的重要部分。
所以,农民身份是构成余秀华的诗歌的内在要素,在中国不存在田园,只有农村,所以余秀华不是在唐顿庄园里写出这些诗的,她是在中国式的农村里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真正的诗人;郭金牛也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打工者,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工人和打工者之间的区别,尤其还是在富士康工厂里的打工者,他竟然成为了诗人。
所以,我认为诗歌的力量不是因为它纯,而是因为它深,尤其是它因为诗人本身世界的展开变得深邃。因为这个,我们不需避讳余秀华的性别、身份和疾病,因为她克服这些东西才让我们感受到生命能量之强大,她完全不需要博得怜悯和同情,其实反倒让我们会反思自己、同情自己,我们是不是何时何地浪费了生命的力量。臧棣说,她不是一个农民诗人,只不过是一个诗人生活在农村。这是不是说,余秀华相当于在黄州写田园诗的苏东坡,或者干脆就是女版的陶渊明。我忍不住怀疑排在中国前300名的诗人们是否能消除对女性、农民和打工者以及疾病的潜意识的歧视,这或许就是他们虽然都是“中国当代新诗的进展”,但却始终无法像余秀华这样引发巨大赞誉和关注,也无法引起国外真正赞誉和关注的原因吧。因为自恋,因为狭隘。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