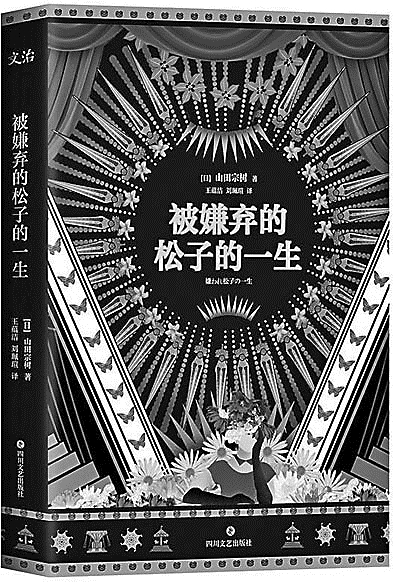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日]山田宗树 著 王蕴洁 刘珮瑄 译 文治图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
“生活安逸时,作绝望之诗。”
松子如你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步履匆匆赶去上班的她,你可以在理发店看到熟练挥舞剪刀的她,你可以在三尺讲台上看到兢兢业业的她。她的一生就犹如泼入米缸的牛奶,将周围的一切都浸润得圆实饱满,自己却看不见一丝痕迹。
年轻时的松子是一个貌美如花、温润如水的姑娘,就像一件精雕细琢的花瓶,人们都喜爱她,她竭尽所能包揽着身边所有的事物,花瓶里的东西越塞越多,渐渐超过了她本身的容积。她想着,“我还能再装一点,别人给我的,我就要接下,别人不给我的,我要努力争取到。”花瓶出现了裂纹,她不管不顾,依旧往里面塞着别人弃如敝履的东西,“啪”,花瓶终于裂开了,碎片撒满了一地,碎瓷难圆,她回不去了,可是她却从未想过她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她翻动着自己的身体,心里念叨着,“碎片锐利的一面一定要埋在地底,平滑的一面留在地表,这样人们踩上去,就不会划破皮肤了。”无数双鞋踩在这数不胜数的碎片上,人们觉得十分舒服,就像踩在了凹凸不平的按摩轮上,碎片越陷越深,直到与土地融为一体,它们被裹挟进无穷无尽的黑暗里。
松子幼时被父亲冷漠地对待,二十多年在缺乏爱的环境中成长,“爱”成为她一生中最为渴望的东西,她穷其一生追逐它,却因为它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她被赶出学校时,她渴望得到佐伯的保护;当她深爱的落魄作家彻也自杀时,她渴望他带她一起走;当赤木离开土耳其浴店时,她渴望他将对自己的爱坦白地说出来;当她赚足了钱,她渴望和小野寺金盆洗手,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她想自杀时,她渴望与救下她的岛津白头偕老;当她穷途末路时,她渴望与龙洋一重新来过……她将每一个平淡如流水的日子憧憬为美好无瑕的日子,将琐碎的幸福无限地放大直到它们将她包裹得密不透风,她堵塞住自己的双耳,蒙蔽自己的双眼,只听得见内心深处自欺欺人声响——可这些终究只是幻想,五彩缤纷的泡沫迟早会炸裂,那噼里啪啦的声响似乎都成了无情的嘲笑声。或许这正如毛姆所说的,“人们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痛代价。”只不过这代价对于松子来说太重了些,这世间所有的悲凉与凄惨似乎都压在了她本就羸弱的躯体上。
松子是典型的服务型人格,“过分无私,时时想的是别人的生活所需,而对自己欲求总是能忍则忍,最终荒废了自我。”松子将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人,物质、前途、爱情,只要是她有的,她都会拿出来送给别人。父亲要她学习文科,她放弃了深爱的理科,父亲却依旧对她冷眼相待;落魄作家彻也要她当土耳其浴女郎,她放弃了纯洁的身体,却被彻也拳脚相加;当她放弃了最爱的美发师行业,在监狱外苦苦等候龙洋一,换来的却是一句“你走吧,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松子似乎总觉得,“当我能感动自己时,想必也能感动他人吧。”松子的价值,不在于她得到什么,而在于她可以给予别人什么。
松子的一生是无数人的缩影,在学生面前营造出为人师表的形象;在男友面前营造出秀外慧中的形象;在好友面前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形象;他们看似匆忙实则是为了掩盖碌碌无为的生活;他们看似充满主见实则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他们看似左右逢源,胜友如云实则孤苦伶仃,无人问津。他们戴着面具,穿着密不透风的衣裳,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当他们想揭下面具,脱掉衣裳,随之而来却是刻骨铭心的难受,它们早已与身体黏在了一起,将它们剥离之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即使承受住了巨大的痛苦,却依旧无法重返最初的模样。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