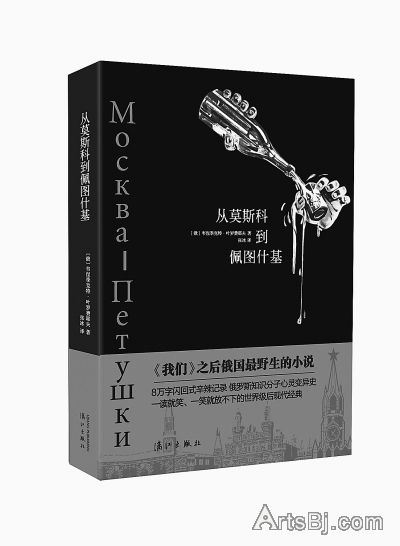
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文学神话归属于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确切地说,归属作家本人和他小说中的同名主人公韦涅奇卡。他们“走出地下”,在祖国的土地上享受合法的阳光雨露,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但他们甫一“出世”即获得彰显的姿态———似乎文学艺术的每一个细部都在为演绎这个神话添砖加瓦,一个曾经“非法”的难产儿在十几年间的“言谈传播”体系中,以“韦涅奇卡·叶罗费耶夫”为主角的醉酒神话、宗教神话、后现代神话等神话形态基本形成。
俄罗斯酒文化代言人
小说中的韦涅奇卡以“酒气熏天”登场,可以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大半行程,主人公随时都要喝上几口。没有酒的时候他忆酒、买酒、盼酒。在车厢里,韦涅奇卡和左右相临的乘客喝酒、论酒。话题中“库普林和高尔基总是醉醺醺的,从来就没清醒过!”契诃夫“临死前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死了’,‘给我倒点香槟酒’。”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间万象、逸闻趣事都是通过酒这个三棱镜来审视的”。
研究者巴什科娃统计并归类了小说中提到的50多种酒,同时,她还将“俄罗斯文化中最饱含酒气”的称号赠与《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在文学研究界,有观点提出“酒是作家叶罗费耶夫创作的根本与实质所在”,评论家丘普里宁更是把作品直接解读为“一个俄罗斯酗酒者的自白”。于是乎,现实生活中的“韦涅奇卡”成为“伏特加歌手”在人们的言谈中广为传播:“没有白兰地他是不会开口的”;“俄罗斯三分之一喝酒的人阅读过叶罗费耶夫,优秀的人中有五分之四一边喝酒一边读叶罗费耶夫”;“俄罗斯醉酒神话是开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钥匙。”作家本人的话也给了这类“言谈”以有力的支撑。在一次访谈中,来访者提醒他酒精对治疗喉癌不利,并劝他不要喝酒,他说“我是俄罗斯人,我是韦涅奇卡,我怎么能不喝酒呢?我劝你也和我一样放开来喝,否则,你就读不懂《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你就无法理解韦涅奇卡这个主人公。”
在某种程度上,极好地塑造了“醉鬼”典型的作家叶罗费耶夫成为最具特色的俄罗斯酒文化的代言人。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则在小说主人公韦涅奇卡醉酒时的麻木、呕吐、恶心,乃至他的激情表白中体悟到存在了几十年的苏维埃生活语境:“现在,俄罗斯所有会思考的人……长醉不醒!即使把伦敦所有的钟都敲响,那俄罗斯也没有一个人会抬起头来,他们陷在自己的呕吐物中,都痛苦不堪。”
宗教意识极其厚重的作品
苏联解体前夜的反酗酒运动以失败告终,把伏特加酒称呼为“俄罗斯上帝”的观点也略显武断。然而,附着在醉汉韦涅奇卡身上的上帝魂灵被人们普遍关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小说中的圣经情节、圣经语汇与宗教意象,被具有深厚宗教背景的俄罗斯国民轻易读出。叶罗费耶夫的朋友、语言学家穆拉维约夫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是一本宗教意识极其厚重的作品,……正是那个韦涅奇卡贯注了浓烈的宗教倾向。”小说中共有170多个与圣经有直接或间接关联之处。近4倍于小说篇幅的注释本作者符拉索夫认为:作家“汲取了圣经中能汲取的一切”。
在韦涅奇卡的旅程中,有诸多细节与圣经故事具有明显的暗指或映射。据此看来,主人公的醉酒也是一种“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因为喝酒,韦涅奇卡接近了真理,他“已经处在一个很容易看清真理的位置”,也正因为“望着真理,所以心中很苦”。可以说,弥漫全篇的孤独、悲伤、苦难与祈祷是醉汉韦涅奇卡对污浊尘世的感情回应。众所周知,俄罗斯民族有着极其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沉寂,它在苏联后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回归热潮。在“宗教复兴”的大浪中,普希金的创作基础被认为是基督教文化,高尔基的“母亲”与儿子巴维尔成了圣母与圣子的关系,诸如俄罗斯文化是“讲新约戒律语言的文化”这样的观点也登堂入室。简言之,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宗教意识再次成为认识世界、审视文学文化活动的一种范式。
时空无序与反体裁写作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开始的头一章就为时间与空间的全面混沌定下基调,“每当我寻找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总是一成不变地跑到了库尔斯克火车站”。尽管小说文本以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列车线路的相临站点为章节标题,也清晰交代韦涅奇卡是早晨8点16分踏上电气列车去115公里外的佩图什基,可是火车刚刚行进了100公里,车窗外已经是漆黑如夜。作品中还充斥着主人公对方位的不断确认和重重疑虑,终了时分,这一回实心实意地去佩图什基的主人公死在了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时空如此无序,以至于韦涅奇卡是否坐上火车都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旅程似乎只是思想上的旅行,其实主人公一直都在莫斯科城中打转”,还有人认为,韦涅奇卡是中途被下车乘客挤到站台,又糊里糊涂地坐上回返列车。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曾把后现代的转移归因于我们对空间和时间之体验中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作为历史坐标的时间和空间存在大大淡化,可以说,叶罗费耶夫的小说文本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伴随时空无序这一叙事策略的,是作家故意而为之的反体裁写作。叶罗费耶夫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长诗”。但有学者认为:“传统叙事长诗的特点在小说中已经丧失殆尽”。可以说,自作品《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问世,俄罗斯国内各界对其体裁的界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让人颇感踯躅的问题,因为我们还要面对中外文体差异和术语的对等翻译,只好大而化之地称其为“小说”,至于是流浪汉小说、冒险小说还是魔幻小说,抑或是其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字里行间韦涅奇卡自己都调侃:“鬼才知道我将采用哪种体裁到达佩图什基,刚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切都是哲理性随笔与回忆录,一切都是像屠格涅夫那样的散文诗,现在么,可是侦探小说开始了……”
在某种程度上,叶罗费耶夫神话就是俄罗斯民众对曾经的极权体制的心理回应,当然,它也是群氓大众对现在、对未来的一种生活态度上的情绪选择。如果说现代社会以来的政治神话和国家神话(关于自身历史和意义的宏大叙事或意识形态)可能是被公认的,也可能是被强加的,文学神话则不然,彻底地人为制造是不可能的,它的背后总有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可以确认,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文学神话———叶罗费耶夫神话即是如此,关于“韦涅奇卡”的每一神话形态都被众多的拥趸者赞同以至“迷思”。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