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大卫·格罗斯曼
相比2007年来华的阿摩司·奥兹受到的追捧,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到来仅在小圈子里引起关注。而在以色列,格罗斯曼、奥兹和A.B.约书亚被称为当代以色列文坛三巨头,格罗斯曼本人戏称三人是“文坛三大男高音”。除了写作,格罗斯曼和奥兹一样,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长期呼吁巴以双方停止冲突,并主张巴以领土合并,实施“一国两制”。
日前,大卫·格罗斯曼来到上海和北京,参加一系列文学活动并接受了早报专访。在格罗斯曼看来,写作是他理解生活、周围人和处境的唯一方法,“只有形诸笔墨我才能真正理解。每当我写到外界的武断,写到占领,以及别的事情,我就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些解脱。”格罗斯曼的代表作《证之于:爱》已于200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近作《陆地尽头》中文版将于下半年出版。
在别的国家,父母还在尴尬地对孩子进行性启蒙,我们却在对孩子说大屠杀,说死亡的事。
“对于每位犹太作家来说,他们都会试图去触碰大屠杀题材,就像任何作家都会写爱情一样,是否这样?”早报记者好奇地问眼前的大卫·格罗斯曼,在他那复杂又极具结构和语言实验性的《证之于:爱》中,作家从不同视角探寻了到底什么是大屠杀,大屠杀对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本人或你的家人遭受了这种终极伤害,你又怎么可能不写呢?我出生于1950年代,那会儿有人还刚从集中营回来。他们在精神上伤痕累累,得费很大力气才能重新相信他人、相信自己还想活下去。他们的家人全都被消灭了,设身处地地想想吧。他们还愿意生孩子简直就是奇迹。我们当然应该写。”大卫·格罗斯曼不假思索地回答。
和许多同代以色列人不同的是,大卫·格罗斯曼不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我父母很幸运,我母亲1930年代出生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我父亲出生在波兰一个小镇,1936年就来到以色列。但从某个角度看,我、我的同辈、我们的后辈,大家都是大屠杀的孩子,因为大屠杀的记忆深深烙印于我们记忆中,让我们痛苦。”
格罗斯曼回忆说,小时候每天下午1点20分到1点半吃午饭的时候,总有个女新闻播报员在报失踪者的名字,“那是他们的家人在找他们。你能感受到人们努力想让生活恢复正常,想把失去的身份找回来。每顿午饭都伴随着伤心的旋律,一长串一长串失踪者的姓名,谁在找孩子,谁在找姐姐。我们从小听着这个长大,都习惯了。但听着就产生了一种特殊感觉:我们觉得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爸妈保护不了我们。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才三岁,幼儿园阿姨就跟他们说了大屠杀的事。在别的国家,父母还在尴尬地对孩子进行性启蒙,我们却在对孩子说大屠杀,说死亡的事。儿子问我:纳粹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对我们做那些事?我当时感到一阵本能的抗拒,我不想告诉他,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因为我觉得,他一旦知道了,这个纯洁的孩子就会被污染。”《证之于:爱》写的就是一个小孩独自对犹太身份、大屠杀和死亡的探索。[Next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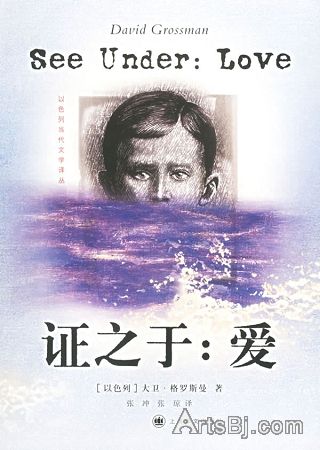
格罗斯曼想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写大屠杀,“我觉得没法不写这本书。我觉得自己身上有那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作为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人,作为父亲,作为作家,作为一个说希伯来语的人。除非设身处地地假想自己曾在‘那个地方’(集中营)生活,并将这经历写下来,否则我就不可能理解自身。我想问问自己:作为犹太人,如果我在场,我会怎么样?我会成为怎样的人?会同流合污吗?会自杀吗?我会做什么呢?在这部杀人机器将我身上的其他人性统统抹掉之后,剩下的会是什么呢?在大屠杀里,人们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失去伴侣、失去孩子,没有名字,只有手臂上文的号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为了保存自我,会做什么呢?”
1986年,《证之于:爱》的出版令格罗斯曼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这部小说被公认为几十年来反思大屠杀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里,格罗斯曼并没有简单叙述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而是不断拷问自己或者人类,在极端环境下,普通人能否抵御诱惑和绝望,“许多身陷战争和敌意的个人和民族,他们都在为这些心理所引诱。我没法把现代人的境况和纳粹那会儿相提并论,但对邪恶的习以为常是相似的。个人在这样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是如何行动的?我在所有作品中都写到了个人对外界的武断的反应;身处其中,你该怎么行动呢?”
尽管有时候很难相信会有和平,但要是绝望的话,我们就没救了。
“你一直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合并,这真能解决问题吗?但与此同时,你还说过以色列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一名活跃于以色列社会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大卫·格罗斯曼坚定地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呼吁巴以领土合并。格罗斯曼的辩护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只有600万犹太人,周围是3亿穆斯林,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想让我们待在那里,他们希望以色列能消失。就算未来有了和平,以色列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我在以色列属于左翼,告诉各位,我不相信阿拉伯国家对我们有什么善意,我希望能有支强大的军队保护我,但是,要想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过上正常的生活,军队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军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靠对话解决区域争端。”[NextPage]
“我们,以色列人,自认为很有道德感的社群,是怎么会如此富有效率地占领别人的领土的?我们甚至占领了就不愿放手。我们对占领者的身份上了瘾。成为强大的一方自有其吸引力;施行武力甚至让人觉得甜美,让人欲罢不能。”“许多人觉得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相互作战,只能仗剑而生,仗剑而死,只能杀人或者被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也许这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民族的最大悲剧:他们不再相信在未来的某时会有条出路,于是渐渐地被引诱着走向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而要指出别的解决之道也变得越来越难。”和许多来自中东地区的其他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格罗斯曼也是一位谨慎的悲观主义者。“你觉得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地区获得和平吗?”“尽管有时候很难相信会有和平,但要是绝望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格罗斯曼又说,不仅是巴以的和平如此的遥远,就连“和平”这个词也可能从字典上剔除了,“‘和平’在我们小时候还是个崇高美好的词,我这一代的以色列孩子开始学写希伯来文时,第一个学的就是这个词;但现在说到‘和平’,它已经连梦都不是了,它是危险,是幼稚,是幻觉。”
“我们得和恐惧焦虑绝望的本能作斗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是,我们两个民族是对方的镜像:两者的情感、幽默、抱负、社会,乃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各个方面都很相像,但两者都拒绝承认这些,只看得见将自己和对方分离的东西、让双方争斗不息的东西。”格罗斯曼是如此洞彻巴以两个民族如今的民族心理。
写作就是重新选择一次生活
尽管家族并没有遭受二战的屠戮,但2006年一场悲剧降临在格罗斯曼头上。那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冲突,就在格罗斯曼和奥兹、A.B.约书亚在电视上共同呼吁停战的第二天,格罗斯曼的儿子驾驶的坦克被火箭弹命中,此时离双方停战协议生效只剩下数小时时间。
谈到战死的儿子,格罗斯曼的声音明显微弱了许多。“我们在2006年的对黎作战中失去了我们的孩子,他是个士兵。我当时正在写一本小说《陆地尽头》,哀悼过后,我接着写小说。孩子死后,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什么事都失去了意义,到哪里都觉得格格不入。而继续写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立身之处的最佳途径之一。写作就是重新选择一次生活,能够幻想,能够将生活注入人物,能和与你不同的人物心心相印,能不屈从于仇恨,能不屈从于绝望,这些,我都能通过写作做到。”
事实上,预想中《陆地尽头》的内容居然和格罗斯曼的现实经历如此相像。“写作时预想一方面描述我们的遭遇,对战争、恐怖和占领做个史诗性描述;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描述这个家庭在这个时代背景中的独特之处,想发现和探索其中的秘密:父母的关系,他们用身体创造抚养了孩子,还有兄弟间的关系。”
《陆地尽头》的完成,格罗斯曼说感谢身边很多朋友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在中国更为知名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我、奥兹和约书亚,我们自称以色列文坛的三大男高音。我们的书出版前都会给对方先看手稿,这个很少见。我的孩子过世后,奥兹和约书亚来找我,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这部小说(《陆地尽头》)。奥兹说:‘这小说会救活你。’是的,写作救活了我。”
在格罗斯曼看来,写作是他理解生活、周围人和处境的唯一方法,“只有形诸笔墨我才能真正理解。每当我写到外界的武断,写到占领,以及别的事情,我就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些解脱。每当我写到这些,我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不是动笔写过的东西,我就理解不了,这是我在和现实接触时的缺陷。”
写作或者是语言也是作家冲破谎言、专制重新获得自由的工具,“如果你身处一个被扭曲的环境——比如我们以色列——首先被操控、被扭曲的永远是语言。政府、媒体、军队、警察、司法,他们会编写自己的词典,目的是保护我们,当然也是在欺骗我们。”被伪造或漂白的语言可能会让人处于无知状态,在格罗斯曼那里,他用自己的语言为现实命名,而在那刻“我变得不再冷漠、不再麻痹,专制也变得不再像是一面没法突破、没法改变的墙壁。我可以在墙上找到裂缝。我不是无助地掉入深渊,而是能有所作为,能保住一些个体性,使其不被扭曲的语言所没收”。
(编辑:李明达)








